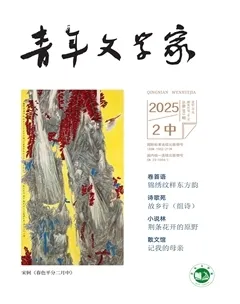半透明的雨
雨又淅淅瀝瀝地降下了。
對(duì)于雨,多年前我是很欣喜的,尤其是黃昏的雨,霧蒙蒙的天色中含著靜謐的綺麗,一瀉而下。雨水急促地穿過(guò)稀薄的云層,幾近透明的日光被掩藏于身后。
現(xiàn)在我對(duì)雨卻充滿了厭惡。
在這樣的雨天,來(lái)往的車輛卻絲毫沒(méi)有減速的意愿,飛馳而過(guò)的車輪,濺起一地的污泥,切斷了行人彼此打量的目光,他們只得謹(jǐn)慎地行走著,眼神慌亂地盯著輪胎,隨之轉(zhuǎn)動(dòng)。
公交車停了,站旁的人搶著上車,柏油路上的人開(kāi)始奔跑,待到他們一齊涌入車中,車門便啪嗒一關(guān),輪胎同樣急匆匆地向前轉(zhuǎn)動(dòng)著,和這急促的雨水一樣心急。公交車?yán)锵喈?dāng)寂靜,我縮在角落里坐著,呆望著被雨水沖刷著的半透明的玻璃,隨著車身不住地晃動(dòng)。
公交車在紅燈處短暫地停下,車窗也停止了晃動(dòng),我只覺(jué)呼吸一滯,竟從窗外看到了倪華!闊別多年的倪華!她撐著傘徐徐前行,透過(guò)雨水,她的臉?biāo)查g模糊起來(lái)。少女身姿纖弱,她身上穿著一件淡綠色的碎花長(zhǎng)裙,腳上配著一雙浸了泥水的白色低跟鞋。伴著黃昏的雨,含著并不稠密的日光的雨,她走得這樣慢。
我與倪華并不相識(shí),那時(shí)我是京郊大學(xué)的交換生,在那里待了一年,第一次見(jiàn)她,卻是在我臨走的那一天。我?guī)е鵀閿?shù)不多的行囊離開(kāi)校園,回家的列車上,我遇到了倪華。
她的臉是平淡泛黃的鵝蛋臉,細(xì)長(zhǎng)的眼睛瞇起,嘴唇抿得緊緊的,瘦弱的身體緊緊地抵著身下的硬質(zhì)坐墊,似乎很怕生。她的樣貌并不出眾,可鬼使神差的,我一上車便注意到了她。一個(gè)人遇到另一個(gè)人是宿命使然,我總覺(jué)得似乎在哪里見(jiàn)過(guò)她,這種熟悉的感覺(jué),足以讓我沉迷。我仗著年輕無(wú)畏,主動(dòng)與她攀談,她卻一句話都不說(shuō),只是怯懦地點(diǎn)點(diǎn)頭。一路上,無(wú)論我向她說(shuō)什么,她只是謹(jǐn)慎地看著我,始終保持沉默。即便如此,我還是很欣喜。
車不慌不忙地行駛著,到了固豐市,她忽然起身拿起背包,我驚覺(jué)她要下車了。我頓時(shí)心急如焚,問(wèn)詢她的名字和電話,這一次她沒(méi)有繼續(xù)保持沉默,輕聲說(shuō)了句“倪華”,把寫著電話號(hào)碼的紙條塞給了我,揚(yáng)長(zhǎng)而去。她還未走遠(yuǎn),列車便已迅速駛向遠(yuǎn)方。
我把這張紙條放在了衣兜最深處。又過(guò)了十多個(gè)小時(shí)我才到站,下車時(shí)已近黃昏,外面大雨傾盆,一時(shí)間竟打不到車,所幸我家就在附近,我便把外套脫下,用衣服遮住腦袋往家的方向奔跑。待我回到家時(shí),父母早已出差在外,我轉(zhuǎn)動(dòng)鑰匙開(kāi)了門,放下浸濕了的行囊和濕透了的外套。恍然間,我想到了外套里的那張紙條,當(dāng)我顫抖地拿出它時(shí),上面的字跡早已被雨水浸濕,全然看不清了。我和倪華竟就只有這一面之緣。后來(lái),我曾數(shù)次坐上那趟列車前往固豐市,走遍固豐的每個(gè)角落,卻始終沒(méi)有再遇見(jiàn)她。
從側(cè)面看,她謹(jǐn)慎地向周邊張望著,與當(dāng)初一樣纖弱的身影逐漸重合。忽地車身抖動(dòng)起來(lái),紅燈變綠,我急不可耐地走到車門前,望著逐漸遠(yuǎn)去的倪華,我心急如焚,在最近的站牌沖下了車。我恨那把傘,它阻隔了我的視線。雨水砸在我的面頰,冰冷的雨瞬間讓我清醒過(guò)來(lái),我看清自己手上的細(xì)紋,才驚覺(jué)倪華此時(shí)早已不是當(dāng)年的少女。
我與她之間,第一次見(jiàn)面便是最后一面,一轉(zhuǎn)眼二十年了。我已有女友,卻始終沒(méi)有結(jié)婚,我不知道我在猶豫什么,是因?yàn)槟呷A嗎?好像并無(wú)干系,這么多年過(guò)去,她的容顏早已變得模糊,像半透明的雨水,讓我始終看不清。我早就應(yīng)該忘記她了,她不過(guò)是我漫長(zhǎng)人生道路上匆匆遇見(jiàn)的人。我從沒(méi)有做好相遇的準(zhǔn)備,卻始終做好了離別的準(zhǔn)備。
天下之大,也許終其一生我們都不會(huì)再相遇,即便相遇了我是否還能認(rèn)出她呢?我不知道。我總幻想著在某一個(gè)黃昏時(shí)踩著溫綿的雨水,走向她。我看不清她的容顏,在夢(mèng)里,無(wú)論是睡夢(mèng)還是白日夢(mèng)。記憶里,她仍是個(gè)怯懦的少女,年輕溫婉,而今,也許她早已變成一個(gè)婦人,甚至是一個(gè)孩子的母親。剛剛那個(gè)女子,還保留著她二十歲的樣子,直至半透明的雨水將她變得模糊。
空想中,我竟已徒步走到了公寓門前,我恍惚地走進(jìn)門。在白熾燈下,我看到了女友臉上的擔(dān)憂。她溫柔地拿著毛巾為我擦拭著早已濕透的頭發(fā),問(wèn)我何故歸家這樣遲,我哂然一笑說(shuō)道:“雨水蒙蒙,一時(shí)竟坐錯(cuò)了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