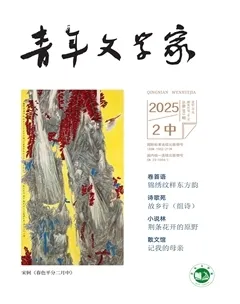矗立于心的小樓
每次從位于鎮中心的老學校操場經過時,我總是要向操場最西頭遙望。可是我知道無論我怎樣凝望,那棟兩層小樓都不會重現,那是我到蘇州后一家人所住的地方。那是一棟陳舊的小樓,但細想一下竟然發現,它是除了我出生的老屋外我待得最長時間的屋子。這就注定了它在我的人生記憶中一定會占據一定的比重,就像那陳年佳釀一樣,年份上去了,酒香自會濃烈。
我仍記得十幾年前第一次到這所學校的情景。當我拎著行李,跟著招聘我過來的陳偉華校長來到它的面前時,我竟愣在那兒。那時是2010年,我們進入21世紀已經有10年了。我在老家縣城剛購置了一套120平方米的新商品房,也剛剛將它裝修好。現在,我卻有一種穿越時空回到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感覺,因為我面前這棟兩層樓房就是那個年代的建筑,沒有特殊情況它的年齡肯定比我大。它的東側臨近操場的墻壁上竟然還有富有年代特征的標語“為學生終身發展奠定基礎,為教師施展才華創建平臺”,墻壁上的石灰也已經斑駁了。陳校長領我打開樓下的一間屋子,樓下共三間,最東側臨近操場的一間作為體育器材室,西側靠近廁所的一間暫時空置,中間的就是我的宿舍了。推開門,屋內還算整潔,有一張床和一張老式的辦公桌。陳校長有些抱歉地說:“房子有些破舊,先委屈些!”我趕緊說:“謝謝陳校長關心!”雖說對宿舍的環境不是很滿意,但我也深知在蘇南這個寸土寸金的地方有一個暫時的棲身之所已屬不易,哪還能挑三揀四。就這樣,我和小樓的緣分結下了。小樓雖已經陳舊,但并不寂寞,除了我和另一位同年被招聘過來的熱情、誠懇的蘇北老鄉繆海峰外,它還有一位房客是早我們一年來的體育老師馬騰,是剛畢業的南師大的高才生,一位帥氣、陽光的小伙子。他和繆海峰住在樓上。小樓在2010年的開學期因為我們的到來而熱鬧起來。不久之后,隨著我妻子、母親和四個月大的兒子的加入,小樓變得更加熱鬧。我把另一間閑置的屋子也收拾出來,這樣我就有了兩居室。而我們一家人就在這棟小樓里正式落戶。
然而不久之后我們在小樓里便有了一次令人啼笑皆非的經歷。一天晚上,我和妻子在小屋里用浴帳給四個月大的兒子洗澡。浴帳是新買的,密封效果很好。我和妻子忙了一身大汗,幫兒子洗好了澡,然后把他抱到床上。這時我俯身看兒子,卻發現他呼吸似乎很微弱,加上當時屋內光線暗,我對妻子說,兒子的嘴唇好像有些發青。頓時,妻子緊張起來。我趕緊叫了樓上的繆海峰和馬騰幫忙。那時還沒有電瓶車,他們兩個迅速下樓和我們一起抱了孩子往醫院跑。在瀏沽涇橋那里,馬騰攔了一個陌生人的電瓶車要送孩子去醫院。那人聽說我們是學校老師,二話沒說就把車子借給了馬騰。然后我抱著兒子坐在車子的后面,馬騰騎著電瓶車,沿著瀏沽涇河邊那條坎坷不平的小路一路狂馳,妻子和繆海峰在后面追。這時我隱約聽到懷里的兒子有了鼾聲,心里稍安些,但又怕他睡著了會出事,就不斷地叫他。就這樣,一會兒的工夫,我們到了醫院。妻子和繆海峰很快也趕到了。因為跑得太急,也太緊張了,妻子在急診室的大廳里一屁股就坐在地上,號啕大喊:“醫生啊,你救救我孩子啊!求求你啊!”醫生看這陣勢,以為是出了什么大事,幾個護士趕緊過來從我手里接過兒子,詢問我們是什么情況,有人扶起了妻子。我們把情況說了一下,護士趕緊叫我們去買氧氣面罩吸氧,然后把兒子抱到搶救室,讓他躺在小床上。等我把氧氣面罩買來的時候,護士指著正在酣眠的兒子對我們說:“孩子不挺好的嗎?沒什么問題啊!你們這么緊張干什么啊?”我和妻子面面相覷,然后尷尬地笑了。一旁的馬騰和繆海峰這時才松了一口氣,說:“沒事就好,沒事就好!”這事已經過去十幾年了,然而現在想起來依然有一種如飲熱茶般暖心暖肺的感覺。這是獨屬于小樓賜予我的異鄉的溫馨。
第一眼看到小樓時,我猶如看到一位風燭殘年的老人在秋風中瑟縮著身體。再加上那時正是開學前幾天,周圍環境空曠,我想這里一定會很冷清,可是過了幾天我就知道自己大錯特錯了。小樓的旁邊有一個操場,這個操場在白天上課期間,學生自然是少不了的。這些熊孩子甚至在體育課的自由活動期間都會到小樓這兒來,有的還敢躥到樓上。到了傍晚,學生雖然放學回家了,但是這里的人并沒有減少,都是鎮上的居民。這時我才知道,這里是鎮上居民們的傳統鍛煉場所,打籃球的、溜冰的、練太極拳的、跑步的,不一而足,操場上到處都是人,甚至到了深夜,還有三三兩兩散步的。
原來小樓并不孤獨啊!
我對小樓的淺薄認知還遠不止這些,這位滄桑的老人可有著極為豐富的閱歷。它的前身也不僅僅是吳縣中學老師的宿舍樓,它曾經還是一所幼兒園,是吳縣中學的附屬幼兒園。這是一所幼兒園,看著它現在破舊的樣子確實是不容易想到,但其實我第一天進來時就有這個感覺了,因為我住的那兩間屋子里竟然畫滿了壁畫,那些畫逼真得讓人嘆為觀止。無疑,這棟樓作為幼兒園已經是多少年前的事了,但是墻壁上的這些畫卻沒有由于年代久遠而變得斑駁不清,雖然不是那么鮮亮,但仍然無法掩住它的生動精彩,就像一位精神矍鑠的老人,面對夕陽依然精神抖擻、神采奕奕。在我床頭的墻壁上畫的是一位大樹爺爺,樹冠上是幾只小鳥在快樂地鳴叫。在對面墻上有一只正在低頭吃草的黃底黑點的梅花鹿,這只梅花鹿已經被我母親和兒子的照片給永久截留了。上方靠近屋頂樓板處是一個長著白胡子的紅色太陽公公,旁邊是一只招手示意的青蛙王子和在壞笑著的蘑菇小妹。在墻的北面窗戶兩側還有兩位長者,一位是穿著西裝的山羊公公,另一位是穿著背帶褲的大象伯伯。在這樣生動活潑的童話世界里當然不能少了孩子,在屋頂上方則畫的是一個乘坐著宇宙飛船的小孩子正在俯瞰著大千世界。這就是我所住的那間陋室內的畫的內容,自然、美好、夢幻、童趣盎然。它伴隨著我兒子的整個童年,承包了我們一家數年的歲月。毋庸置疑,它一定是孩子夢境的重要底色,因為它本是為了伴隨孩子們的童年而生,盡管屋子的功能后來由幼兒園轉變為了職工宿舍,但幸運的是,它依然是我們童真歲月的最后一站,滋養了我們的心靈。
操場附近像我所住的這樣的小樓有好幾棟,它們就像人一樣已走過人生中最輝煌的歲月,現在都垂垂老矣。不過如果你因此而輕視它,那一定就錯了。離我所住的小樓六十米左右有一棟建筑,它不是樓房,但卻有不亞于樓房的高度,而且很長,有大概六七十米,它的窗戶也特別高、特別大,門前長著一排排的樹,每棵樹都有兩人合抱那么粗。這棟建筑當時是體育館,可以打羽毛球、籃球。里面空蕩蕩的,因為特別高的原因,所以人站在里面,仰頭看頗有一種身處荒原之感。然而,這棟始建于20世紀70年代的建筑,曾有個非常豪橫的稱呼—“全國最大的中學宿舍”。大到什么程度呢?最多時大約有一百多名學生住在里面,一間宿舍一百多號人,不要說那時候,即使現在恐怕在全國也是第一。一百多名學生齊聚一堂,那場面絕對壯觀,十幾個人的宿舍,就已經是亂成一鍋粥了,現在十幾倍的人數,大概對面說話都得對著耳朵吼吧,當然最頭疼的應屬看宿舍的老師吧。
不過我想這體育館被改成男生宿舍,應該只是暫時的。因為1985年,在這棟建筑的東面50米左右處又建了一棟正規的男生宿舍樓,共五層,但這棟樓在我搬過來時就已經廢棄不用了,因為原先的吳縣中學已經搬走,現在的滸關中學沒有住宿生,自然也就不需要宿舍樓了。我當時還想住進去,后來學校領導說里面水、電都沒有了,不方便,便作罷了。那棟五層的宿舍樓因為它的高度在周圍的建筑中顯得格格不入,仿佛也在彰顯著它不同的身份。不久后,這棟宿舍被拆除時,吸引了無數人的目光,因為它有太多的鋼筋,拆除時,施工隊噼里啪啦地用挖掘機竟然砸了好長時間,讓包工頭狠賺了一筆。圍觀的人發著感慨:“那個時代的人們不偷工減料,實誠。”這時知道內情的人說:“你們不知道這棟樓是花了大價錢的,花錢的單位還不是吳縣中學,而是一個有錢的單位—中國高嶺土公司。”我們這才知道,在1985年,觀山駕校邊上的中國高嶺土公司職工子弟學校關閉,初中學生全部進入吳縣中學就讀。作為交換,高嶺土公司以捐助名義為學校建了這棟宿舍樓,那是一個有錢的單位,更何況是為了自己的孩子上學,自然不會偷工減料。這是我到滸關后見的第一棟拆的小樓,一時還覺得新鮮,后來整個老鎮都成了一個大的拆遷場,每天都響徹著刺耳的砸鋼筋聲,包括我所在的學校也在不斷地被拆,很多熟悉的建筑漸漸地消失在煙塵中,隨同消散的,還有那些刻在這些建筑身上的諸多印記。對此,人們或許已習以為常,但內心卻不由自主地涌起一股煩躁與惘然。
日子如水一般平淡而悄然。在不知不覺中,我住的小樓仿佛在一夜之間變得衰老了,那個時候整棟樓已經只有我們一家人了。小樓似乎有些冷清了,繆海峰調到實驗高中好幾年了,馬騰也早搬到自己的新房子里去了。我和妻子則搬到樓上原來馬騰的房間,因為那里可以裝空調。我們買了一臺空調,那經年腐朽的磚墻讓裝空調的師傅頗費了一番功夫。裝上空調后,懷孕的妻子便少受些許酷熱之苦。到了蘇州五年后,年近不惑的妻子懷了第二胎,小樓即將迎來又一位小房客。某一天夜里,突然樓上發生一聲巨響。第二天,我四處查看,發現樓上東邊的一間屋頂已經坍塌。抬頭一看,小瓦和屋梁部分墜落在地面上,還有一些懸掛在空中,隨時也會掉下來,地面上到處散落著瓦片。我把殘破的門關閉,想用鐵絲把門扭緊,但那門年久失修,已經無法關緊,只得囑咐家人不要進來,防止被砸傷。這時候它外墻的石灰也已大片大片地剝落,就像一個老人滿臉皺紋一樣。屋頂是江南小樓特有的小瓦,這時從遠處看已經是高低不平,坍陷的部分也很明顯。又一個刮風的夏天,小樓邊上的廁所屋頂開始坍陷,先是南面一間,再是北面一間。沒有了廁所,我們的生活會受到極大的影響。于是,我到建筑工地上扛來了一塊做活動板房的泡沫板,把它塞到屋梁上,這樣,即使有瓦片掉下來了,也不會砸到人。還別說,一直到我們離開,都沒有發生瓦片砸落的情況。不知是不是冥冥之中約好了一樣,也或者學校的這些建筑都是同氣連枝的原因,學校北邊的一棟教學樓也發生一聲巨響。雖然那棟樓是新建的,但是這不明原因的聲響還是讓學校領導感到很緊張。于是學校領導就決定把那一屆的初一學生全部拉到小學去了。由此,學校以及周邊拉開了拆遷的大幕,先是操場邊上的學生宿舍樓被拆除,緊接著是以前做浴室的配套用房,隨后是有問題的那棟教學樓,最后是原屬于吳縣中學的教師宿舍樓。一棟棟樓房在煙塵中轟然倒塌,運河邊那些獨具特色的粉墻黛瓦、木質排門的兩層小樓,以及小巷里那些不知歷經了多少歲月的低矮小屋,都逐一消失了。但奇怪的是,學校內有一棟早已經廢棄不用的四層小樓,卻一直矗立在那里。這棟小樓,就在學校最前面的教學樓的旁邊,外墻上綴滿了爬山虎,已是殘破不堪,周圍由鐵柵欄圍成一個小院。我曾經多次想進去探幽尋勝,結果連進去的路都沒找到,只能懷著一種莫名的敬畏遠遠地看著它。這棟小樓最終也沒有被拆遷。后來我才知道,這也是一棟有歷史的建筑,這棟三層的青磚樓建于“民國”時期,它的原主人是原國民黨南京兵工署主任童致咸。這棟小樓20世紀80年代曾作為滸墅關派出所的駐地,后來按國家政策歸還給童家后人,但后來童家后人又把它捐給政府,在之后很長一段時間是作為吳縣中學的教師宿舍的。這些沉默的建筑無意中見證了歷史的興亡更替。
那一年,在小樓的那間裝空調的房間里,我的女兒出生了。那一天的下午,我陪著妻子在操場散步,還在計算著日子,結果當天晚上羊水就破了,女兒著急出來過中秋了。想當年在老家時,我和妻子為兒子的出生費盡了周折,而這次一切都那么風平浪靜,妻子甚至一直工作到臨盆,中途還在操場上摔了一跤,這讓我不得不感嘆這江南的風水就是好啊。后來,還有老師總結說我們學校的老師都生了一兒一女,還有人說這學校原來是龍華寺,是塊福地、善地。雖說有牽強附會之嫌,但看來冥冥之中,這些拆了的和沒有拆了的小樓也許都在庇護著這里的人們吧,當然也包括我們一家。女兒出生了,然而她并沒有像我兒子那樣幸運地擁有一個有著一大片操場的童年,因為我們所住的這棟樓房突然變得那么不宜居了,那個夏天,無數白蛉日夜不停地往我們住的地方爬,原因大概和房頂的坍塌以及周圍房子的搬遷有關系吧。我特意找了生石灰撒在房前屋后,可即便如此,也無法阻止它們的瘋狂入侵。后來,在枕頭下發現一只蜷曲的大蜈蚣之后,我決定舉家搬遷到新房子。彼時我的新房子已裝修好,但還不滿半年,幸好當時從環保考慮并沒有使用太多的木板。但搬家還是遭到母親和妻子的反對,妻子認為新房子有甲醛,母親覺得還是這里方便。是的,住了五六年的地方當然是習慣了,也有感情了,更何況這里門前就是廣闊的操場,人來人往很熱鬧。到了新房子就會整日待在樓上,自然憋悶。最后我們決定先搬走部分東西,晚上還過來睡覺。然而就在我們搬走部分東西的第二天,樓上房間里新置的桌凳和沙發椅,以及廚房所需的微波爐、電磁爐、插座都被洗劫一空。我們趕緊報案,派出所的警察備了案。但是,偷竊仍在繼續,我們樓道間有一個鋁合金的伸縮門,也被人硬生生用鐵棒撬開,把房間里的電線和鋁合金窗戶都拆走了。這時我們才意識到這是一群拾荒者所為。這些人像蝗蟲一樣,憑著他們獨特的嗅覺,瞅準我們不在這兒的時間,進行“合理合法”的行竊,因為他們自稱“拾荒”。我們在小樓的東西已經再無保障,五六年來,我們門有時候都可以不關,可是現在關上門的鎖都被他們生生撬開,我們嚇得趕緊連夜搬運重要的物品。一天,我母親在操場上看到三個五大三粗的男子,用三輛三輪車把小樓能拆的全部拆走了,我母親跟在后面追,他們早就飛也似的逃走了。
就這樣,我們被迫離開了小樓,沒有舉行任何莊重的告別儀式。我們就像那些在蝗災中急于搶救莊稼的農民一樣,在一個天色陰沉的黃昏,回望那座已變得滿目瘡痍的小樓,用借來的板車裝載著最后一批生活用品匆匆離開,心中那種如同與母體割舍般的痛苦讓我忍不住淚流滿面。
我以這樣的極為尷尬的方式離開這座頗有歷史的運河小樓,搬進了另一棟運河大樓。我在這座城市真正安了家,一家人生活在現代化的居住環境里。可是,我仍然無比想念著那一棟棟運河邊的小樓,它們在喧囂中終于安靜下來。也許有一天,它們終會消失,但那些它們曾經承載的記憶不會。因為它們曾經像一枚圖章一樣,清晰地在這塊土地上蓋上鮮紅的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