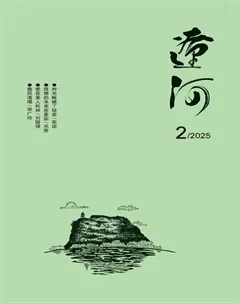家園守望與文化鄉愁
近年,“新山鄉巨變”主題創作如火如荼,但似乎也面臨不同層次的藝術困局。突破已有作品,彰顯藝術個性,成為每個作家的創作訴求。
曲子清在這方面做出了努力和嘗試,她的長篇小說《冰陷湖》(春風文藝出版社2024年出版)以村黨支部書記黃巧云為核心,書寫在鄉村振興中遼河濕地坎村綜合治理所取得的成就。以黃老歪為代表的老一輩坎村人,以巧云、向陽、一丁、二丫、向東、金貴為代表的年輕一代的“歸鄉人”與“在鄉人”,在鄉村振興治理過程中都做出巨大貢獻,但也呈現不同面向。尤其是黃家六代守護冰陷湖的犧牲精神以及村民對冰陷湖的復雜情感,流淌在文本中凝結成揮之不去的意緒。
作者承繼現代鄉土書寫、國民性批判的歷史傳統,致敬經典作家;同時更新文學觀念和審美意識,開啟“后知青”寫作。小說聚焦鄉村發展史的高光時刻——從創業史、改革史到振興史的多彩畫卷,輔之以富有意味的龍門渡傳說、冰陷湖意象和鯉魚夢境,表現出新時代鄉村美學實踐的特有品質——執著的家園守望與濃厚的文化鄉愁。
一、文學史視域中的文化傳承與觀念更新
以文學史視域觀照,我們發現《冰陷湖》從三個方面與文學傳統保持關聯。一是小說寫美麗鄉村建設,雖然作者在主觀上可能未有寫史意識,但從客觀上來說,小說為我們提供鄉村發展史上重要的一環——從柳青開始的農民“創業史”,高曉聲《陳奐生上城》、賈平凹《臘月·正月》《浮躁》等展現的農村改革史,到當下的鄉村振興史,彰顯知識分子寫作的責任與擔當。
二是作為主題創作,作者并沒有回避美麗鄉村建設中的諸多矛盾,《冰陷湖》真實地反映了社會現實、人物心理和國民性,讓我們看到其與魯迅、蕭紅、高曉聲等鄉土寫作中含蘊的國民性批判的精神傳承。
三是放在知青文學的角度上,小說中的喬姍是知青,主人公巧云是知青的后代。作者更新文學創作觀念,打破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梁曉聲《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史鐵生《我的遙遠的清平灣》、葉辛《孽債》等知青文學樣貌,為我們呈現出“后知青”文學的美學品格。
作者自覺不自覺地續接現代以來的文學傳統,站在新時代的起點上,創構屬于自己的鄉村美學實踐。
二、鄉村振興的力度與矛盾的多重設置
《冰陷湖》的鄉村美學實踐,富有濃厚的生態意識和文化意味。
小說描寫了坎村的空間地理環境:它是非常偏僻的、邊緣的、泥濘的,在他人的眼中它就是一個“爛泥包”。但在坎村人眼里,冰陷湖有它特有的美麗。
作品以村黨支部書記巧云所推進的三大工程——疏浚擴容、雨污分離以及村容村貌整治等,展現新時代鄉村的嶄新面貌。
小說不僅寫到鄉村的外在之美,也寫出鄉村真正的內在之美,一代又一代坎村人為建設家鄉做出自己的努力,龍門渡文化公園、旅游文化、稻香鴨等美食文化彰顯著文化的力量,塑造著內外統一的美麗鄉村形象。
從“爛泥包”到美麗鄉村,小說設置多重矛盾,突出美麗鄉村建設的難度和力度。在巧云的周圍,存在各種各樣的矛盾網絡,其復雜性猶如柳青的《創業史》。
一是巧云與高占福、高寶財父子等人之間的矛盾關系。高占福是老一代書記,有自己的權威性,父子二人或明或暗阻撓巧云的工作推進。
二是巧云與養父黃老歪的關系。這讓讀者自然聯想到《創業史》中梁生寶和養父梁三老漢之間的關系。黃老歪一家六代守護冰陷湖,祖先湖葬于此,這里有祖先的靈魂,所以冰陷湖疏浚清污的工程方案,父女二人很難達成一致。
三是在巧云的周圍有村民、巡查組以及和她構成情感關系的人物,一丁、向陽等。
四是從成長小說的角度上看,還有嚴鎮長等對巧云的關心和引導。從市里、縣里,到鎮里、村里、家里各個層面的人和事,環繞在巧云周圍,構成非常復雜的矛盾關系,可見坎村建設的艱難。這也從不同視角寫出立體的成長中的巧云形象。
《冰陷湖》所呈現的不僅僅是物質上的,而更是一種文化上的、精神上的振興史。在矛盾設置上,還有作者更精心考慮的方面,其中的“流言文化”(圍繞在巧云周圍的猜忌、嘲笑、刁難、詆毀等)構成了對國民性非常重要的文化場景展示,和《呼蘭河傳》有異曲同工之高妙。
三、湖的品性與家園守望的精神同構
作者始終以“冰陷湖”為核心展開情節,蘊含豐富的情感結構,顯示出湖的品性與家園守望的精神同構。在黃老歪眼里,湖從不反駁、從不抱怨。他和湖具有一樣的品性,他家六代人守護湖。他有守湖的孤寂,也有和湖一樣渾厚的包容的心胸。守護湖,就是守望自己的家園。
老一代人和湖有著天然的情感聯系,高占福、葉瞎子等無不如此。葉瞎子得知自己妻子的風流韻事后,只有在湖里才自由自在,感受到湖對他精神上的撫慰。
湖的品性,對于老一代人是生命的包容和精神的撫慰,是上善。那么青年人和湖之間有什么樣的內在關聯?
巧云、向陽、一丁,他們是屬于“歸去來”一類的青年人。起初,巧云歸來是服從養父黃老歪的意志,后來逐漸轉變為自己的意愿,主動投入鄉村建設之中,鯉魚夢境表現出她在內外沖突中的復雜心境。因為和巧云的情感關系,向陽、一丁歸來,而后他們逐漸轉化為與冰陷湖不可分割的情感關聯,為坎村建設出謀劃策。
與“歸去來”相對應的是青年人向東和二丫,他們一直堅守在農村的大地上,是“在鄉人”。高寶財的形象比較復雜,他是離開而未歸來者,小說并沒有丑化他,而是揭示出他對坎村的真情。坎村是坎村人的根。
無論是老一代還是新一代,坎村連著他們的根脈,冰陷湖是他們的家園所在。冰陷湖養育一代又一代坎村人,湖的品性與家園守望的精神同構。但“湖”“水”不僅僅是表現對象,更是一種內在的氣質和節奏,成為具有深刻內涵的意象。蘆湖—冰陷湖—龍門渡—受氣湖—標志湖—文化湖,名稱變化和情節推進緊密相連,和坎村人命運息息相關。湖水塑造坎村人的生命意志,流動著代代坎村人的精神血脈,承載著坎村人的文化鄉愁。
四、文化鄉愁的底色與美學呈現的成色
文化鄉愁,與黃老歪獨特的形象相關。黃老歪最后撐船沉湖而去,這一結局符合他的內在性格,也是作者的精心設計,這是小說寫得最精彩的段落。
如果說巧云、向東、一丁回歸鄉村的行為,先是一種外在情感召喚,逐漸內化為一種再生動力,那么,黃老歪一家六代守望家園,而后他自身湖葬而獻祭,則是他一生的宿命,是他主動的、執著的唯一選擇。他與湖、與他守護的先人成為一體。當疏浚、清污湖水被放干之后,他深感龍脈被驚,產生了自己愧對祖先的有罪意識,他沒有辦法面對。同時,對巧云他不能不支持,不能去反對在風口浪尖上的巧云。父親的獻祭也想為女兒、村民“贖罪”,這就是“生祭”。
湖葬,受到現代生態文明的沖擊,從難以為繼到不能為繼,黃老歪別無選擇。黃老歪的離去,是一種終結,也是一種告別。雖然有無奈、不舍,卻也是必然。《冰陷湖》中石房子的倒塌,猶如沈從文《邊城》白塔坍塌一樣的隱喻。
黃老歪的主動“獻祭”和“贖罪”讓我們看到另一種文化鄉愁,它古老,是挽歌,是承諾,也是拯救和新生,因而《冰陷湖》也是頌歌。
與這種文化鄉愁相適應,小說在美學呈現上更耐人尋味。這篇小說具有雙重結構:一重結構是美麗鄉村建設,另一重結構是文化鄉愁。透過這鄉愁可以看到傳統與現代的沖突,黃老歪的形象具有悲劇的意味。
小說以畫面疊加和風景話語營造、內外沖突與夢境建構、象征意象創造與詩化語言運用等方面,表現出鄉愁的豐富性和復雜性。這反映出作者的復雜心緒,是傳統的鄉愁與現代的鄉愁的矛盾體——對當下無法擁有的某些失去的東西的渴望,又是對它某些不變東西的憂慮,充滿藝術的張力。
作為“新山鄉巨變”主題創作,《冰陷湖》尊重歷史發展邏輯和人物性格邏輯,描寫新時代回鄉青年、在鄉青年帶領全村人進行美麗鄉村建設,譜寫了新中國農民創業史—改革史—振興史的新篇章。作者努力打破創作格局,于家園守望和文化鄉愁中進行一次別致的鄉村美學實踐,為讀者帶來全新的審美體驗。其時代觀照和文化思考具有深刻的歷史穿透力,是“新山鄉巨變”的重要收獲。
作者簡介:吳玉杰" 遼寧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