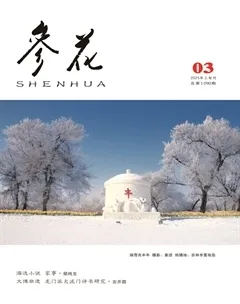木炭物語
1
當湘南千山紅遍層林盡染,豐收后曬干的五谷已在倉庫里安眠。此時,秋高氣爽,云淡風輕。麻雀在收割后空寂的稻田上空時起時落,勾勒出一幅寂靜的人間畫卷。忙碌了大半年的農(nóng)人可以歇息了。可農(nóng)人又是閑不住的,別看他們平時累得齜牙咧嘴,恨不得到了秋冬季節(jié)睡個天昏地暗。可習慣了長年累月勞作的他們,如果不做點事兒,總感覺缺了點什么。在農(nóng)村,一家老小的生活,都離不開柴火。打柴是農(nóng)民過日子的大事,秋收之后,趁著這時節(jié)上山砍柴以備過冬,是他們的首要選擇。而燒炭,更是一舉兩得的事情。
2
柴刀在刀閘里藏身,爺爺背著刀閘在前面帶路。刀閘隨著爺爺前進的腳步有規(guī)律地搖晃,形成固定的節(jié)拍。刀閘,其實就是一截橫向掏空的硬質木料,將掏空的部位設計得足夠狹窄,僅能容納刀身,而刀柄過于粗大無法深入,從而固定刀身。農(nóng)人又在刀閘的兩端用鉆頭各鉆一個孔,在孔里穿上結實的繩子,將繩子調整到合適長度,使其像單肩書包一樣斜挎于肩上,從而解放雙手。
打工的浪潮將青壯年都卷到了城里,留守的老人與兒童相互依靠。由于父母常年在外打工,我和哥哥跟隨爺爺奶奶生活。做些力所能及的農(nóng)活兒,是農(nóng)村孩子與生俱來的自覺。我提著水瓶,哥哥握著一把矛鐮,跟著爺爺往山里走去。選取炭柴是有講究的:粗細是首選,一般以手腕粗細為準;質地堅硬是第二選擇,質地疏松的木柴在碳化的過程中會化為齏粉。燒炭需要的大型硬質炭柴,在山林深處,在云海深處。
展現(xiàn)在我們面前的是一片枝丫密匝的森林,那里便是爺爺?shù)呢熑紊健M矍暗牧帜荆瑺敔斖O履_步,對我們說,到了。他將柴刀依次從刀閘中取出,給我們兄弟分別遞上一把,又將空蕩蕩的刀閘掛在樹枝上,對我們說,可以開工了。
柴刀被爺爺磨得鋒利,然而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空氣氧化,原本能映出人影的刀面有了一層淡淡的黃銹。爺爺蹲在一棵雜木前,右手高舉,刀鋒揚起,與爺爺?shù)念^部同高。在臂膀的帶動下,柴刀劃過空氣落在雜木貼近地面的根部。刀身陷入樹身,爺爺拔出刀子,又補一刀。隨著木屑橫飛,一根手腕粗細的雜木斷作兩截。爺爺扶在樹干上的左手輕輕一撥,雜木無力地倒了下去。
我和哥哥學著爺爺?shù)臉幼娱_始砍柴。爺爺一邊忙活,一邊對我們說:你們要注意安全,左手不要扶得太低,容易傷到手。看我們挨得太近,他又說:你們分開點,刀子不長眼。我們應聲拉開了距離,嘴里答道:經(jīng)常砍柴,知道的。
當我在一棵茶樹上砍下一刀后,看到這一情景的爺爺驚叫起來:快住手,你這是干什么?他放下手頭的活兒朝我這邊奔過來。我說:爺爺,我在砍炭柴哩,您不是說,多砍質地堅硬的木柴嗎?爺爺笑著說:你這個傻孩子。燒炭是為了取暖,也是為了賣錢。然而,茶樹是寶,我們每年還要上山揀茶籽,回家榨茶油。你把茶樹砍了,以后哪有茶籽?沒有茶籽,就沒有茶油。茶籽比炭還要寶貴。爺爺看著茶樹被砍了一刀后裸露在空氣中的米黃色木質部位心疼不已。我恍然大悟:有價值的茶樹要像寶貝一樣呵護著。
爺爺怕我們兄弟再次砍錯了炭柴,又交代一番說:燒制木炭需要新砍伐的炭柴,曬干的柴是不能燒炭的。只有材質堅硬且還有水分的木柴燒出來的炭才耐燒、有重量、有賣相。松木和杉木是不適合燒木炭的,它們價格昂貴且木質疏松;茶樹質地堅硬,卻因為可以結茶籽榨油,燒炭不劃算。燒炭,最好是用質地堅硬的山毛櫸。
山毛櫸是湘南山林常見的樹,它們軀干筆直,且質地堅硬。曬干后的山毛櫸堅硬無比,能把刀砍到卷刃。這種質地堅硬的樹生長較慢,就算沒人砍伐,能長到碗口粗,已經(jīng)是同類中出類拔萃的存在。這種樹木盡管有著挺拔的軀干,卻不能打造家具,只能成為灶臺的柴火,或者成為燒炭的首選對象。
在我們爺孫三人的努力下,刀砍雜木的聲音在山林里此起彼伏。雜木像秋天被冰雹打倒的稻谷,很快就倒下一大片。爺爺砍伐是有講究的,他只砍伐手腕粗細以及更粗壯的雜木,尚未長成的雜木無論如何得留著。他懂得不能涸澤而漁的道理。
在山林中,生長著一種叫作刺木藤的植物,它的名字雖然帶有“藤”字,卻不是藤蔓植物,而是可以直插藍天的雜木。如果沒有人去砍伐,它們也是可以長到碗口粗的。這種植物橫向生長得極其緩慢,但這并不影響它們追求高度,在軀干部位只有拇指粗時,卻能長到一米五甚至更高。刺木藤有著極強的韌性,用力扭曲,能打成結而不斷裂,這種屬性與藤蔓植物頗為相似。這特殊的屬性,讓刺木藤難以自由長大,它將成為捆柴的最佳工具。爺爺看到刺木藤,都會順帶一起砍下,放置一旁待用。
大片倒地的雜木四處散布,嚴重影響行走,爺爺便開始下一道工序。他放下柴刀,拾起矛鐮。那是一種半月牙形的刀具,刀口鋒利。燒炭需要較大的木料,然而那些小枝丫也是不能浪費的,它們將作為柴塞進灶膛。爺爺用左手握住雜木的軀干部位,右手握住矛鐮沿著軀干一路劈下,枝丫便紛紛與軀干分離,雜亂無章地躺在地上。待到劈砍結束,爺爺才拿來刺木藤將炭柴與枝丫分別捆成捆。
深秋的湘南早已有了涼意,然而在勞動的作用下,我們絲毫不覺得寒冷。彎腰砍柴久了,身子有了些許的疲憊,爺爺就安排我們喝水、歇息。利用這間隙,他會給我們講故事。聽完故事,我們再次投入工作。其實,于燒炭來說,最辛苦的工作不是砍柴,背柴才是巨大的工程。砍伐的炭柴不會長著腳走到窯邊,我們也沒有諸葛亮的天縱之才制造木馬牛車。這一切,全部靠人力來完成。爺爺背著沉重的炭柴,我們兄弟或背或抬,成為爺爺?shù)男褪帧>d延的山路,漫長的煎熬,沉重的柴壓在稚嫩的肩膀上,有著難以言說的沉重。時間久了,還有鉆心的疼,火辣辣的。掀開衣服,肩頭紅通通的。回家之路顯得尤為漫長,甚至難以企及。
陽光透過云朵的間隙灑向人間,透過樹葉的縫隙落在地上,形成點點圓斑。我們沉默著,一步一步地往山下挪去。累極了,就躺在山林間滿地的落葉上,摘一根草莖放在嘴里咀嚼,看天上流云飛渡。等緩過勁來,又繼續(xù)前行。我們不會撒嬌,也不會跟爺爺提出回家休息的請求。在農(nóng)村生活,我們親眼看見了爺爺奶奶的艱辛,知道一粥一飯來之不易。我們的心中,種下了一顆責任的種子,它在日積月累中茁壯成長。爺爺愛憐地看著我們辛苦的樣子,卻又無可奈何,偶爾說一句,以后好好讀書,做農(nóng)民實在是太苦了。
在我的心中,就有了無限遐想——有一道光,穿過幽微的間隙,透進心中。
3
炭柴扛到指定地點后,接下來的工作就是截斷它們。數(shù)米長的炭柴是無法直接放入窯洞的,截斷就成了必要工作。根據(jù)炭柴的大小,選擇砍還是鋸是農(nóng)人要思考的問題。比手腕細的炭柴,直接將其底部立于地上,目測所取的長度,砍上一刀,再旋轉一百八十度,補一刀,炭柴就斷作兩截了。炭柴難免會有不夠長的時候。在炭窯的角落里,這些長短不一的邊角料就有了用武之地。面對粗壯如大腿的炭柴,刀砍的效率是低下的,這時就需要用到木馬。那是一種由三根木頭固定形成的工具,兩木交叉,在上端形成一個小小的夾角,再用一根木頭穿過交叉點,三根木頭就固定成了木馬。架上兩個木馬,將炭柴的兩端放入小小的夾角,拉動鋸條,炭柴也不會滑動。爺爺目測好炭柴的長度,將要鋸的部分置于木馬之外,再用左腳壓住炭柴。他右手拉鋸,鋸齒鋒利,在炭柴上來回穿梭,木屑紛紛揚揚,如下起了一場小雪。很快,一截炭柴就斷開了。爺爺再次移動炭柴,周而復始地鋸下去。這是一項枯燥乏味的工作,可爺爺把它當成了藝術創(chuàng)作,他用心做好每一個步驟,欣賞著自己的勞動成果。我和哥哥忙前忙后,把爺爺鋸好的炭柴整齊地碼好,看著越堆越高的柴垛子,疲憊之余成就感油然而生。
炭窯是燒炭必不可少的。炭窯有土窯、磚窯、水泥窯等多種類型。磚窯與水泥窯造價高。在農(nóng)村,最常見的還是土窯,畢竟,土在農(nóng)村無處不在。制作土窯,首先,土窯的選址是有要求的,要有平整的地面,便于加工和存放炭柴,取窯后,也好放置和運輸木炭;其次,土窯的土壤要堅實,最好是黏土;最后才是水源,取窯的時候,窯內溫度極高,如果窯內的火還沒有熄滅,一旦開啟窯口,火勢會迅速增大,此時,水就成了必不可少之物。
制窯開始了。在離家不遠的山坡上,當爺爺用鋤頭勾勒出一個直徑兩米的圓形輪廓時,我才知道這是一塊制窯的寶地。挖開植被,展現(xiàn)在我們眼前的是質地結實的黃土。黃土性黏,不松散,掘成的窯洞十分穩(wěn)固。鋤頭、鐵鍬這些事先準備妥當?shù)墓ぞ咴跔敔斒掷锝惶婀ぷ髦P绿扛G從一個圓形開口,到一寸寸地往里吃進,再一點點拓寬,直到挖出炭化室的雛形,爺爺才開始往外面掏泥。我和哥哥拿著撮箕搬運泥土,累了,就休息一會兒。說來也怪,一休息,我就精神十足了,跳進爺爺挖掘的炭化室里刨根問底,向爺爺了解關于燒炭的知識。爺爺一邊忙活,一邊不厭其煩地解答我提出的各種稀奇古怪的問題。以爺爺當時的眼界,自然看不到未來幾十年社會的變遷。他認為,技多不壓身,我多學習一門技藝,未來的生活就多一份保障。炭化室挖好后,前期鋸好的木柴就被搬運過來,一根一根地縱向排列在炭化室里。此時,排列緊湊是首要的標準,如果不夠緊湊,炭柴炭化后將會形成巨大的真空地帶,而這真空地帶會導致炭過度燃燒,進一步減少炭的數(shù)量。
技藝都是有講究的,裝炭柴也不例外。裝好的炭柴要像面包般中間凸起,四周逐漸降低。炭柴完全裝好后,爺爺先在炭化室后面正中間處挖煙道腔和排煙孔,又找來竹條,密集地扎在炭化室的四周,形成一個如蒙古包般高高的拱形,再在炭化室上面蓋一層稻草,最后在四個煙孔的位置上放上四個藤圈。這些工序完成后,前期挖炭化室的土方派上了用場——它們結實地覆蓋在稻草之上。至此我才知道,蓋稻草是為了防止土方掉落,這一步驟稱為筑窯蓋。窯蓋務求牢固,邊鋪土,邊打緊,錘打得越緊越好。窯蓋筑好后,將排煙孔中的泥土挖去,并輔松土。這一工序完成后,制作土窯的工作還沒有結束。燒炭少不了燃燒室,需要在炭化室前端下方,挖掘一個與炭化室相通的燃燒室。其實,燃燒室就相當于燒火做飯的燒火口,火焰通過燃燒室進入炭化室,而炭化室因密不透風,從而讓炭柴徹底炭化,變成我們想要的木炭。
爺爺是十里八鄉(xiāng)的燒炭高手,他一邊忙活,一邊語氣凝重地跟我們講燒炭的技巧。他希望將這一身技藝傳給我們。他說,窯很重要,窯不好,再好的技術也燒不出好炭來。他指了指挖好的炭窯說,窯有三個口,窯門、煙囪和燃燒室的點火口,它們的位置和大小都有講究,窯門要能讓人自由進出裝柴、取炭;點火口要順著風向,以便火苗往炭化室跑;煙囪則貼著山壁開在窯頂里側,通氣好,又不影響窯頂?shù)姆€(wěn)固性。窯壁厚度和窯膛大小也要適合。所以,挖一口炭窯一點也馬虎不得。
爺爺?shù)囊幌捵屛抑懒松畹钠D辛。燒炭是力氣活兒,也是技術活兒。
我問爺爺:那下次燒炭,還需要再挖一個窯嗎?
爺爺說:傻孩子,燒一次炭就挖一個窯,那得多累啊。取出木炭后,只要頂蓋完好,窯就成功了。為什么要放置竹條將窯頂制成拱形呢?就是為了固定土壤,讓它們定型。
聽爺爺這么說,我也松了一口氣。
爺爺又在忙活了。鋤頭、鐵鍬等工具在爺爺那雙粗糙的手里來回倒騰,發(fā)出“當當當”的聲響。湘南農(nóng)村的大山,彼此相隔不遠,聲音不斷地傳到對面的山上,又被一一彈回。一聲未絕,一聲又起,彼此應和。我又想起了一些往事。當北風呼嘯著一路南下來到我們村莊時,勁風如刀,將落葉喬木的葉子紛紛削落。風打在臉上,似乎能割掉耳朵。一場秋雨一場涼,一朝秋露一朝霜。白霜過后,寒風吹徹,冷氣不住地往衣服里鉆,直入骨髓的寒冷讓我整日縮著脖子。裸露在外的雙手就沒有那么幸運了,它們患上凍瘡后開始皴裂,火辣辣的生痛。到了夜間,手放入被窩,因為暖,生凍瘡的手就發(fā)癢,一撓,它就出血。如果鬧感冒,還會流鼻涕。那時的農(nóng)村是沒有紙巾可使用的,不懂事的孩子就用衣袖擦拭鼻子。冬天冷,一件外套要穿一個星期以上才換洗,幾天下來,兩只衣袖沾滿了鼻涕,別提多惡心了。冷歸冷,孩子們還是習慣在外面瘋跑,非得到春和景明,凍瘡才逐漸好轉。冷到了極致,我們就跑回家烤一會兒火,不過燒火總會有煙。稍微有點風,煙就隨之流轉。這時,爺爺就會說,要是烤炭火就好了,炭火沒煙。
我的心中便有了向往。
4
燒窯正式開始了。
我從家里給爺爺搬來一把凳子放在窯口,他穩(wěn)穩(wěn)地坐在凳子上,一心一意守著炭窯的火口,一把一把地添著細柴。由于燃燒室較深且火太過旺盛,平時燒火做飯用的火鉗因為太短根本無法使用。手還沒接近火口,一股灼熱便撲過來。爺爺早有準備,他砍了一根硬木棍子,在樹杈位置截斷。硬木棍子長達兩米,再也不用擔心大火灼傷人手。猛烈的火勢會點燃棍子,如此一來,硬木棍子在大火里也經(jīng)不起幾個來回。爺爺在身旁放了一桶水。每次捅火后,他便將硬木棍子從燃燒室取出放入水中滅火,到下一次需要捅火再拿出來使用,水對硬木棍子能起到暫時性的保護作用。
畢竟是新窯,燃燒室內還沒被大火炙烤過的粉石與泥土遇上高溫急劇收縮,不時噼啪爆響,仿佛點了一串一千響的大地紅鞭炮。火苗乘著風勢,往炭化室里猛沖。窯頂上,白煙滾滾,扶搖直上。如若有風吹過,煙受到壓制便被風撲倒在地。偶爾因為風向的原因,煙還往燒窯火的人身上撲,直熏得人睜不開眼睛。
燒窯需要持續(xù)地燒,吃飯也無法離開。奶奶主要負責家務,她和爺爺是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內”。飯菜做好后,奶奶會打包好,她自己送過去或者叫我們兄弟給爺爺送過去。那時的農(nóng)村沒有保溫飯盒。為了保暖,奶奶就把飯菜放在一個碗里,上面再蓋一個大一圈的海碗。爺爺喜歡喝酒,每餐都要小酌幾口。于是,酒也成了必備之物。如果是奶奶自己前去送飯,她到了窯邊,就會讓爺爺先吃飯,自己坐到矮凳子上,接過爺爺手里的捅火棍繼續(xù)燒火。兩人時不時地說幾句家常。冬天很冷,飯菜冷得快,把飯菜帶到外面吃會冷得更快。所以,更多的時候是奶奶匆忙吃罷飯去替換爺爺,直到爺爺吃完飯回到窯邊,她才回家慢慢地做家務。
冬天的夜來得早,當夜幕垂落在湘南農(nóng)村,天與山的連接處只剩下一根細細的虛線,寒風隨著夜幕的降臨更是隨心所欲,在村莊里如一群追逐打鬧的小獸亂竄,撞到人的身體,就送你一陣寒意。爺爺還在窯邊燒火,如果順利,也需要燒到大半夜。土坯房里,五瓦的白熾燈昏暗地亮著,奶奶攏著兩個更小的堂弟在火塘邊枯坐。堂弟們還小,很快就有了睡意,奶奶只好帶他們上床睡覺。堂弟們倒是很快睡著了,奶奶卻沒有睡意,對我們兄弟說:爺爺一個人在燒火,太孤單了,要不你們去陪陪?我們懂事地點點頭。推開木門,凝固的夜色有了質的變化,它迫不及待地流進屋里,屋內如豆的燈光也借著這機會從門縫里流出。踏著微弱的天光,我們往炭窯而去,遠遠地看到還在燒火的爺爺如山岳凝重,他依然穩(wěn)穩(wěn)地坐在凳子上,好像一整天都是這個坐姿,偶爾從桶里取來棍子挑動燃燒室的柴火。聽到我們的腳步聲,爺爺轉過身子,驚訝地問:你們怎么來了?
哥哥說:爺爺,我們來陪你。
爺爺揮手對我們說:回去吧,我不怕。爺爺經(jīng)常在外做木工,每次回來都很晚。常年穿行山路,他確實不怕。
我說:我們想陪你。
爺爺指了指地上的稻草說,坐吧。他起身觀察了一陣出煙口,看到白煙有了轉青的跡象,估算了一會兒,說:再燒三四個小時,就差不多了。又枯坐了一會兒,爺爺問我們:你們餓不?要是餓了,就去地窖里拿幾個紅薯和土豆來。
一聽這話,我和哥哥顧不上寒冷,蹦蹦跳跳地回到家中的地窖取紅薯、土豆。取來之后,爺爺在燃燒室的火灰中扒開一個洞,將紅薯、土豆放進去,再用滾燙的火灰將它們覆蓋。只消十幾二十分鐘的工夫,埋下的食物就熟了。爺爺將它們扒拉出來。紅薯和土豆太燙,在我們的雙手間來回顛著,待到冷卻一些,剝開皮,香氣撲鼻;咬一口,香味四溢。紅薯和土豆還不是最惹人喜愛的,如果有板栗和花生,尤其是雞蛋,放在火灰里燜熟,更是極佳的味蕾享受。我們吃著東西,烤著火,爺爺有時候會詢問我們的學習情況,有時候則給我們講故事。燃燒室里,大火依舊在熊熊燃燒。窯火的光亮從燃燒室中映射出來,將我們爺孫三人的背影鋪展在身后,像一張厚厚的黑色被褥。
爺爺不愧是燒窯的高手,他的估算是準確的,白煙完全轉青,就到了封窯的時候了。爺爺將排煙孔蓋上,同時封閉燃燒室的灶口。他并不放心,俯下身子將耳朵貼在出煙口,靜靜地聽上一會兒,確信封閉到位才肯回家。只要有一絲一毫的走氣,爺爺都得用細土認真覆蓋。爺爺說,一旦走氣,極有可能導致一窯炭化作白灰,那就前功盡棄了。
多年后,我上了初中,在物理課上才知道,燒炭,那是農(nóng)人用自己的赤誠點燃了一個火熱的世界。隨著高溫的炙烤,炭柴一點一點地縮水、收斂、炭化。如珍珠蚌內的砂礫,歷經(jīng)歲月的洗禮,終成珍珠,又像斗霜傲雪的梅花,留給世人無數(shù)詠嘆……
5
封窯之后,爺爺還是不敢大意,他早晚還得到窯邊看上兩回。從封窯到取窯,還有三到五天時間的冷卻期,爺爺利用這空檔,又帶著我們去山里砍炭柴。
取窯的日子到了。爺爺準備好鋤頭、撮箕、水、水勺,取下壓在窯口木板上的木樁,打開壓在窯口的木板,挖開窯口,將土運到一邊。待到窯口徹底挖開,爺爺提著一桶水,貓著身子往炭化室慢慢移動。炭化室沒有火是最理想的情況,如果有火,爺爺就舀水滅火。確認炭化室安全后,爺爺開始取炭。我們蹲在爺爺身后,以接力的方式將炭裝進炭簍子里。炭不能壓著,要像裝炭柴那樣豎立放置。為了防止炭碎造成損失,我們提前在炭簍子里鋪上一層稻草。
隨著愈發(fā)深入炭化室,原本在窯洞外瑟瑟發(fā)抖的我開始出汗,繼而感到悶熱難當,窯里的高溫讓我懷疑自己都要被烤成“木乃伊”了。我凝視著手中的木炭,只見木炭純黑的表面帶有白色的粉末,用手指輕輕地敲擊炭身,發(fā)出沉悶的音質。剛好爺爺出來透氣,忙對我說,炭容易碎,不要敲。
我看了看爺爺,他的臉上全是汗水。窯洞里黑色的灰塵到處飛揚,與汗水混合在一起,在爺爺?shù)哪樕狭粝铝艘坏赖赖摹皽羡帧薄V钡剿械奶咳⊥辏覀兌汲闪撕谌藘海B鼻孔里都是黑色的灰塵。在那個年代,沒有口罩這樣的勞保物品。這紛紛揚揚的灰塵對身體該有多大的傷害?
事后過了秤,爺爺欣慰地說,累也值得,有三百斤炭呢。
數(shù)千斤的濕炭柴變成這三百斤木炭,爺爺還說值得。我理解爺爺,很多技術不到家的燒炭人,往往燒一窯炭,最后只有一百多斤炭出窯。
燒制一窯炭的正常周期是七到十天。一窯完畢,又開始下一窯。直到寒冬徹底來臨,爺爺已經(jīng)帶著我們燒了十窯炭。那是三千多斤木炭啊,當一窯又一窯黑得發(fā)亮的木炭在屋里排得滿滿當當時,我們的心里感到踏實。
6
隆冬如期而至,爺爺就跟奶奶商量,這么多炭,去賣一點吧。奶奶嗔怪道:家里的事情,都是你做主,你看著辦。沒有讀多少書的爺爺掐著指頭算了算,說:家里需要留下五百斤炭,還有一些親戚朋友,可以送一些炭過去,待到下雪時再去送,雪中送炭嘛。我賣一半吧。
湘南農(nóng)村,五天一集,到了趕集的日子,爺爺就推著家里的獨輪車去趕集。車上是沉重的兩簍子木炭,一車就有兩百斤。爺爺?shù)那趧谂c為人處世在家鄉(xiāng)有口皆碑,木炭基本上到不了集上就會銷售一空。每年的初冬,就有人上門打招呼:三爺,今年給我留兩百斤炭呀。爺爺在他們四兄弟中排行第三,鄉(xiāng)親們習慣叫他三爺。爺爺甚是豪爽,碰到他人壓價,也會同意。碰到特別客氣的人家要多給錢,爺爺卻又堅決不收。人家說,三爺,燒炭辛苦,收著吧。多幾塊錢,給娃買糖吃。
爺爺堅決不要。當時我無法理解,人家壓價,爺爺就肯,多給幾塊錢卻堅決不要,這不是傻嗎?長大后我才明白,那正是我們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形成的關鍵期,爺爺在無形中幫我們塑造了正確的三觀。
將炭賣了錢后,爺爺買來家里生活必需的鹽、火柴,又給我們兄弟買來本子、筆,給奶奶買針頭線腦兒。他把剩下的錢交給奶奶保管,又對我們兄弟說:你們辛苦了,買點什么吃的給你們?聽到這話,我和哥哥喜笑顏開,帶著兩個堂弟開心地來到村里的代銷店挑選愛吃的零食。那一刻,燒炭所有的艱辛都被零食“收買”了,先苦后甜的欣喜溢滿心頭。
7
北風愈發(fā)強勁,農(nóng)人真正休閑的時間到了。有了炭,就不用忍受煙熏、煙嗆的柴火。在這里,就需要用到一種可以移動的火塘。那是一種用木頭釘成的四方形中空的架子,將從集市上買回來的火盆放置其上。在火盆的底部放一層冷灰,防止長時間的高溫縮短火盆的使用壽命。將炭架起來,點燃后,一家人將腳搭在火盆架子結實的寬邊上,一起圍著烤炭火。如果來了客人,就在架子上放上一張桌子,桌子上方鋪一床不用的舊被子。只消一會兒工夫,桌子與被子便都暖烘烘的了。這時,拿出瓜果來吃,或者拿出紙牌娛樂,實在愜意。打牌是男人們的娛樂項目,女人們也有自己的娛樂方式,她們擠在一起,忙點針線活兒,說家長里短,偶爾還講點私密的悄悄話。當我湊過去豎著耳朵聽時,女人們就揚起巴掌,說,小屁孩懂個啥,快去一邊玩。我得到指令,一溜煙兒跑出家門,與小伙伴們瘋玩。我和伙伴們追追打打,弄不好就有孩子哭叫起來,于是驚動了大人,他們跑出來,拿著一根棍子攆我們,嘴上大聲叫罵著:你們這些小鬼,無法無天了嗎?
在家可以烤火,學校卻沒火可烤,同學們就自己想辦法,這就需要用到一種叫“小火籠”的工具。其實就是一條凳子,凳子的底部是一個中空的四方形,在里面放上鐵制的內膽,內膽里鋪上一層灰,將炭火放進去,就是一個小型的移動火塘。大家提著小火籠去學校,再用塑料袋子包幾節(jié)木炭放進書包里,這一天的保暖問題就解決了。提著小火籠時需要小心,燃燒著的木炭被風一吹,炭皮爆出的火星子直往外躥,往往會燒壞衣服。
這樣的情景伴隨著我讀完小學。到了初中,路途遙遠,我開始住校。許是全球氣候變暖的原因,湘南的農(nóng)村也沒有那么冷了,曾經(jīng)掛在屋檐下一米長的冰柱逐漸縮短到最后消失不見。只是到了冬日的周末和寒假,我依然會幫爺爺去山里砍柴燒炭。再后來,電爐子大量普及,隨著爺爺?shù)睦先ズ腿藗儹h(huán)保意識的增強,燒炭在湘南農(nóng)村成了傳說。倒是鎮(zhèn)上有白炭賣,據(jù)說是干餾法制作而成的。看到這些白炭,我又想起塵封已久的往事。砍柴、背柴、鋸柴、制窯、裝窯、燒窯、取窯、賣炭、圍爐而坐的幸福……那些記憶彌足珍貴,點亮鄉(xiāng)下人家的溫暖瞬間。
(責任編輯 宋旭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