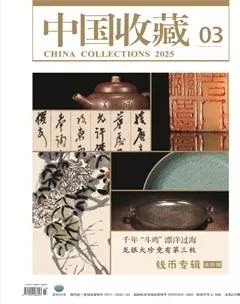弘光通寶映現明末短暫余暉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1644年4月25日),李自成率領農民起義軍攻陷北京,明思宗崇禎帝朱由檢于煤山自縊而死,享國276年的朱明王朝在戰火中退出歷史舞臺。
此時作為江南富庶之地的南京,明朝初年首都,永樂年間遷都北京以后的留都,一直保留了六部、都察院等一整套與北京相對應的中央機構。這里的官員、官僚在獲知北京陷落的信息后,夢想依仗長江以南的半壁江山力圖“復國”。

多方博弈福王登場
由于崇禎帝死后,皇子被大順軍俘獲,沒能逃出京城,擁立誰為新君便成為江南官員最為迫切的事情。從血緣親疏來看,有資格繼承皇位的是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潤、桂王朱常瀛、潞王朱常淓。其中福王朱由崧擁有諸多的優勢條件,是最有資格繼承皇位的人選。在山海關之戰不久,清軍在北京趕走李自成后,在江南以鳳陽總督馬士英、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淮安巡撫路振飛、禮部侍郎錢謙益、兵部侍郎呂大器、右都御史張慎言、守備太監盧九德等為代表的官員、軍閥等多方反復博弈下,于崇禎十七年(1644年)五月十五日擁立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稱帝,改元“弘光”,稱1645年(順治二年)為弘光元年,它是歷時18年“南明”朝廷的第一個短命的政權。
弘光政權建立伊始,全國范圍內存在四個政權,即在北京的清朝政權、南京的南明政權,還有西安的李自成大順政權和四川的張獻忠大西政權。勢力相比,南明政權勢力范圍包括南直隸、浙江、福建、廣東、廣西、云南、貴州等省份,以及湖廣、河南、山東的一部分,仍擁有淮河以南大部分土地和全國最為富庶的江浙地區,擁有號稱百萬的兵力,軍事力量主要由江北四鎮和左良玉兵團組成。江北四鎮包括東平伯劉澤清管轄淮北一帶11個州縣,興平伯高杰管轄徐州、泗州等13個州縣,廣昌伯劉良佐管轄鳳陽、壽州等8個州縣,靖南侯黃得功管轄滁州及和州等十余個州縣。寧南伯左良玉則以駐守武昌各鎮為策源地,掌握的軍隊有80萬之多。弘光朝廷無論在財力、民力、兵力上都不遜于當時的清廷,如果能夠勵精圖治,恢復中原,確保半壁江山安然無恙,不是不可能的事。
國本之爭加速滅亡
貨幣作為政權宣示經濟主權的標志性符號,對于弘光政權也不例外,在弘光政權建立后不久,便鑄造發行了“弘光通寶”錢。由于南明弘光朝存在時間短,錢幣鑄行時間短,目前研究史料相對缺乏。根據《三藩紀事本末》載:“福王名由崧,神宗孫,福王常洵之子。洛陽陷,王避亂南下,次淮安。值甲申三月國變,南中府等官會議監國,鳳督馬士英移書史可法及兵部侍郎呂大器,請奉福王……王至南京,以內守備府為行宮,四日監國,十五日僭即位,稱明年(1645年,順治二年)為弘光元年……六月,命禮部鑄國璽,以金代之……十月朔,命鑄弘光錢。”另外,民國時期丁福保編撰的《古錢大辭典》一書輯錄了前人對古錢的研究與考證,相對“弘光通寶”錢記載較為詳細(今天看來部分說法有待商榷),可供錢幣研究及收藏愛好者參閱,筆者在此不再贅述。

弘光政權建立后,由萬歷朝末期“國本之爭”引發的東林黨與閹黨之爭充斥朝野。黨爭和武將專權貫穿于弘光一朝,弘光朝廷坐擁富庶之地,卻難以有效地組織動員起來,整個朝廷渙散無力,內訌不斷,錯過了“翻盤”機會。隨著清軍進占北京等地,李自成的大順軍西撤,山東、河南東部地區出現權力真空,這本是弘光朝廷北上恢復中原的良機,由于弘光朝廷和實際掌握朝綱的馬士英等主政官員缺乏政治眼光,在弘光朝“借虜平寇”政策指導下,弘光朝廷對清廷不發一兵一卒,坐等清朝不斷擴大地盤,唯恐激怒清軍,將大好河山拱手相送。為了聯絡清廷,弘光朝廷派出了以名臣兵部右侍郎左懋第為首的北使團,攜帶國書和白銀十萬兩、黃金一千兩、綢緞一萬匹前往北京。最終遭清廷拒絕,左懋第被殺,導致“借虜平寇”政策的全面失敗。
弘光朝廷坐擁淮河以南,是當時中國人口最密集、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且受戰亂影響較小。弘光朝廷倘若好好治理,至少可像南宋一樣偏安一隅。但其腐敗超乎想象,導致軍政、財政情況極其糟糕。由于武將擁兵自重,飛揚跋扈,龐大的軍費負擔導致財政入不敷出,為解決財政問題,戶部決定加征稅賦,對民眾敲骨吸髓,導致四鎮之間相爭不斷,弘光帝朱由崧逐漸失去了民眾的支持。朱由崧執政期間,沉湎于酒色之中、醉生夢死,政以賄成,腐敗至極。尤其是經歷著名大悲案、假太子案、童妃案(史稱“南渡三案”)之后,弘光政權江河日下,加速了其滅亡的步伐。
清軍在擊敗大順軍后,由多鐸、拜尹圖、韓岱分率三路兵馬南下進攻南京。戰事期間,弘光朝廷內部仍然斗爭不斷,軍事上準備不足,無法形成有效的抵抗力量,官員紛紛降清。弘光元年四月,清軍直驅揚州,史可法請求明廷支援被拒,雖經奮力抵抗但揚州仍失陷,史可法被俘后英勇就義(史稱“揚州十日”)。隨后,清軍渡過長江,克鎮江,弘光帝出奔蕪湖。當年五月十五日,眾大臣獻南京投降清兵,南京陷落;五月二十二日弘光帝朱由崧在蕪湖被虜獲,當年九月送往北京,順治三年(1646年)五月被處死。其在位僅一年,政權即覆滅。
亂世鑄幣版式復雜
弘光通寶伴隨短命的弘光朝廷僅鑄行了7個月,它的發行對于弘光朝廷的經濟具有一定的穩定作用。在動蕩時期,它為南明政權的經濟發展提供了支持。弘光通寶從目前留存和出土分布來看,鑄造地及版別眾多,分小平錢和折二錢兩種。它們錢文直讀,有真書、隸書兩種,小平錢直徑通常多在2.4厘米至2.5厘米之間,重量在3.5克上下,折二錢直徑在2.7厘米至2.8厘米之間,重量在5至6克左右。該錢通常分為南京版、鳳陽版(圓貝寶版)、桂林版(桂版)、貴陽版(黔版)、云南版(滇版)、背貳手版等。
弘光通寶小平錢南京版(圖1),真書面文,整體字體規整,雙點通,寶字為八貝寶,弘字弓部第二筆前后出頭,爾寶,光字第一筆對折,通寶兩字通常較寬。
弘光通寶小平錢鳳陽版(圖2),在小平錢中最有特點,真書面文中帶有隸意,雙點通,寶字下貝圓目,雙點作小點“八”,雙點略低于穿口,弓部不出橫弓,通字高于穿口小邊緣,鑄造精美。
鳳陽版背“鳳”錢(圖3),錢文隸書,弘字右邊呈現三角狀,通字隸書明顯,寶字下背目字兩橫與邊框不接,與早期唐開元通寶寫法近似。“鳳”指省鳳陽,紀地錢,所指為馬士英鑄于安徽鳳陽,存世較少,為弘光錢中的名譽品。

弘光通寶桂林版(桂版)小平錢(圖4),真書面文,單點通,弘字弓部為左出弓,通寶兩字較長,通字的甬字頭通常“鴨嘴開口”,非常有特點。
弘光通寶貴州版(黔版)小平錢(圖5),面文真書,弘字弓部通常類似“虧”字,有行書的味道,弓字第二筆較長,左出,雙點通,分大字版和小字版兩種。另外從弘字寫法上,還有橫斷弓版,另外有背星者(圖5-1),兩種均較為少見。

弘光通寶云南版(滇版)小平錢存世量極大,版別也最多,其特征明顯,菱頭雙點通,背上星,由于弓字寫法及鑄造有較小差異,通常還分不出弓、右出弓(圖6)、雙出弓、肥字等多種版別,具有極其典型的滇版錢風格,能從部分崇禎通寶、興朝通寶和永歷通寶中找到形制和工藝相似的地方。
弘光通寶折二錢是南明錢幣的珍品,存世稀少。折二錢錢文柔弱,鑄造多不精,背貳錢以弘字寫法差異,分為大字版和小字版(窄弘版,圖7,泉友陳宗楠藏品)兩種,筆畫寫法略有差異,真書錢文含行意,單點通,穿右背文皆為“下點貳”。

近期國內不少泉友已經發現了數枚與折二背“貳”錢面文風格一致的光幕小平錢(圖8),定名“背貳手小平光背錢”,整個錢幣開門見山,多數泉友認為此錢和折二背“貳”錢,均為南京為核心的南直隸地區鑄幣,也有認為系位于徐州等地弘光朝江北四鎮鑄幣,筆者認為具體鑄幣地點需要進一步科學考證。
弘光通寶折二光幕錢為試鑄性質,泉界目前多數認為僅見于《戴拓》一枚,存世極罕。劉征著《大明泉譜》引用該錢拓圖(圖8-1)。馬定祥批注《歷代古錢圖說》中,在注釋“弘光通寶背貳錢”時說“另張叔馴藏有面文細字之折二型光背錢,珍。”華光譜《中國錢幣大集》、孫仲匯《簡明錢幣辭典》《中國錢幣大辭典》(元明編)所載之拓圖,筆者仔細觀察為同一枚錢,屬于何人收藏不得而知。近期據悉又有泉友新獲發現,未見其面,是否開門不能斷言,在此筆者不再展開評說。
滇版三錢非系補鑄
行文至此,筆者要說的是,多年來泉界有泉友和學者認為弘光通寶桂版、黔版、滇版應為后期永歷朝補鑄。特別是云南出土的崇禎通寶背星錢(圖9)、弘光通寶背星錢(圖6)、隆武通寶背星錢(圖10),版式風格、錢幣大小、制作工藝銅質銅色完全一致,與滇鑄永歷通寶錢風格高度契合,于是滇版上述三錢系永歷朝補鑄成為泉界的直觀感受認識。由于到目前沒有任何資料和確鑿的物證證明永歷朝在云南補鑄了滇版崇禎、弘光、隆武錢,此事未有最終結論。

2018年2月,故宮博物院劉舜強先生在《中國錢幣》上發表撰文《滇鑄“崇禎”“弘光”“隆武”三朝年號錢考》,從云南鑄幣歷史、相關錢幣文獻及永歷朝廷發展歷史綜合考證,得出結論:云南存世的大量崇禎通寶、弘光通寶和隆武通寶分別是明代崇禎朝(1627年至1644年)和明朝滅亡后云南地方留守政府奉“弘光”(1644年10月至1645年6月)、“隆武”(1645年6月至1647年3月)兩朝年號鑄造的貨幣,并不是永歷帝在1655年后在昆明補鑄的錢幣,詳細內容有興趣泉友可翻閱著述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