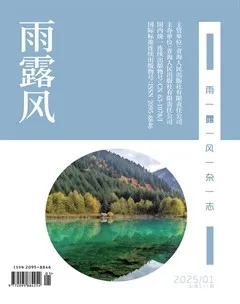一曲“老腔”贊鄉土

無論是在黃土飛揚的關中大地,還是在江淮水鄉、嶺南山川與巴蜀沃野,每一片土地都有其孕育的“老腔”。它們源遠流長,根植鄉土,帶著歲月的風霜與泥土的芳香。雖被人稱作“土”,卻以最原始的震顫觸動靈魂,仿佛陳忠實、趙樹理筆下那些揮灑大地激情的文學作品,醇厚、深沉,讓人不由得心生敬畏。作為一種與其發源地血肉相連的藝術形式,“老腔”震撼人心,正因其生于鄉土而魂牽故里。
對于在家鄉土壤里長大的人來說,家鄉的風物、聲音和記憶,是歲月留下的烙印;而對背井離鄉的游子,這份情感則愈加濃烈如酒。時常可見那些遠離故土的人,將家鄉的藝術和美食帶到城市中,在陌生的街巷里播撒熟悉的溫暖。這種舉動,是思鄉情愫在血脈中的回響。鄉土,是他們心靈深處的根,是飄零歲月里不變的歸宿。而“老腔”,這從泥土中長出的藝術,每一聲高亢的吼唱,每一段鏗鏘的敲打,都飽含著泥土的氣息,宛如一道無形的橋梁,牽引著聽者的心回到故土深處。正如陳忠實曾在“老腔”中聽到關中大地的雄渾回響,記起了蒼涼而厚重的鄉土畫卷。設想一個走出“老腔”故鄉的游子,在他耳畔再次響起那激越的旋律時,心底翻涌的,豈止是感動,更是千絲萬縷的歸屬感,在異鄉的風中如夢囈般盤旋。
“老腔”的震撼,能打動那些素未謀面的異鄉人。每片土地皆有其獨特的藝術遺產,那是千百年來人們審美的沉淀,是古老文化的載體。“老腔”正是如此,它以方言唱詞和特有的樂器,講述著土地的故事,延續著鄉土的脈搏。對不熟悉它的聽者而言,初聞“老腔”,便猶如觸碰到一塊散發著溫熱的石頭,感受到一種陌生卻引人入勝的力量。它那粗糲的聲調,不事雕琢,卻挾裹著文化的厚重與自然的律動,仿佛將人置于土地的心臟,感受其生生不息的脈動。
在《白鹿原上奏響一支老腔》中,白毛老漢與半大老漢那一聲聲擲地有聲的吼唱,敲擊木磚與長條板凳的節奏,仿佛是對天地間那份質樸與粗獷的禮贊。他們的全情投入,不僅展現了對藝術的狂熱,更展現了對鄉土文化的自豪。那是一種無須言語的執著,是一種深深扎根于血肉中的敬畏與自豪。聆聽他們的歌聲,我們仿佛也被那熱烈的火焰烘烤,感受到那份發自靈魂深處的呼喚。這種自信與熱愛,在時代的洪流中令人動容、震撼。
如《鄉土中國》所言,中國的根脈自始至終被鄉土文化深刻影響著。人與“老腔”的聯系如人與故土的聯系一樣緊密。是土地給予了“老腔”生命與靈魂,而“老腔”以其激越的聲音回饋鄉土。人們傳唱“老腔”,在傳唱中守護著鄉土,而“老腔”則喚醒了人心中潛藏的共鳴,這二者如風與沙,無法分離,共同訴說著大地上的故事。
“老腔”之所以震撼人心,正因它承載了鄉土的靈魂,在它的歌聲與節奏中,我們聽到的是土地的呼吸,感受到的是屬于這片大地的無言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