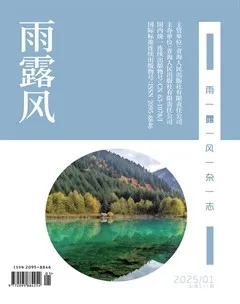玉米地里的小土堆
人們總說逝去的記憶就像電影中的黑白默片,隨著暖陽的蒸融,會變得愈來愈模糊,可那幾年刮在我臉上的寒風,卻真真切切。在孩提時,冬天的出行總是讓人不禁想起唐僧經歷的九九八十一難,兩個輪子的摩托車承擔起了一家的出行,在這般寒風刺骨的北方,每次長時間的出行,都令人感到畏懼。先是臉頰被凍得通紅,再是一股凜冽的冷風直往衣領鉆,使得人們只能將衣服再裹緊點。連呼出的氣都夾雜著塵土和汽油的味道,最是不喜冬天的出行。這時玉米地還很是平整。
總是記得傍晚時分的月亮跟我一起坐著摩托,摩托加速從淹沒腳面的河灘駛過,石頭頑皮地頂撞車輪,把人拋得一上一下,不多時便到了外婆家。“亞亞(‘亞亞’是媽媽的小名),回來啦!”一個小小的身影在微弱且散著暖黃色的燈光下走了出來。帶著外婆獨有的溫柔和方言的氣息從嘴唇發出,招呼我們去土灶的跟前烤火,那時外婆的臉上還沒有太多歲月帶來的小線條。一間小土屋承載了媽媽全部和我少部分的童年(我多數的童年時期是在爺爺奶奶家度過的)。就是這樣的日子,想起時就熱了眼眶,只是那時還沒有玉米地里的小土堆。
而在夏天,順著公路向上蜿蜒,等我完全熟睡,這時便走出了城市,再走過能印出腳印的小泥路,又蹚過一條清澈見底但兩邊河岸卻相距有些距離的小河,河中沒有小橋,只有大大小小的石塊,左一塊兒,右一塊兒,連接成一條小石道。外公總是來接我們,蹚過河灘,還有一段距離。小時候的孩子總是對水充滿親切感,喜歡光腳踩在水里,喜歡石頭的鈍感和腳的碰撞。向上走有個長坡,是條土路,下雨后,會出現小泥潭。泥潭的旁邊會出現洗衣的人家,山上的小泉匯集在這低洼的地方。鄉間的人們把這塊寶地叫“舡”,其實就是泉的意思。那時的玉米帶著泉水的清甜。
吾不識青天高,黃地厚,唯見月寒日暖,來煎人壽。上了初中后,學業的忙碌以及年齡的增長,讓我不再那么喜歡水的流動和外出了。等外婆的兒女們都有了自己的家庭,我的外婆便開始了自己的“職業生涯”,照顧一些手腳不便的老人。我真的覺得很神奇,我的外婆真的是一個很嬌小的人(上初中的我也不是很高,卻已經比外婆還要“冒”一些),腳也小,衣服也是最小碼數。她養活了四個孩子,自己找的工作。外婆工作的地方大多媽媽帶我去過,有鄉村的,有城市的。這次外婆可以決定為自己活。我的長輩們總說外公的脾氣犟得像牛一樣,可我覺得牛的脾氣才不像他那樣犟,外公的脾氣讓他的妻子和兒女忍耐了太多,難道是親近的人就要忍受他這樣的脾氣嗎?孩子們既憎惡著他的壞脾氣,又憐惜他的辛苦付出。這時的玉米地里也沒有小土堆。
這時的外婆已然不像我童年見到的那樣年輕,走起路來一只腿也是蹣跚的。當時的小土房也成了水泥和石磚砌起來的大房子。只是少了泥土的氣息,多了一絲冰冷。玉米也沒了甜糯的味道。
“時光只解催人老,不信多情。”這時我記憶中的外婆好像還是坐在家中那把低矮的椅子上,雙眼微瞇著。才突然想起原來清晰的臉龐居然顯得模糊。那青澀的童年早已成了模糊的記憶,在時間長河的沖蝕下任何事物都將變得不再清晰。凌晨的電話聲劃破了黑夜,明明是前幾天才見到的人,等救護車趕到時一切都已來不及。生了病之后,外婆便沉睡在床上,兒女和孫子女怎么也叫不醒,看著她一點點地消瘦,一點點地憔悴,而后和整個季節一起老去。只是在一個陽光明媚的清晨,有的人永遠留在了昨天。媽媽不止一次地后悔自己沒有太多時間陪伴外婆,她的時間給了我們。
外婆的一生就好像是大多女性的一生,為了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兜兜轉轉,安排好了這個卻放心不下那個。她們應該是自由的。有些鳥注定是不會被關在籠子里的,因為它們的每一片羽毛上都閃耀著自由的光輝。一叢叢的玉米擋住了那個小土堆。親人的逝去,就像那片曾經繁茂的玉米地里,最挺拔、最飽滿的一株,突然間靜默地倒下。始是終,終是始,我們會在下一個春天相遇。
作者簡介:歐曉晶,陜西人,就讀于西安外事學院,是一位熱愛文學與創作的青年。對文字有著濃厚的興趣,喜歡在字里行間尋找心靈的慰藉與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