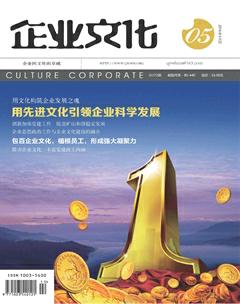論人的不安全行為及控制方法
程皓
摘 要:大量數據表明,人的不安全行為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本文闡述了人的不安全行為的概念和基本分類,并對產生不安全行為的原因進行了分析,最后提出消除人的不安全行為的具體控制方法。
關鍵詞:安全管理;不安全行為
一般來說,生產事故隱患主要集中于人、機、環境和管理四個環節,即人的不安全行為、物的不安全狀態、環境的不安全條件和管理上的缺陷。根據人因失誤理論,一切事故都是因為的人的失誤造成的。由于人的失誤導致的事故占事故總量的90%以上,因此研究和控制人的不安全行為是對于預防和減少傷亡事故具有重要意義。
一、不安全行為的概念與分類
人的不安全行為是指違反安全規則和安全原則(包括違反安全法律、法規、規程、條例、標準、規定,也包括違反了大多數人都知道并遵守的不成文的安全原則),使事故有可能發生或有機會發生的行動。
從人的心理狀態出發,人的不安全行為分為有意和無意兩大類。有意的不安全行為是指有目的、有意圖、明知故犯的不安全行為,是故意的違章行為,如酒后上崗,酒后駕車等。這些不安全行為盡管表現形式不同,卻有一個共同特點,即冒險,心存僥幸。無意的不安全行為是指非故意的或無意識的不安全行為。人們一旦認識到了,就會及時地糾正。這類錯誤行為的表現比較多,概括起來大致有幾方面:人體的生理機能有缺陷,如聽力或視力較差等;因知識和經驗缺乏而造成判斷失誤,如從業時間短;大腦意識水平低下,不能滿足工作需求,如疲勞作業等。這些因素可能單獨導致不安全行為,也可能共同作用導致不安全行為的發生。
二、產生不安全行為的原因
(一)虛假安全現象。二次大戰后,英國空軍在統計戰爭中戰機失事原因時,非常震驚地發現,奪走飛行員生命最多的不是敵人猛烈的炮火,也不是大自然的狂風暴雨,而是在完成任務凱旋歸來,即將著陸的幾分鐘里飛行員操作失誤造成的。心理學家分析稱,一個人在高度緊張過后,一旦外界刺激消失,人的心里就會產生“幾乎不可抑制的放松傾向”,安全管理專家稱之為“虛假安全”現象。毋庸置疑,在我們日常的生產活動中,“虛假安全”現象隨處可見,如臨近下班時換班時,在高度緊張過后,有的職工就會產生極度的放松,對手頭工作馬馬虎虎,不按規程操作,最終釀成大禍。
(二)行為人安全意識淡薄,工作態度不端正。通常表現為如下心理特征:
1.麻痹心理。有這種心理的人往往基于錯誤的經驗:例如某項違章操作從來未發生事故或多年未發生事故,人的心里危險意識就會弱化,最后習以為常,認為不會有危險。
2.冒險心理。有這種心理的人大多是剛參加工作的年輕人,或喜歡逞能、爭強好勝,或急于求成,不按規程作業,甚至有人會認為自己的冒險行為是“英雄行為”。
3.僥幸心理。有這種心理的人往往基于一種錯誤的認識:認為違章操作不一定就會發生事故,即便發生了也不一定會造成傷害,或者相信自己有能力應對。久而久之,人們便形成了錯誤的作業習慣。
4.捷徑心理。有這種心理的人會把安全管理制度規定、安全措施、安全設備當作其完成生產任務的障礙。例如為了省事、省時間不戴安全帽,戴帽不系帽帶,高空作業不系安全繩、擅闖危險區域等。這種心理造成的事故,在所有事故中占很大比例。
5.從眾心理。有這種心理的人,其工作環境內大都存在有不安全行為的人,于是也隨之效仿,甚至擔心不這樣做會不合群。如果有人不遵守安全操作規程并未發生事故,其他人就會跟著不按規程操作。
(三)工作監督不力。管理人員安全觀念欠缺,安全技術水平低,本身看不出問題所在,找不到安全管理的切入點,造成安全現場管理不嚴格、不到位。
(四)行為人的生理和心理有缺陷。每一項作業對行為人的生理和心理狀態都有一定的要求,如果不能滿足這些要求就會造成行為人的判斷失誤和動作失誤。如果行為人的體能、體形不符合要求,視力、聽力有缺陷,反應遲鈍,高血壓、心臟病、孕婦等生理缺陷或過度疲勞,情緒恐慌、焦慮等不穩定心理狀態,都會產生不安全行為。
(五)作業環境不良。生產作業環境的好壞直接影響人的作業行為。狹窄的空間難以使人按照安全操作規程進行安全作業;高溫會使人產生疲勞,引起行動遲緩、作業失誤;噪聲使人煩躁,無法安心工作;照明不足使人視覺疲勞,容易接受錯誤信息等。惡劣的作業環境不僅增加了人的勞動強度,易使人產生疲勞,更會使人感到心煩意亂,注意力不集中。因此,作業環境不良也是產生人的不安全行為的一個重要因素。
(六)培訓教育不到位,安全技能低下。一是沒有對行為人進行必要的安全培訓教育,使行為人缺乏必備的安全意識、安全知識和安全技能,不具備安全作業能力。二是培訓的頻次不足,形式內容單一。
三、不安全行為的控制方法
(一)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是做好安全工作的保障。管理制度必須是合法合理的,并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能夠最大程度地調動人的積極性,引導人自覺遵守制度;另一方面,對于違反制度的行為必須嚴厲處罰,獎懲分明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二)采取各種形式開展有效的安全培訓與教育,不斷提高人的安全意識、知識水平和技能水平。對員工的培訓、教育,真正做到區別對待、有的放矢。對新員工在上崗前要進行應知、應會和安全操作知識的培訓和教育;對特種作業人員要經過培訓、教育、考核,合格后,做到持證上崗;對熟練工重點加強安全操作規程的強化教育,堅決杜絕習慣性人的不安全行為的發生。
對員工安全教育應區分安全心理教育,安全知識教育,安全技能培訓和安全應急能力培訓等。通過各種形式的宣傳培訓、教育,使每位員工知道不能做什么、應該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在突發意外時如何自救等。更重要的是如何提高員工的安全意識,培養員工遵章守紀的自覺性,從而消除人的不安全行為。
(三)堅持“將合適的人放在適合的崗位”這一理念。由于人的生理狀況和個性不同,每個人能夠適應的工作內容與工作環境也不同,因此在安全管理工作中應高度重視這一點。合理運用行政手段將不同類型的人安排在適合的工作崗位,并在工作中注重觀察人的情緒和生理狀態變化,必要時做出合理的調整,可以有效的控制人的不安全行為。
(四)創造良好的現場工作環境。良好的現場工作環境可以令人感到心情舒暢,緩解工作壓力,提高人的工作積極性和工作效率。因此安全管理人員應經常檢查作業環境,發現問題及時改善,避免因噪音、光線等因素造成人的行為失誤。
(五)強化檢查監督是有力保證。制度再好,關鍵在于執行。各項安全制度和安全操作規程都是血的教訓換來的,但是,由于每位員工的素質和知識水平的差異,加上其他因素的影響,在實際生產作業中,有些員工不能自覺地去遵守規章制度和操作規程。因此,加強對人的作業行為的檢查和監督是非常必要的。
首先是安全管理人員應經常對員工實施作業的現場和作業過程進行檢查和監督,其次應及時了解和掌握員工的生理和心理狀態,發現人員異常時采取調離崗位等必要措施,對患嚴重疾病的、懷孕月份長的女工等人員強制離崗休假,最后是加大對“三違行為”檢查考核力度,以防止各類事故的發生。要用強制手段培養員工自覺遵守安全制度,安全操作規程的習慣。
(六)努力營造具有企業自身特色的安全文化。安全文化是安全行為規范和價值觀的綜合體現,是一個無形的磁場。它規范制約著人對安全的態度和采取的行為方式,任何人的行為都要受到制約、受到左右,他能時刻提示和驅使行為人自覺地抵制違規、違章、蠻干行為。這個磁場越強大,對人的約束力越強,安全越有保障。因此,建設企業自身安全文化是控制人的不安全行為的根本途徑。
總之,控制人的安全行為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不可能立竿見影。應以提升職工的安全意識和安全行為的自覺性為切入點,以健全制度和培訓教育為途徑,以形成安全文化為終極目標,有效地控制人的不安全行為,避免和減少事故的發生,實現企業的平穩安全發展。
參考文獻:
[1]孫斌.等.對人的不安全行為的研究及解決對策.山西焦炭,2003.(1).
[2]梁麗.關于安全行為科學的探討[J].中國安全科學學報,19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