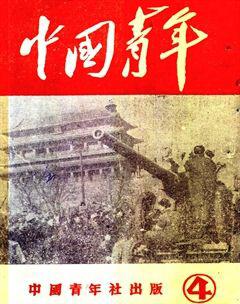論“土地之監”
何其芳
1
舊俄羅斯有這樣一個對知識分子的稱呼:
“土地之監”。
我想,這恐怕只是在“到民間去”的民粹主義者們的時代里流行過,而后,知識分子經過了革命的考驗,歷史的考驗,這個說他們是人民的精神的比喻就慢慢地被忘記了。
現在我們說到知識分子,往往帶著一種不好的意味。
我聽見過一個知識分子的同志說,“我真討厭知識分子,所以我從嚴不理他們。”他是寫小說的,已經寫了好幾本短篇小說。
我聽見又一個知識分子的同志說“我真慚愧我也是一個知識分子。”他這句感欣的話的說出是當我在前線,當另外兩個剛離開學校的年青的同志在一次行軍中疏忽地丟失了行李。他參加部隊久一些。他仿佛不愿意和他們共同一個稱呼。
不過也有一個手工人接觸過的同志告訴我,工人同志們并不輕視知識分子,并不像知識分子那樣輕視知識分子。
2
知識本來是可珍貴的,有了知識本來是很好的事情。我讀過高爾基的一篇叫做《書籍》的文章,那篇直是一篇頌歌。他總帶著深沉的感謝談起他的那些先生,從教他識字讀書的一個船上的廚子到修改他的作品的珂羅連科。十月革命剛過去以后,他總是那樣喜歡打電話麻煩列寧,請求釋放某個被捕的教授,或者為某同學者要屋子,要糧食。這個從無產階級出身的人,這個自言“每一部書是一個梯子,使我從獸類爬到人類”的人,對于知識分子和文化的重視的態度是對的。
但這也是事實,知識分子是一個特殊的,沒有獨立性的階層。是一個搖擺于舊的營壘與新營壘之間之階層,是一個在某些關頭顯得軟弱無能,容易迷失,甚至于可恥的階層。所以高樂基
又以一種詛咒的態度在小說中描畫了他們。
3
中國的知識分子更明顯地有一個不好的傳統我想稱他為“爬”的傳統。
這是一有個名的典故,然而不妨重述一次:
梁實秋在韋勃脫字典上查出了“無產階級”不過是一些沒有職業的,窮苦的,并不高貴的人之后,開始嚴肅地說道,“你們,無產階級的朋友們,為什么不學好?為什么不求上進?為什么不把學問弄好好?為什么不多賺一些錢,變成闊老?為什么不好地當工人,然后升為工頭,再升為資本家?你們也可以住上爬呀!”
4
比較起來,我們容易鄙棄古老的中國的一些朽腐的東西,而不覺察從歐洲來的資本主義時期的思想(雖說對于中國的封建社會的產物而言是有著進步的意義的)也帶給了我們一些需要再否定一次的不好的影響。
特別與知識分子有關系的一點,我想稱它為十九世紀的精神,或者個人主義:
兒童似的自我中心主義。
每個人都感到自己是精神上負著十字架的基督。
總以為自己想個很深沉:迷失于一個自己虛構的迷津。
5
廢名在他的小說《橋》里面寫那個男主人小林有一天忽然對那個女主人公琴子說,
“昨夜我做了一很世俗的夢,醒來我悲哀得很……”
你看他說得多動人,多神秘,多深沉!但讀過這部小說,而且還讀得細心,而且已經習慣了,理解了他那種含含胡胡的寫法的人會知道小林這句話是指的什么。就在前面一章,這個被寫得幾乎沒有人間煙火氣的人物和他的一個在塘邊洗衣服的嫂子發生了性的關系。
由于藝術家的直覺,或者由于一個人的實際生活的體驗,廢名不能自止地在那樣一個童話似
的故事里而插入了這樣一個現實的事件。然而他仍然躲避開了,沒有在這問題上多停留一會兒,沒有想通這道理。他不能肯定人的肉體的自然的要求。他不知道那不能用“世俗”這個字眼來輕輕抹去,那并不是夢,那也沒有什么可悲哀。至于說于他們愛著的女子,小林做了一個不好的行為,不忠實的行為,那卻都是另外一個問題。作者并沒有觸到它。
6
我想寫出這樣一個公式:
單純——復雜——單純。
說得詳細一點:由原始的單純,通過應該有的復雜,達到新的圓滿的單純。
這個公式對于思想,對于人,都是適用的。正確的道理總是明確而且簡單。經歷的斗爭越多的人越是平易近人。
7
人制造著書籍,而書籍也在某種意義上制造著人。
我們的生活環境決定了我們了所能接受的知識,而它們也反過來影響了我們。
現在我們需要更多的有著正確的觀點的新的書籍。
現在我們需要對一切的知識投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光輝。
8
由于社會環境的特殊性,中國的知識分子是更容易走向革命一些的。而且,從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已經有了好幾代了。最年青的一代,參加了抗戰以前的學生運動而參加著抗戰的一代,應該是最接近新的典型的一代。然而就是這樣的人也仍然有時苦于一些個人的問題,仍然給人家這樣一種感覺,“知識分子真是問題多!”我想,一個簡單的口號是需要提出來的:
“一個新的知識分子起碼應該會正確地處理他的私人問題。”
(一九四○年十月革命節后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