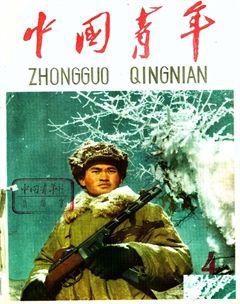作文卷的三種毛病
克民
作文章的人,總希望把這文章寫好,沒有希望寫壞的。但我最近看了一些中學作文卷子,其中最不通順的,往往倒正是那些極力想把文章寫好的同學。(普通些的卷子,雖然平淡單調,或錯字多,或像流水賬,卻較少特別刺眼的不通。)我想這主要是因為大家辨別不清文章的“好”與“壞”的緣故。這問題恐怕許多初學寫作的人都有。
我姑且用這些中學同學所犯的幾種毛病作例子,試談談如何避免這些毛病。
第一種毛病,是在文章中充滿了許多月亮呀、微風呀、白云呀……的風景描寫。不管文章是什么題目,也不問這描寫與自己所要說的事情有無關系。例如下引的一段文章:
“淺藍色的高空,懸掛著一輪銀白色的月球。無窮的光芒,灑遍了山崗田野。長蛇似的河流,歡喜得發出嘩嘩的喧叫。微風細吹,波動禾草,灣屈著殘老的身軀,掙扎著向上微笑。”下面接著卻是“濟南解放,錦州攻克,接著長春的敵人,也全部求降了,人民解放的自衛戰爭,在這第三個秋天……”
且不說頭一段風景描寫好不好(禾草絕不會微笑,這句子已經不通),單問它與下面那段可有絲毫關系?寫這文章的目的,既是談人民解放戰爭,那么,凡是與人民解放戰爭無干的東西,隨便怎樣美妙,就都不能放在文章里。放進去就是廢話。
又例如,一篇描寫翻身農民回憶舊社會痛苦的文章,前面來上一段:“太陽還沒有升上地平線,蔚藍的天空中還露著幾顆淡淡的星兒。河岸山上一片綠草,親著許多野花,清幽鮮艷……”一篇描寫黃河船夫勞苦生活的文章,卻寫上……“那輕絮似的白云微微飄動,月亮露出溫柔的笑容……”這種描寫,對于文章的中心意思全沒幫助,它的情調與文章中心內容完全相反,如果寫一對愛人劃小船,或者可以說月亮白云都在微笑,在與波濤斗爭的黃河船夫眼中,月亮怎會那樣笑法呢?
許多人所以喜歡用這些風花雪月的濫調,恐怕是因為有些中學教師在教學生讀名家作品時有些編向。常是專摘其中描寫自然風景的詞句,說這些詞句“好”,更誤以為作品之所以好,全在這些地方,教學生抄錄。實際上,一篇真正好的作品,一定是全文組織周密,圍繞一個中心思想,不應該有一句沒用的話。每一句描寫風景的句子,都要在最必需最確切的時候才能寫上去。例如魯迅的“藥”,有一段:“微風早經停息了;枯草支支立著,有如銅絲。一絲發抖的聲音,在空氣中愈顫愈細,細到沒有,周圍便都是死一般的靜。兩人站在枯草叢里,仰面看那烏鴉;那烏鴉也在筆直的樹枝間,縮著頭,鐵鑄一般的站著。”
這是很好的風景描寫。為什么好呢?因為全文是寫一個還沒有為落后的市民所懂得的革命先驅者,流血犧牲之后,他母親獨自去上墳;在末段悲憤沉重的情緒中,放上這一段描寫,每一個字都有分量的打動人心。假如是寫慶祝革命勝利的狂歡大會,也放上這么一段,那就不是好文章,成了最壞的文章了。
一個初學寫作的人,還不能適當的作風景描寫,那該怎么辦呢?最簡捷的辦法就是:只有在你覺得若不寫上這段風景,意思就說不清楚說不周全的時候,那才寫;此外就不要去講那些月亮星光。無論那詞句雕琢得多么得意,也不要舍不得割愛!
第二種毛病是:有人受了文言的國文課本影響,在文章里裝上些不通的之乎者也。例如下引的文章:“是時,太陽斜射過來。小鳥更樂,然小鳥之樂,而不知我之樂。我之樂,而不知農民之樂而樂也。”
這自然是套的宋朝歐陽修的“醉翁亭記”了。你猜前面說什么?原來卻說的是一個解放區工作干部在田野里訪問農民翻身的情形,完全是白話文,可拖了這條“醉翁亭記”的尾巴。上下連起來一讀,更使人發笑。還有一個人在“我學國文的目的”一題下寫道:“所謂國文乃一國之文也。比如俄文乃蘇聯之文字,英文乃英國之文字,方塊字乃中國之文字也。吾身為中國國民,不學中國文字,豈不等于一有眼之瞽乎?”
這段文全是“之乎者也”,沒有什么內容。對于這樣的學生,我們只能有一句忠告:“決不要寫文言文!”
我們并不是說中學課本中絕對不能選出一點淺近文言文。少讀一點,使學生獲得一些看懂文言的能力,是可以的。因為在應用文上,文言迄未能完全絕跡。但這目的應該只到看懂為止,而且選材也應著重通電新聞等眼前要碰到的東西,和較有歷史價值的文字;決不可以學起唐宋八家的腔調來做文章!應當知道,這種腔調是和它封建陳腐的內容相結合的,用它來裝進步內容,就是對于內容的諷剌!(青年同學們若要知道關于這一點的詳細道理,請去讀近代中國啟蒙運動史。)
第三種毛病是,有些人常在完全不適當的條住下,模仿一些決議指示文件上的詞句。例如一標題為“夏晨”的文章,有這么一句:“我奔跳了幾下,完成了呼吸新鮮空氣的任務后,即返回歸路。”又一個人寫自己小時候的回憶,有一句道:“天冷了,我響應了母親多穿衣服的號召”更多的文章,則正像毛主席在“反對黨八股”中所說,不論寫什么題目,一律是“一國際,二國內,三邊區,四本部”一律是在文章中堆滿了政治名詞。乍看彷佛政治性很強,很嚴肅,實際上空空洞洞、并未說清任何一個最小的問題。例如:有一篇題為“學習國文”的文章,全文只有二百多字,前面講:“時代的車輪勇猛前進,人民解放軍在進軍,”以下是講錦州濟南的勝利有何意義,這樣足足占了一百七十多字,等說到本題時,文章也沒有了。又一個人,在“我為什么學國文”的題目下,寫的是:
“今后,首先應該認識到文化政治理論日常工作等是有它密切聯系的。絕不能單純分開來看。任何的單純觀點,是不對的,是學不好的,是用不上的,是會定向偏差的!有了文化即應提高到政治理論,工作即是學習文化的具體對象,因而在思想上應有高度的自覺性……”
這些話何嘗解決了他為什么要學國文的問題?詞句上總是“國文對于其他學科的學習起著推動作用”,或前面說學國文可識生字,后面說“以達看懂別人寫的東西,特別是關于政治修養的,領會其精神與實質,和運用到實際之目的。”等等。把這類句子仔細看看,其實意思極不確切,似是而非;甚至完全不正確。試問:僅僅學國文,難道就能領會政治修養的精神實質和運用到實際了嗎?許多用同一題目寫的文章,都是這樣子。很少人能夠清楚的說出自己在工作學習中因為國文程度究竟碰到過什么困難?在幾時?為什么事情!自己到底是否深刻體驗到學國文的必要?所以犯這個毛病,恐怕是由于許多人讀文件讀指示時,看到那上面總是講形勢講任務,總是有許多政治名詞;于是不論自己寫什么文章,都照樣來。實際上,那些文件指示,是非那樣寫不可的,中共中央發個指示,怎能不根據全國的形勢?黨委講干部學習,自然必須談到大家的觀點,自覺性,要大家掌握文件精神實質。否則就不能表達一定的政治內容。一個初中學生學國文,盡管也與全國形勢有關,但若就把它完完全全歸結到全國形勢上去,那就是不實事求是,取消事物具體內容的作法。真正政治性強的馬列主義者,正是應該反對這種作法的。以上三種毛病,主要恐怕也是因為寫作的人不肯照自己原來心里想的東西去寫,不肯用力把自己想的東西確切表現出來;而只是用力去裝飾文章。所以文本寫不好,寫不通。關于怎樣寫就好,本刊第二期有篇寫作范例曾經談到,現在不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