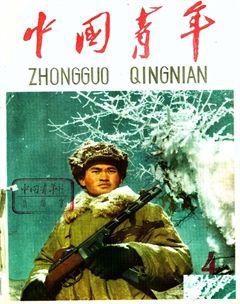讀“夏紅秋”
韋君宜
“夏紅秋”是值得工作干部與新解放區學生都愛看的書。這本小說說到下一個目前我們大家正關心的問題。新區學生可以拿他當鏡子照照自己,工作同志們可以由此多少了解一些新區的中小城市中學生們到底在想些什么東西。對執行城市政策上頭有些幫助。
這小說是寫的在東北的安東市,日本投降之后,一個十七歲的中學女生夏紅秋,一下子從十四年的睡夢中醒覺,知道了自己還有個祖國。她很快很容易的就接受了國民黨的“正統”宣傳,把親愛的祖國和“蔣委員長”統一起來,天天夢想銀色胡須金色肩章的“將委員長”,騎著白馬帶著全部是美男子的軍隊,前來解救這些失去祖國十四年的苦孩子們。但是,事實上來的不是“蔣委員長”,卻是一群穿黃大掛的“窮八路”,她和她的同學們毫無理由地用蔑視、譏笑、辱罵來對待這個軍隊和政權,笑他們窮、土氣,蔑視那些不忍得電燈的戰士和穿破軍服的女干部。她偶然參加唱唱進步歌曲,反受到國民黨暗藏特務與大批落后同學的笑罵。她就抱著一顆追求“光明”的心,跑到國民黨統治的沈陽去了。想進學校,但她沒有門路,沈陽根本沒人理睬她。她又在一家派館里見到國民黨接收大員的丑惡。終于,碰到了一個也是滿懷熱望來投奔國民黨結果卻流落在街上賣煙卷的舊日老師。她聽了他的勸告,回到安東。她又在半路上,在參觀團中,在招待會上,分別看到工人農民士兵真正偉大。便下決心說出自己去沈陽的經過,參加了革命組織——文工團。
中國學生有著五四、一二九、一二一的光榮革命傳統,但是,我們也不能忘掉在平津京滬昆明重慶成都……之外,還有好些中小城市里的中學生,近幾年來沒有機會接受民主運動的影響,除了課本與老師之外沒接觸過的知識,飽受國民黨的長期愚民教育,懷著盲目的“正統”觀念。這是學生運動亟待開辟的一塊新土,也是中等教育中極重要的問題,“夏紅秋”之所以在東北連銷幾版,也就由于它提出了這一問題。目前,國民黨反動政府即將土崩瓦解了,學生們對國民黨盲目的正統觀念也會大部分跟著消失。這是比“夏紅秋”所描寫的更新的一個情況,但是,對國民黨的幻滅,卻并不等于真正認識和相信了共產黨和民主政權,更不等于樹立了“為人民服務”的新觀念。所以,“夏紅秋”還是完全值得讀的。
在提出問題方面,這小說寫得很好,很真實。只是后半部解決問題那部分顯得太潦草些。
它寫夏紅秋對共產黨與解放軍的糊涂與敵視,的確刻劃出一個幼稚的中學生的落后想法,而絕不是有什么很深成見的反共分子的想法。寫夏紅秋開始看到共產黨的好處,也恰如其分,并不曾把她寫成怎樣透澈了解了和堅決相信了新民主主義與共產主義。(如果寫成那樣,倒是違反真實的夸張了。)
例如前段描寫夏紅秋和她的同學看不起“八路”,作者抓住這群中學生和一個“八路”女干部打交道的場面。寫那由偽滿時代留用的教師單著重介紹那女干部是“貝滿畢業生”,寫夏紅秋想:“八路那里來的中學生?一定是吹牛!”寥寥兩句話多么生動的描出了他們的知識水平和看問題方法!后來,她開始佩服這女干部,主要也不是由于什么思想上打通,而是首先由于女干部會說話,而且是漂亮的北平腔,會演戲,和氣……等等。后來寫夏紅秋赴蕭司令員的招待會,思想已經開始轉變了,但使她大驚敬服的不是別的,卻是蕭司令的年輕,文雅,給她們敬酒……等等。夏紅秋在會后寫的壁報文章;“誰說共產黨不重視青年知識分子呢?你和司令同桌吃過飯嗎?誰說共產黨沒有人才呢?你見過這樣年少的將軍嗎?”也畫出一個十幾歲中學生的思想和口吻。
也許有些革命經歷的讀者會以為這種“思想轉變”未免太淺薄了,但這寫的正是真實。我們的確也聽到,正定、石家莊、濟南等地有些中學生對共產黨開始佩服,就不過因為發現了自己唱歌演戲原來遠遠比不上共產黨而已。“夏紅秋”的作者用他的故事告訴我們:這群十六七歲的孩子們原是單純的,他們不靠近共產黨只不過由于鐵桶似的愚民教育所造成的愚昧。一經共產黨的萬丈光芒透過鐵桶漏進一點點光來,這單純愚昧便冰消瓦解了。
但問題是,這種單純的愚昧雖比較容易消除,而要使這些青年真正覺悟要獻身于新民主主義與共產主義事業,真正建立起為人民服務的新人生觀,卻不是那樣簡單的事了。那需要耐心的教育,須經過細致復雜的思想過程。“夏紅秋”在這一方面就寫得較草率。去沈陽碰釘子是她轉變的關鍵,在從沈陽回來后,作者為了要說明夏紅秋認識了工農兵的偉大;便寫她在路上遇見一個老農婦,參觀一回工廠,又在火車上遇匪受到戰士的保護。工、農、兵每樣碰到一次就使她由“工人農民像土豆一樣”的思想,一下子進步到懂得“勞苦群眾是人類智慧的源泉,力的海。共產黨在工人農民中扎了根,怎會不勝利呢?”直可太簡單了!那幾次遭遇,自然會對備有影響。但是在這里在們沒有常見剛萌芽的新思想如何與盤據頭腦的舊思想斗爭,沒有看見剛開始垮下去的舊思想還有多少殘余,特別是沒有看見共產黨的教育究竟怎樣一點點在夏紅秋身上擴大影響。(作品中完全沒有觸到,學校的課程、教師、討論會……可發生過作用?)作者已曾告訴我們,夏紅秋只是開始轉變,并沒有進步到怎樣完美。但他對這一點缺乏深刻具體的分析。讀者并不能由作品中看清夏紅秋在參加文工團時,究意進步到怎樣一個程度了。她參加文工團是否除去模糊的“為工農兵服務”觀念力外,就沒有混雜其他動機和幻想呢?(而在夏紅秋這類青年,這通常是會有的。)這些問題,夏紅秋本人不見得了解,但,作為一個作者、是應該用比夏紅秋看得更遠更深的眼光,來把這些問題分析給讀者看,形象化的表現給讀者看的。
雖然有這樣缺點,但“夏紅秋”還不失為一本好書。我希望東北以外的其他解放區能翻印一些,給新解放區的青年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