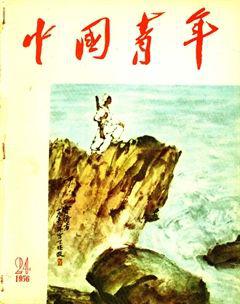愛養父母在社會主義社會里也是必要的美德
馮定
人,從來不是也不能離群索居而孤單生存的,于是人和人之間就不得不發生關系;那么這種關系怎樣處理才算正確和怎樣處理才算不正確呢,這就是倫理學上所提出的問題了。不過在有階級的社會里,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總是有不同的甚至是完全對立的道德標準的;只有當階級已經被消滅的社會主義社會里這才開始可以談不是分裂的而是整個人類的共同道德了;這樣的道德,既是社會在發展中必然要形成的,也是我們應該來研究和倡導的。
人類的生存,其實正是人這個族類的生存;所以我們如果暫時抽出階級因素不談的話,那么所謂人類的共同道德,就應該從人類這個族類的生存和繁榮來考慮。當我們在關懷人類這個族類的時候,有三個環節是必然會引起我們的注意的,這就是整個人類、民族和家庭;而家庭在人類這個族類或社會中是居在基層細胞的地位,它對人類社會的存在、延續和發展有著重大的作用。家庭或婚姻的形式,古往今來,雖隨著社會的發展而在改變,但我們只要稍微研究一下人類在兩性關系上的歷史,就可以明白:人類從最原始時期的雜交和亂婚,而血族群婚,而亞血族群婚,而對偶婚,而一夫一妻的家庭,不管家庭或婚姻的形式如何改變,但家庭總是存在著。因此,人類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家庭同樣還是需要的。
家庭,當做人類這個族類的基層細胞,在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社會主義社會里,才體現出來了根據自然本質而來的、最美滿的人類感情。組成家庭的主要成員,當然是夫妻;這正是我們大家提倡夫妻和睦、互相敬愛、互相幫助的道理,但是承認一夫一妻制的家庭是最好的家庭形式,是不是就可否認家庭中還有子女和父母之間的倫理關系呢?完全不是的。因為既然家庭中有了夫妻關系,自然而然會有上對父母下對子女的關系,永遠會有父母子女的關系。恩格斯說:“父母、孩子、兄弟、姊妹等稱呼不僅是一些表示尊敬的稱呼,而且是一種要求擔起一些完全確定和異常鄭重的相互義務的稱呼,而這些義務的總和便構成各處人民中間的社會制度重要的部分。”因此,搞好夫妻父母子女的倫理關系,鞏固家庭,對社會生活的正常化是很重要的。
在家庭的倫理道德方面,我國是有“孝”的傳統的。“孝”為什么會被封建統治階級利用來當做其鞏固統治的重要手段呢?這正是因為當做人類,子女和父母之間的感情本來是自然而然存在的。封建統治階級將父子、夫妻、兄弟、朋友這些人和人中間永遠不會沒有的關系,和君臣這樣統治和被統治的關系,或者統治階層中還有上尊下卑這樣的關系,放在一起,并且倒轉過來,又特別使父子的關系也好像是君臣的關系,于是在“百善孝為先”的吹捧下,使得每一家庭的男家長都成為“小君主”,因而也就成為“大君主”的普及而深入的支柱;這自然是使統治階級能夠鞏固統治的最可靠、最有效的手段。但是我們不應因為封建統治階級利用了“孝”而就抹煞了“孝”這個德目在人類的自然本質上是有根據的;我們更不應忽視“孝”在我國往時的勞動人民中的流行。除了迷信的、不科學的、有時甚至是很愚蠢的所謂“孝行”毫無提倡的必要以外,除了只顧父母而不知有國家社會是不足為訓的以外,的確也曾出現過許多足以動人的情節的;如像依靠自己辛勤的勞動所得,甚至寧使自己忍饑耐寒,而去奉養父母、奉養公婆,還盡量使得父母公婆在晚年獲得些精神上的快慰,這不能不說真正不愧為人類才能有的美德的。
當然,過去為了反對封建制度,就不能不反對封建道德;如像在“五四運動”之間及以后,“非孝”往往成為進步的論題之一,這是無可非議的。在革命的過程中,青年子女為了民族解放的事業,為了社會解放的事業,不能不離開家庭而投身革命;其中,有的家庭本來是反動的可不必說了;然而有的家庭本來也是勞動家庭,父母本來也是善良的人,只是因為革命青年將家庭的利益和革命的利益、和民族國家以至整個人類社會的利益權衡一下,也就不管父母生活怎樣,硬著心腸離開家庭,拋別父母,這也是無可非議的。后來,在革命隊伍里,在工作機關和學習機關里,在為了國家的經濟和文化建設而分配人的力量的時候,也還強調不要有家庭觀念。特別是“三反”五反”運動時期,黨號召和資產階級家庭“劃清界限”,雖在當時也巳說明了需要劃清的是政治界限,而不是指在日常
生活上和在家庭情誼上也非得“一刀兩斷”不可,但強調與家庭劃清界限這在當時也是無可非議的教育和措施。也正因我們有了這么一些歷史的和社會的原因,今天就更需要大家研究和倡導,來建立子女對于父母正確的社會主義道德了。
有人認為父母養育了我,我也養育子女也就盡了我的義務;至于反轉過來再去贍養父母,就并不是我的義務了。是的,從前只憑子女是父母所生,于是父母對子女就可隨意生殺予奪,或者必須根據“養兒防老、積谷防饑”這樣的原則來“報恩”,自然是荒謬的。但是我們也不同意用收入多少支出多少這樣的辦法來解決倫理問題,不同意只拿義務而舍棄一切人類感情來解決倫理問題。干脆些說,這樣的解決辦法正是從資產階級偷理觀點而來的。資產階級是提倡極端個人主義的,是以個人利益為中心的;只看父母當初為養育自己花了多少勞動力,這些勞動力值多少就報答多少,這豈不是商品買賣關系的反映?我們也并不否認父母早該為晚年生活有所積儲;然而今天當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還在艱苦奠立基礎的時候;當年老父母不可能都有職業、都有積蓄的時候,如果子女都不贍養父母,實際上是將贍養的責任推給了社會和國家,無疑是會損害社會主義的建設或者是會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的。我國婚姻法規定子女有贍養父母的義務,正是從整個社會主義的利益出發的。何況人類的感情,特別是父母子女這樣從自然本質而來的感情,除了不要以此而去妨害革命或者社會和國家的利益以外,是不應拿錙銖計較的辦法來對待的。人,因有思想,因有感情,所以人和人的相處也應該不同于一般動物,一般動物憑本能只能養育和衛護子女,而不會疼愛和贍養父母。是不是人的倫理也必須以此為止了呢!這是只有“撕破了家庭關系上面所籠罩著的溫情脈脈的紗幕,并把這種關系化成了單純金錢關系”的資產階級,才會這樣肯定的。人是不能像動物那樣生活的,也不是只有物質生活而沒有感情生活的。因此,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正是要使:我們的幼年,應該有美滿的教養;我們的成年和壯年,應該既有足夠的物質生活,也有美好的精神生活;而我們的晚年,就也應該既有溫飽而又有人情的怡悅,首先就是從子女而來的怡悅。我們絕不提倡大家庭和“五世同堂”等等,但是只要條件許可,將年老無依的父母接住在一起有什么不好呢,更不必說有屋也不讓父母住或將父母驅逐出門而令其流浪是太不合情理了。再說,就是將來社會主義甚至共產主義社會已經建立起來了,養老的設備都也已很圓滿了,但因為父母疼愛子女而子女也疼愛父母,老年父母喜歡長期的或臨時的住在這一或那一子女那里,這又有什么不好呢!
現在,按照婚姻法,我們必須肯定子女是有贍養父母的義務的。是的,贍養了父母,總不能不使子女的生活受些影響;因為父母年老了,總不會是壯健的勞動力,有的只能燒水煮飯和縫補衣服,有的只能看守門庭,有的耳聾目聵什么事都不能做,有的甚至經常臥病還妨害了子女的勞動,一切這些都不能不成為子女的負擔。然而我們是不能這樣來計較的;否則全都將父母的生活推給合作社,或者讓其在街頭流落,事實上是既不對家庭負責,也不對社會和國家負責了。
如上所說,子女對父母的關系,只有感情沒直義務是不對的,只有義務沒有感情也是不對的。真正的道德,應該是二者的結合,而不是兩者的分裂。我們現在是處在大變革的時代,因而在思想和習慣上,父母和子女間往往代表兩個時代,有的父母非常老悖,甚?,至對子女婿媳活潑愉快的新生活也表示不順眼,要這要那,罵東罵西,又嘮叨,又頑固,于是就阻礙了建立彼此間豐滿的感情;這也是事實。但是人和人之間的思想習慣總是異中有同而同中又有異的,就是拿夫妻來說吧,也不可能全都是永遠齊頭并進的;所以只要不是反革命的父母,子女也是可以和顏悅色對父母講些新道理的,有些事情也是可以容忍、可以遷就的。比如父母反對加入合作社,反對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就得勤勸力爭,但也不必動火;因為這些本來都是好事,父母遲早會領悟的。又比如父母每逢喜喪“大”事,就要大擺筵席,或者大做佛事、道場,自然也得勸阻,必要時甚至簡直可以不加理會,事后再一步一步進行解說。至于小事細節,甚至如像上墳燒紙、誦經吃素等等近乎迷信的待業,就不必太過勸陰,勸阻不聽也就算了。父母究竟是年老了,為了父母而忍些氣和生活多少受些影響,是不會永無止境的;然而由此在社會上而建立起來了人和人的融治氣氛和高尚道德,卻是有異常良好的后果的。
總之,在社會至義社會里,子女和父母之間的倫理關系怎樣建立,要根據理論,也要根據實際;要根據傳統,也要根據新的情況;要根據人的生活,也要根據人的感情。倡導子女愛養父母,也并不是定要將父母接住在一起,也并不是國家和社會需要我們離開家庭時也決不離開。但是愛養父母在社會主義里終究也是必要的美德,是仍必須加以倡導和發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