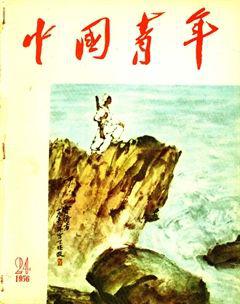第一棵圣誕樹
徐遲
“看!柴達木盆地。”
孫德和猛然煞了事,手指一指下面,這樣說。
我們是從敦煌出發,經過戈壁,而后從大鄂博圖的新壁公路,面上祁連山,盤旋在山中,終于到了當金山口的最高點的。
我們想望已久的盆地出現在眼前了。至今還是一個沒有解答的謎一樣的盆地啊!
顧教授,一個蘇聯的地球物理專家,下車就拿起他的照相機,湊到他繡花小園帽下面的,一雙閃耀的眼睛前,這頂維吾爾族的繡花小園帽是他剛從新疆克拉瑪依油田來的標志。他的翻譯小陸,一個眉清目秀的南方人,接著又給教授本人照了一張相,孫德和把“六九嘎斯車”車頭上的蓋子打開,讓水箱吹吹風。老章,我們的保衛員和我走到山口去了望。
在群山環抱的中間,一片絕平絕平的盆地一直伸展到遠方。我們大約是在四千公尺的高度,盆地的在三千公尺左右。高原的特點是百里見秋毫的,因此這巨大的盆地和點綴在它中間的小山都色彩鮮明地呈現在陽光中。
一眼看去,柴達木真像一只淡黃色的盆子。一座又一座山峰,像盆景,微呈紅色。使我們驚喜的是看見了兩個藍色的湖泊,藍得像一對眼睛。一種奇異的光彩在照耀盆地上的這一切:那是高原的光彩。
景色是這樣的安靜,并且秀麗得甚至可以說是嫵媚的,可是,這只有第一眼才是如此。觀看得稍久一些,那景色的安靜中就漸漸顯示出來了:這是死一般的安靜。如同看見一個已經逝世的少女,那秀麗與嫵媚也是虛幻的,沒有生命、沒有呼吸的,令人心悸,令人痛苦的。
在盆地中生活過的人前一天曾給我講過:在柴達木是寸草不生的。不僅沒有植物,并且沒有生物。它沒有任何生命。看見烏鴉從盆地邊沿飛向盆地中心去的時候,地質隊員就笑指著它們說:“你們,倒霉的烏鴉啊!你們將要餓死在里面了!”而他們說話是有根據的。他們事實上找到過這些饑渴而死的烏鴉。
在當金山口,祁連山從東蜿蜒而來,阿爾金山向西蜿蜒而去。山口自成兩山的分界線,在那兒休息過后,我們又登車,飛奔下山,直趨盆地中心。
我們的心情是又驚又喜的。這個烏鴉的故事弄得我們有點不安。因為,現在我們是落入這絕頂荒涼,真正荒涼的世界中間了。什么叫荒原?什么叫死谷?可以說,這兒就是。
當我們經過河西走廊的戈壁時,景色也是荒涼,不見人煙的。可是,那里至少還有駱駝草生長在沙土礫石上。這里卻速駱駝草也長不上。
“在那兩個湖泊里面”,我們的司機嘮叨起來,我們正向那一對藍眼睛飛奔:“含有一種化學成分,叫做什么硝酸鎂,還不知是氯什么鎂,反正我也弄不清楚。他們說這就是瀉鹽的成份。盆地里的許多湖泊,都是瀉鹽。我們初來時,迫不得已,只好喝它啊!天天喝瀉鹽,”于是做了個鬼臉,“可不得了。”
是的,在河西走廊上,只要有水,便是綠洲一片,生長很茂盛的莊稼,森森的樹林。而這里,有水也是鹽水,比海水還咸,有的成了苦水,不能喝,不能灌溉,里面沒有魚暇。
“簡直是什么生命也看不到”,一忽兒,顧教授感嘆起來,連連搖頭。“沒有飛鳥,沒有走獸,你們又說,沒有魚暇。多少年前,我曾在北冰洋上工作過。可是,北冰洋上還有企鵝、海豹,充滿飛鳥,走獸和水族動物,有村落又有居民,那里充滿了生命……”
“這里啊,我看,可太像月球了,”我肯定地說,
雖則我從來沒有去過那里。
“可不是?你看那些沙丘,你看!你看!就是像月球,”他同意了,雖則他也沒有去過那里。“可是,不要這樣說,”教授忽然又宣稱。“在這個沒有生命的地方已經出現了人的蹤跡。生命正向盆地進軍!我們,石油工作者,是在大進軍!”說到這里,教授舉起一根手指,向我們莊重地指出:“這里有石油!石油!這是最重要的。”
是的,我們不能不發現這個:生命正向盆地大規模地進軍。在我們面前,出現了這一條半個月前建成通車的公路。它平坦地,筆直地穿過盆地去。我們能看到逆著天空,地平線上的一隊隊的駱駝,在行進。它們是給遠離公路的工作人員運水送糧食和騎行的。而公路上一輛又一輛的載重卡車,揚起灰塵,隆隆經過,滿載乘客、滿載勘探器材。在有的卡車頂上,兩排鋼管挨著排列,好像“喀秋莎大炮”一樣。這里,那里,在荒涼的風景中,突然出現筑路隊、修路隊、測量隊、地質隊,各種野外隊的人員和他們的帳篷。這不禁使我們心中叫喚起來:敬禮!敬禮!三倍的敬禮!開發柴達木的人們啊!
后來,我們看見三個銀色的閃亮的大油罐,矗立在盆地的空曠的中心。它們旁邊站著個小小的紅色的加油箱。你立刻能聯想到,將來這里要矗立幾十、幾百個大油罐的。一忽兒公路上閃過“202隊”,“運輸處”,“區隊部”等等木牌和信號旗幟,那里都有成行成排的汽車,一大片一大片的帳篷。
孫德和忽然指著幾排磚木房屋說,“我們的基地。”自從我們進了盆地,他就自動地充當起我們的響導來了。但我們沒有聽懂,因此問他:“什么?”這時房屋已一閃而過。
“在這個地區要建設石油基地了,”他解釋,“將來的冷湖市就建在這里。聽說這里要有一個火力發電廠,還有什么煉油廠,總油庫……”
啊!這真叫人惦異!這樣看來,盆地里面的人已經在蘿想,不,不是蘿想,而是在計劃,在籌建未來的城市和工廠了,一一可是,這里出了石油沒有呢?要是出了,那日后這陌生的地名:冷湖,將成為我們的石油基地之一!
沒有在基地停車,我們一直去了冷湖的第四號構造——那兒一個產油區,聽說那里已經見了油。
到了那里,就再感覺不到什么荒涼和死寂了。這不但是一個帳篷城市,而且是整個文明社會。一個個帳篷里,有的在開會;有的在辦公;一個姑娘在搖計算機,一個很長很長的帳篷里,出售罐頭和酒,月餅和哈密瓜。冷湖鉆探大隊的杜隊長跑出來迎接我們。他安置了我們。他們給我們睡的不是帆布床,而是鋼絲床,被褥俱全。用晚餐時,開了兩瓶開胃的葡萄酒。而且,這恰是星期六晚上,廣播室的帳篷內很忙碌。兩個年輕的姑娘在挑選唱片,準備一忽兒舉行同末舞會。
生命在冷湖地區簡直是沸騰的。使它這樣的,正是教授莊嚴宣告的石油。將近兩年前,普查隊到了這里。當時,這湖泊連名字都還沒有呢。他們來到時,氣候正冷,就命名它為冷湖;普查隊在盆地到處取名字。那時,他們發現了八個儲油構造,可是他們還并沒有看見那些油苗。一直到一年半以后,今年的春天,地質部派了一個隊來詳查時,這次才在山坡上發現了瀝青,就打了一口地質井。這口井打到深三百多公尺時,噴了石油。
“油噴射時,高過二十多公尺,比哪一個大噴泉還大。地質隊員沒有準備,慌了。他們處理不了,就打電報找我們。”
杜隊長說,一邊說,一邊伴我們上山。“那時是五月底。六月初,我們來了。跟著,我們的鉆井隊也一個個地來了,這地區就變了樣子,現在快有兩千多人了。”
我們翻過一座矮矮的山,山下又出現了一片帳篷,從中一條公路引我們進一個紅色的山峰。我們看到了山坡上的黑色的瀝青,跟著到了四號構造的頂部,那里樹立著鐵塔似的一座石油井架。不遠處,還有兩座大井架。杜隊長先讓我看井架附近一個石碑似的用水泥封住的井口說:
“就是這并。它最初噴油的。井噴射時,有間歇,噴了一回停一回。我們趕到時,井已噴了幾天。后來就研究了它,趁它間歇的時候,用了四噸重金石將它壓住。這口井就封死了。我們開始打這口探井,”說著他把我們帶到了高聳三十公尺的井架底下。
“這口井打完啦?”我們問,看見它靜靜地站在那里。“完了,正在試油。”
“試出了油來嗎?”我們趕緊問。到柴達木之后,這是最主要的問題了。
“試了兩層,都沒有出油,”隊長回答,“現在要試第三層。”
你看得出來的,在這里所有的人都在等待著出油。所有的人都眼睜睜地看著這座井。新華社有三個記者在那兒等。所有的活動自然也都繞著這口井旋轉,甚至在夜深,帳篷群之間的一塊空地上,舞會已進行到了最高潮的時候,突然!唱片中途停下,喇叭里“汪”的一響,“咚咚咚”有人敲了敲話筒,于是出現了一個廣播員的女聲:
“同志們注意!馬上,隊上要試驗射孔槍,準備明
天正式射孔試油。請大家在聽到槍聲的時候,不要驚慌。不要驚慌。”
聲音重復了一次之后,舞曲的聲音才又重新流出來,它抑揚頓挫地迥旋在夜空中。在舞場上空懸掛著五彩的電燈泡,在它們照耀之下,盆地的生活是出奇地美麗的。人們在這樣的夜晚里,組織了舞會;居然還有自己的幾件打樂器,大鼓和鐃鈸,幫助唱片敲出舞曲的節奏來。當然這舞會并不是在細嵌木地板上舉行的。這是在柴達木的廣場上,舞興一濃,就要塵土飛揚。突然!
“砰!”
一聲巨響爆炸了。過了不一會兒,又傳來了第二聲巨響。預先有了警告的,舞會上的人聽到就滿不在乎。可是人人的心都飛到一號井去:不知道明天射孔以后,會不會有石油噴射?
可是,第二天,沒有等它射孔,我們就離開了冷湖,向青海石油勘探局的駐地芒崖而去。我們的工作很緊張,因為,教授是來檢查和幫助盆地中的地震勘探工作的;他要趕回北京去上課。
不待說從冷湖到芒崖三百公里的路上,又是一片荒涼的景色。不過,在路上,我們已以很不寂寞了。
“我們要糾正昨天的說法,”我說,“我聽杜隊長說這里不是完全沒有生命的。在盆地的南部,有水草可以放牧,而且有很多很大的蚊子,多得這樣,你一巴掌可以打死幾百個。有一次,一個同志打死了五百個,他只這么抹了一下……”
這時,忽然在前面的路上,有亮光在晶耀和閃動。仔細看去,盆地上處處都出現閃光,一直閃亮到天邊。車飛著,更多更多的閃光從遠處隨著地平線出現。車一直在光海中飛去,看得我們把蚊子的事情也都忘記了。“嘖,這是金剛鉆鋪起來的路,”我說,“漬!嘖!”
“是鹽的結晶吧,”小陸說。
“不,這是石膏的結晶,孫德和很有學問地回答。
啊,柴達木是多末神奇的地方!那閃閃發亮的是石膏的結晶,可是我們經過的又確實是一片產鹽的土地。有一大段路,車在鹽巴上飛駛。現在,高原的光在沙土上強烈地反射,大家取出了黑眼鏡來帶上。據說,最初有人曾因此而得了夜盲癥。
而車飛馳著,一忽兒我們又進入了一片流沙地帶。這卻是很可怕的經歷,初次看見這四面的沙丘。在流沙上面,形成的波浪竟然像水波一樣粼粼,可是這水波是僵死不動的。忽然,風一吹來,沙子卻叉亂舞超
最后,翻過一座小山之后,我們望見了一座這樣大規模的帳篷城市:芒崖。
在芒崖,成千座帳篷扎在昆侖山前。
這是最雄壯的景色:昆侖山,這是最美麗的城市,拓荒者的城市:昆侖山下的芒崖,高聳天際的昆侖山,一排幾十個峰,峰上疊峰。全部晶耀著積雪,一片大閃光。
我們都是在小學時代就從教科收上讀到這我國最偉大的山脈的,在神話傳說中我們也聽到過它,可是我們都沒有見過,誰也沒有想到過跑到這里來看看昆侖山的:它處在這樣遙遠的一個地方。然而,現在,它在我們面前,而它的面前是芒崖一堆一堆雪白的帳篷,和雪山交相輝映。
芒崖是這樣一座大城,當我們在這帳篷城內散步時,我們發現它不見得比青海省會的西寧舊城小了什么。驚人的事,是它已經不是帳篷城,因為它有不少新建房屋。電廠的煙囪高聳,機械廠的廠房雄峙。到了芒崖,我們沒有睡帳篷,簡直令人感覺到很遺憾呢。而且,我們在芒崖還在很漂亮的浴室內,洗了一個熱水淋浴,這簡直是極大的奢侈!
可是,柴達木是亞洲內部最大盆地之一:而盆地里巳發現了上百個儲油構造。幾個探區都見了油。見了油,自然芒崖要建設起來了;不僅有浴室,而且蓋起了高大的文化宮。一旦它出了油,更要大規模地建設。
在芒崖作了一些時間的停留之后,我們又有機會回到了冷湖第四號構造。
可以想像,我們一到冷湖,首先就要打聽,一號井究竟出了石油沒有?
在下面的地震隊里,傳說它已經出油,我們需要證實一下。可是我們不能不失望了。我們走的那天射孔之后,這口井的確噴出了一些石油,而且化驗結果,
(圖片見原版面)
芒崖的一角(新華社記者趙淮青攝)
質量還是好極了的。可是后來它噴出了大量的水和天然氣,又沒有油了。“不知是怎末回事?”杜隊長說,望著教授的臉。
在繡花小圓帽下的教授的臉思索起來。他表示,井下的情況總是很復雜的,像這樣的第一口井,自然不容易掌握它的規律。
當我們走到井前看看時,前幾天還聳立的井架已看不員了。一臺十五噸吊車正把它最后的部分拆除。
在井口,已出現了一套采油設備。頂上一只油壓計,下面是各種閘門。幾個巨大的圓盤和密封鋼管組成的一套設備在閃閃發亮。它的形狀非常精美,像一個個葫蘆疊起來似的,下面的較大,上面的漸小;也可以說它們像一座小寶塔。不過,它早巳有一個全世界通用的名字:對誕樹。中國石油工人也叫它圣誕樹。
而在柴達木,這可是第一棵圣誕樹——第一口生產井!
當時,這棵圣誕樹上,閘門關著。我們看到試油工程師申德斌正在換油嘴子。后來,我們問他:怎末啦?究竟怎末回事?
他已換好了油嘴子,讓工人打開生產閘門,于是我們聽到地下潺潺的奔流之聲。這潺潺之聲從鋼管中奔流通過,到附近兩個大油罐上面,深棕色的原油噴射了。
“這不正是油嗎!”我們一看就叫。
“看它能噴多久?”工程師冷靜地回答,睜著他的眼睛。
我們又一次失望了。石油噴了兩三分鐘之后忽然又沒有了,只見大量的水嘩嘩地流,天然氣一團團地奔騰。
申德斌解釋:根據電測資料來看,這一次他們射孔時,可能把離石油層只一兩公尺的高壓水層打開了,因此油給水壓住了,出不出來。他的計劃是用堵塞器來把高壓水層堵死。不過,這樣一來,得化上半個月的時間。
那一天,我們徘徊在井旁,繞著那第一棵圣誕樹轉,很沒精打采。
第二天清早,我們很早起床,準備出發到另一個地震隊去。
孫德和早已烤暖了,發動了他的車。天色微明了。帳篷之外,卻還冷清清的。我們把行李放上車,打算出發。
忽然,我們發現杜隊長的帳篷中燈光很亮,人聲不少,非常吵鬧,非常緊強,好像出了什么事。這時,有人從那里面奔跑出來,我們抓住這人就問:
“什么事?”
“昨夜兩點鐘以后,一號井就不再噴水,一直在噴石油。幾個小時下來,油罐都快滿了。”
“到底出了油!”我們興奮地叫起來。
一號井出油的消息,一忽兒已在整個冷湖傳遍,并且,新華社記者已經在擬電訊稿了。
“柴達木出現了第一棵圣誕樹!”我們跳上車,關上車門。“六九嘎斷車”發出一陣歡呼的震響,離開了隊部,向前馳去。車正對著積雪的阿爾金山。一道陽光投射到山頂,山頂顯出金光。接著,車拐彎向東,出現了畫中似的秀美的一條小山脈,中間挺立著幾座白色的奇峰。它們下面的平原上,將來會出現嶄新的城市。而整個畫面上,在高原的光彩中,像涂了一陣粉似的美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