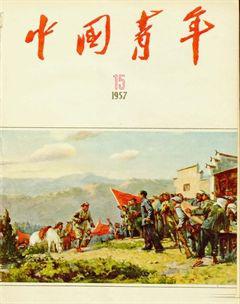在農業社安家的兩個姑娘
陳萱
我剛一到武漢團市委,就聽說武漢市15中學兩位教員的女兒已經自愿參加了農業生產合作社,從事農業勞動,于是我來到了武漢市郊區紅旗蔬菜生產合作社,訪問了她們。
這是一個涼爽的陰雨天,出來的時候還有些小雨,到了郊區雨已經停了。公路兩旁一望無際碧綠萬頃的菜園和禾苗被雨澆洗得綠油油的越發鮮潤了。從圖案式的豆架瓜棚里不時地吹過來一股股成熟了的黃瓜、豆角的誘人的香味。米黃色的蝴蝶繞著菜畦飛舞,使人眼花繚亂,藕田的荷葉上珍珠一樣晶瑩的水珠凝然不動,菜農們披著蓑衣赤著腳正在忙著整理被雨澆得倒歪了的菜畦和菜秧。從繁囂的城市來到這里使人感到心曠神怡。
“請問您,兩個參加農業生產的女學生在那里住?”
“你問的就是咱們社的江芙蓉和劉美言嗎?”一位老大爺笑呵呵地順手一指告訴了我。穿過一條遮滿了柳樹蔭的小路,我來到了一棟瓦屋的前面。房子的女主人是一個三十來歲健壯樸實的農村婦女。她親切地把我迎進了堂屋里的一間西套間。在這干凈樸素的小房間里我看見了兩個穿著勞動服的短發姑娘,一個正蹲著洗衣裳,另一個高個子姑娘手里捏著一大把信在看,高個子姑娘就是初中畢業生江芙蓉,她是個共青團員,今年18歲。矮個子的高小畢業生劉美言比她小兩歲。一個多月的農業勞動似乎已經使她們變得黝黑了些。
知道了我的來意之后江芙蓉把一大疊信退給我,用手指梳攏了一下短發,閃閃發亮的大眼睛流露出半喜半憂的神色:
“你看,我們正在發愁,同學們來了這么多信,叫我們怎么有時間回呢?他們問農業社歡迎不歡迎我們,有地方住沒有,勞動苦不苦。這些問題我們原來也有,所以我們很想把我們的情況告訴他們。”
她談到下鄉的時候,她的父親說她的身體不大好,不放心她來,有些熟人也告訴她們,說農村怎么苦,農民吃糠咽菜住牛棚。一個街坊撇著嘴譏誚她們說: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鄉里的姑娘都往外走,你們還往那兒去?但是她想到自己是個共青團員,吃點苦算什么?不能升學就應該帶頭下鄉。下來后生活是有些不習慣,吃水要自己挑,點的是昏暗不亮的洋油燈。但是并不像別人說的那么苦,現在對環境已經很習慣了。
她捏起拳頭在我眼前一幌又搖了搖手臂對我說:
“你看,我的胳膊有沒有力?下鄉以后我不但沒有生病,反而強壯起來了。我們的飯量也都增加了。”
劉美言洗完了衣服,整理了一下床鋪,坐在床上笑瞇瞇地參加了談話。
“我們未來以前最耽心的就是吃飯睡覺問題。農村又不比機關學校,也不像墾荒隊,既沒有宿舍又沒有食堂,我們在鄉下是匹馬單身,什么也沒有,在什么地方吃飯睡覺呢?難道說要帶著鍋碗瓢盆下鄉嗎?我們還害怕自己不會勞動,農民看不起。誰知道這些問題合作社早就替我們想到了。5月20日一清早,我們正要背起行李下鄉,合作社的社主任、黨支部書記、團支部書記、婦女代表七八個人接我們來了。到了社里,社員們馬上把我們領進了這間房字。我們在社員家里搭伙吃飯,伙食費也先不叫我們拿,由社里墊出來,等以后我們掙了工分再扣。青年生產隊還開了大會歡迎我們。在會上隊長、隊員互相介紹認識了。我們的女隊長祁幼仙犧牲午睡時間引我們出去認道,認識各種蔬菜。不幾天我們的心就安頓下來,以前的各種顧慮都無形消失了。”
殷勤的女主人給我們提來一大磁壺開水,送來兩把芭蕉扇。江芙蓉給我們每人倒了一杯水,她咕嚕咕嚕一飲而盡,又興奮地接著談起來:
“我們兩個每人有一個老師傅。生產的時候,師傅邊解釋邊做出各種勞動的姿勢教我們。比如鋤頭該舉多高才不累,鋤草時腰怎么挺起,草鋤多深才能保持土壤的濕度和不傷豆根。社員知道我們沒有種過地,沒有體力勞動的習慣,對我們的要求也是實事求是的。經常勸我們不要和別人競賽,累了就干得慢一些,有時還叫我們提前休息。我們倒覺得人家那么大年紀
的老婆婆都不休息,咱們年輕力壯的怎么能休息呢?看到我們干活被拉下了,社員們就來自動幫我們一把。社員愈是關心我們,我們愈覺得要好好干才不辜負他們的期望。
“另外我們還學了很多生產知識,比如蕃茄整枝只能留兩個主枝,其他的枝都要打掉,打枝怎么才能不損傷皮,蕃茄的枝怎么捆才能不松不緊,摘豆角為什么要先摘顏色發白的,留下顏色發綠的,怎么才能不碰掉豆花,打殺蚜蟲的1065藥水為什么要從枝葉下面往上打?咱們社生產的蔬菜作物有82種,不要說去掌握栽、培、生產這些作物的本領了,就是把82種種子辨認清楚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呀!我們在學樣里學的一點書本知識比起這些豐富實際的生產知識確實太少了。農民說:‘三年做個莊稼漢,十年難做菜園老。這句話是有道理的呀!”
“體力勞動現在已經習慣了嗎?”看著兩個女孩子仍然顯得有些稚氣的臉,我不禁有些耽心地問。劉美言卻搶著說:
“成!現在問題不大了。剛開始勞動還是覺得很累人的,胳臂腿都不習慣,全身發脹發酸,特別是在猛烈的太陽光下曬幾個鐘頭,頭暈暈的,臉上和身上的皮膚也發燒得有些刺疼,鉆在不大透風的豆架里邊摘豆角,汗水把雙層衣服都濕透了。但是曬過幾天脫掉一層皮以后再曬就不感覺那么疼了,頭暈也好些了。開頭,我們碰到最大的問題是晚上和青年社員們玩得很晚才睡覺,早上六點鐘下地起不來,常影響出工。后來團支部注意了這事,我們也早點睡,現在已經能夠在第二天打出工鐘以前就醒了。”
“想家嗎?”我故意逗她們一下。
一撇幸福的微笑浮上了江芙蓉的面龐。她搖一搖頭說:“不想,這兒就是我的家了。”她談起她們與社員們在勞動中建立起來的深厚感情:
“我在吳大娘家吃飯,大娘就像我的媽媽,有的時候生產累了我就不愛說話,吳大娘就心疼地問我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每頓吃飯,大娘總是給我揀我喜歡吃的蔬菜和鹽蛋。現在大娘正幫助我計劃掙了工分以后,秋上該添那些衣服呢!”
說到這里她有點不好意思似地停了一下:
“起初我們還準備試試看,只帶了個臨時戶口,合則留,不合則去,現在已經把正式房口轉來了。有時下雨天不出工回家去看看,社里叫我們第二天回,可是我們人在城里,心里卻老惦記著社,總是當天就趕回來。”
談了兩個小時,生產隊的兩個小伙子來叫她們了,我就辭別出來想到社辦公室去。路上一個十七八歲梳著兩個小辨身材苗條的姑娘一面送我,一面和我談。她驕傲地告訴我她們團支部為了安置學生下鄉做了許多工作:
“美言她們來的那天一清早,我們就忙起來,團支部書記段學機和團支部委員胡俊伶給她們騰房子、安床,生產的時候我們注意不讓她們太累,太疲勞。吃完晚飯我們就拿著報紙、口琴、二胡和她們一塊玩,以免她們感到生疏想家。”這時我想起了江芙蓉的小屋子和她們屋里大梁上掛著的二胡和桌子上的報紙,看了看這個天真熱情的姑娘,我想到組織上對人是多么關懷啊。
到社辦公室,黨支部書記舒浩瀚同志聽說我來拜訪這兩個小姑娘,很高興地向我說:“開頭,我們有些社員還懷疑合作社不一定缺乏勞動力,不大歡迎學生來。我們給大家算了兩筆帳:看問題要從發展上看,合作社要進行技術改革,準備逐步地把水田改成土豆與稻輪作,把旱地變成菜園,把粗菜地改成細菜地,還要多養豬,這樣活路多了勞動力就不足了。我們有兩個隊就今年還缺20個勞動力呢!再說,改革生產技術需要文化,這正是我們社的缺點。去年派了五個人去學習抽水機技術,五個人一路去一路回,兩個初中高小程度的,學的就比較快。多來幾個學生有什么不好?青年人嘛,只要肯吃苦,求進步,我們是歡迎的。這兩個女學生表現還不錯,她們對社有幫助,她們自己也找到了正確的出路。”是的,這兩位姑娘是選擇了正確的道路,我相信她們將會和千千萬萬走向農村的知識青年一樣,成為祖國第一代新型農民中的優秀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