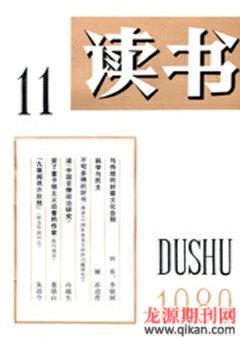中國美學史的先聲
陳鳴樹
中華書局最近出版的施昌東同志的《先秦諸子美學思想述評》,是為中國美學史宏偉結構打基礎的工作,也可以說是開中國美學史的先聲。
美學這門新興學科,在解放前雖然有少數人研究,但并不系統。解放以后,先是傳入了蘇聯的美學理論,但失之粗糙,教條主義習氣很濃,而且往往將文藝理論與美學理論混為一談,常常模糊兩者的研究對象。這個流弊,在后來我們不少美學論文中還存在。在五十年代中到六十年代初,美學在中國曾吸引了不少研究者,但因為開創階段,大都集中于名實之辯、概念之爭,這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當時報刊上爭得很熱烈,后來還編出了好幾本《美學討論集》記錄了這一盛事。接著就來到了十年浩劫之際,社會上的美丑都顛倒了,當然也不再會容許研究美學,現在該到了美學真正發皇的新時期。
中國人研究美學,不但要總結外國的經驗,當然更主要的還要總結自己民族的經驗。只有研究自己民族的美學傳統,總結出其特點、規律,才能對世界的美學理論增添新東西,才能有所貢獻。馬克思主義如果離開了自己的民族特點,就會失去生命力;而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美學理論的建立,也只有建立在我們民族的特點的基礎上。這應該從那里入手?應該從整理我們民族的美學的思想遺產著手,切不可忘了自己的老祖宗。
當然,這呼吁已久矣夫非一日了。由于上述的客觀原因,似乎至今還沒有見到有這方面的系統的著作出版。因此,施昌東同志這書,就開了這個先聲。自然,這還不是中國美學史的分冊,但這卻是中國美學史的扎實的基礎。如果循此一直寫到晚近,一定能夠成為一部很有價值的中國美學史的雛型。聽說作者雖以抱病之身,曾立下宏誓,有志盡瘁于此,我們祝愿他的成功。
本書的特點是:概念明確,邏輯嚴密,文字質樸,時有創見。作者不騖炫耀,不矜宏博,而是嚴格地從美學研究對象去鉤稽搜求,因此,讀者所見到的諸子美學思想,是真正的美學思想,不是引申意義上的美學思想。作者在這方面使用的概念十分明確。在先秦諸子中,“美”“善”不分,對“美”的概念使用還不十分自覺。因此,有倫理學意義上的“美”,有美學意義上的“美”,如不加以嚴格區別,容易含混,以致得出似是而非的結論。作者從分析概念出發,進一步區別概念的性質,這方法是可取的。例如,作者在分析孔子對“美”和“善”這兩個概念的不同的使用方式時,就總結出了這樣的規律:“如果說,使用‘善這個概念時,可以不顧事物的形式,而只顧事物的內容(道德思想、功用、價值等等),那末,使用‘美這個概念(美學的)時,就不能只顧內容不顧形式了。因而‘美這個概念嚴格地說是被用來從事物的內容與形式的統一上或從事物的具體形象上來反映和評價事物的品質的。”(第3頁)這樣,就把握了這兩個概念的特征,也進而把握了孔子美學思想的核心——對“美”的看法。
作者在分析諸子美學思想時,先求得諸子對“美”的看法,對“美感”的看法,然后及其審美評價,再及其對社會美、自然美、藝術美的看法,最后找出其階級根源和思想根源。將散見在諸子篇什中的一鱗半爪都匯集起來、理得清清楚楚,因此邏輯十分嚴密。作者又盡力從諸子的思想實際出發,不生搬硬套一些美學概念加以附會。
作者根據自己的分析,引出了一些獨創性的論點,是值得重視的。例如指出墨子的“非樂”思想“并不是一般地絕對地反對音樂活動、更不是一般地絕對地反對和否定音樂本身,他不過是反對‘王公大人違背‘仁者之為天下度也,違反‘先質而后文的做法而已。”(第41頁)又如肯定了法家美學思想的進步作用,指出“那種認為法家沒有美學理論,是文藝的絕對否定論者的觀點,是違背歷史事實的,毫無根據的。”(第151頁)而這種理論是相當流行的。“四人幫”利用法家大搞封建法西斯專政。但我們也不能因為“厭惡和尚,恨及袈裟”。作者所取的態度是科學的。再如,據作者分析,孔子和荀子都用“君子比德”的觀點來看待自然美,即認為自然物之所以美得為人們所觀賞,在于自然物本身的形象表現具有與人的美德相類似的特征,從而指出“這種對于自然美的看法,有其普遍的意義”,“所以自然美實際上是社會生活的‘美的一種象征或一種特殊形式的表現”(第3頁)。作者的這種觀點是前人未曾說過的。
當然,在這本書中,有些觀點我還不能茍同,例如,對孟子的“口之于味,有同嗜也”,完全簡單地歸之為人性論,否認不同階級之間有“共同美”存在,似乎還可以商榷;對韓非贊揚“燔詩書而明法令”的主張,也作為反復古主義來簡單肯定,不分析其另一面的反動性,似又失之過偏。不過這都是白譬微瑕。
作者在序言中談到自己是在與癌癥斗爭中完成本書的,同時據報導,作者又在這期間完成了另一規模巨大的著作:《“美”的探索》(上海文藝出版社印),提出了自己的美學理論體系。(見《復旦學報》一九八○年第一期的《學術流派評介》)。作者曾身處逆境,又為病魔蹂躪,還以這樣堅強的意志,頑強的工作精神,奮發有為地為祖國學術作出自己的貢獻,這就更加難能可貴了。
(《先秦諸子美學思想述評》,施昌東著 ,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五月第一版,0.52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