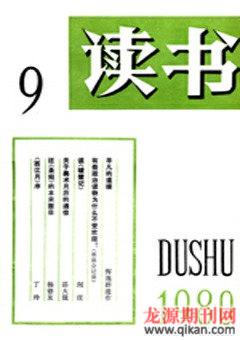光明的使者
劉季星
寄碧野同志
第四次全國文代會期間,讀完了你的新作《丹鳳朝陽》,這時正好你在北京,十多天內卻沒有機會到你的住處面聆教益。這部小說是你在十年浩劫期中頂住林彪、四人幫的種種壓力堅持著寫出來的嘔心瀝血之作,現在終于送到了讀者手上。雖然沒有來得及配上插圖,裝幀也并不精美,但我喜歡它,也為你感到高興。
你是勤奮的人。解放以來,你筆走龍蛇,寫出了一部接一部長篇小說,出了一本又一本散文集。先是《我們的力量是無敵的》。這部歌頌人民和人民軍隊的長篇,因為沒有按照某種模式描寫人物,被指為“歪曲”,遭到了“批判”。不久前讀報,得悉武漢的作家們有一次集會,為某些作家和作品“落實政策”,也宣布給你的這部作品“平反”了。其實最好的平反應該是重新加以出版。歲月如流,都快三十年了,特別是經歷了十年的黑暗時代,我們有許多年青的讀者恐怕連這本書的名字都沒有聽過,但它是你參加解放太原戰役在硝煙彈雨之中親身戰斗的記錄啊。接著出版的是《鋼鐵動脈》,然后是《陽光燦爛照天山》,都是數十萬字的巨著。還有幾本散文集:《在哈薩克牧場》、《邊疆風貌》等等。后來就是描寫鄂西北風情的《情滿青山》、《月亮湖》。單憑這些集子美麗的名字,也就可以想見其中的詩情畫意了。現在的《丹鳳朝陽》,又一部四十多萬字的長篇。這部作品是寫水庫建設的。你長期在水利工地生活,似乎已經被“同化”了,你也成了一名水利尖兵了。你用筆和墨為讀者建設了一座一座水庫,清亮的水灌溉著他們的心田,強勁的電力點燃著他們的智慧。讀者們將感謝你的勤奮。你的勤奮還表現在你對待生活的態度。解放后你們一家進行了三次大遷徒。北京有你的親戚故舊,有舒適的住宅,你卻舉家西征,千里迢迢,來到邊遠的烏魯木齊;習慣于拿碗和筷子的手,卻要學會直接抓飯吃。你們終于安下家了,楊靜同志還在庭院里經營了一架葡萄。而幾年之后,你們又從烏魯木齊折向東南,甘愿跳進長江中游一個大火坑,經受武漢酷熱的燃燒。上面草草列舉的那些作品,就是你們大遷徙的里程碑。此外還有一次掃地出門,那就不必去說了。家住城市,你更多的時日是在人民之中觀察,分析,學習。遙遠的邊疆,新興的工地,荒僻的山區,到處留下你的足印,也留下你的手跡。現在,你已六十開外,行動不便,但你并不因病弱之軀而稍有懈怠,或因寫了幾部小說而躊躇滿志,得意忘形,自以為了不起。你從來不想宣揚自己的什么經驗,更不會打開門來稱王稱霸,貶斥別人,吹噓自己,不可一世。你是勤奮的,又是謙虛的,樸實的。你的作品也是樸實的。
你寫《丹鳳朝陽》的時候,正是林彪、四人幫猖獗之際。你樸樸實實地按照你的信念寫作,沒有一點虛飾。你書中寫了大水庫工程局的黨委書記,寫了工程局的局長,副局長,又寫了總工程師和技術員。你不顧棍子、帽子以及隨之而來的更為嚴重的災禍,你把他們寫成如我們現在從作品中所看到的這個樣子。有人曾要你添上個“走資派”,把總工程師改成“反動學術權威”,你斷然加以拒絕。你忠實于生活,忠實于黨和人民所賦予作家的神圣的使命,忠實于一個正直之士起碼的道德,表現了你可貴的本色。在封建社會,有的知識分子還能夠具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操守,何況我們是在社會主義時代。可是人海茫茫,這世間畢竟還有無恥之徒啊。你這種精神不應該大大提倡和發揚嗎?你在書中也寫了不少先進人物:老工人,復員軍人,民工,還有工人家屬,你沒有拔高他們,神化他們;他們不是四人幫窠臼里不食人間煙火的泥塑木雕,而是有喜怒哀樂的血肉之軀。他們經歷了挫折和不幸,有過煩惱和痛苦,當然,也嘗到了成功的歡樂。你喜愛他們,他們是你的可以推心置腹的密友,不是你手中的木偶。我曾經零零落落地聽你談過黨委書記那間隨著工程進展而推移的板棚,總工程師床頭的兩架電話機。你終于把它們寫進了小說。還有一些動人的細節和故事你割愛了。但可惜小說里的黨委書記和工程局長在性格上沒有顯出各自的特點,形如兩人而其實是一人。寫賈有富為周麗芬所控制,二人合謀破壞大壩,沒有令人信服的根據;他們的行為不是他們的思想和他們所處的矛盾的合乎邏輯的發展。
我相信你是喜歡來鳳的。來鳳的形象寫得光彩照人。你寫的是水庫,對于開挖、爆破、澆灌等等技術操作十分熟悉,寫來得心應手,毫不費力,其實你著力的是在塑造人物,在表現人的精神。普希金曾經把他的一部長詩稱為“詩體小說”,這個稱呼的確切的譯法應該是“敘事詩”;而你這部長篇,真可以稱之為詩小說,或小說詩,是詩與小說的融合。水庫名叫丹鳳(這名稱多么貼切,又多么美),建設水庫的女技術員名叫來鳳;水庫的大壩高聳在大河之中,年青的女技術員也在藍天中展翅高飛了。來鳳就是羽毛華麗、在朝陽照射之下五彩繽紛的丹鳳。我還忘不了來鳳進山在金鼎房內憑窗遠眺山間月色那一段描寫,我似乎看到了朦朧的月光,聽到了淡淡的悠揚的笛聲;我還忘不了來鳳落水后千軍萬馬與激流搏斗救她脫險的描寫,紙上似乎發出了驚濤駭浪的洶涌澎湃的怒吼,仿佛映出了人人臉上緊張焦慮的眼神。你用筆細膩柔和,而又雄壯奇偉;輕描淡寫,卻力透紙背。兩者是矛盾的,但又是和諧的,自然的。
我應該告訴你,這部小說勾起了我的“鄉愁”。我在你現在居住的城市里度過了二十多個酷暑,它是我的第二故鄉。雖然盛夏的傍晚,擦一根火柴似乎可以把空氣點著,那里的氣候使人窒息,但一旦離開,卻又不勝依依。“故土堪憐雖可恨,他鄉似主卻如賓”,感情竟是這樣的復雜。你當作丹鳳水庫描寫的那座水庫,我沒有去過,但我曾在它所在的縣城住過,在它附近的崇山峻嶺中走過。你筆下出現的人物和風景,使我感到十分親切,我相信也會使我的“鄉親們”感到更加親切和可愛。現在鄂西長江上正在興建一座比丹鳳水庫大壩更加宏偉的大壩,無數丹鳳正在那里展翅欲飛,她們讀了你這部小說一定會得到很大的鼓舞。她們,還有我們,更盼望著你的醞釀中的新作問世。我知道你正在構思一部反映架線工生活的小說。架線工是水庫和城鄉“千里姻緣一線牽”的使者,是光明的使者,他們為水庫輸送電力開辟坦途,架設線路,把每座工廠的機器開動,把每家的黑暗驅散。他們是值得尊敬的人。——可是,有誰會不以為你們作家也是值得尊敬的架線工,那光明的使者呢?
197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