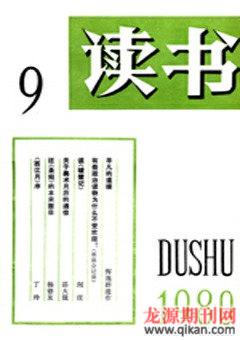可敬的人!
彥 火
《當代中國作家風貌》代跋
在那些灰黯的年代,有不少文藝家為真理、為國家民族而殉難。
在中國,遠的有屈原、司馬遷,近的有在戰爭里犧牲的文化戰士,最近的有在一九六六年開始的十年文化浩劫中被迫害的大量文藝工作者。
有些是以死諫君的,有些是被殺害的,有些是自殺的。
有一些日子,讀了不少紀念在“四人幫”時期被迫害而致死的文藝工作者的文章,心情是沉甸甸的。
在殘酷的現實面前,有時是很令人氣喪的,但是,卻也有那么一些人熬過來,而且在白色恐怖下象小偷(黃永玉語)那樣進行忘我的創作。
巴金在那段被無情批判打擊的日子里,爬上汽車房,埋頭翻譯俄羅斯民主主義作家赫爾岑的回憶錄《往事與隨想》(全書分五卷,計一百五十萬字);姚雪垠在“五七干校”勞動時,爭分奪秒地繼續未完的《李自成》長篇歷史小說;艾青受排擠,在邊遠的新疆寫著小說;丁玲舉著不靈,胸懸木板不忘創作……。
他們在波濤洶涌的年代,沒有逐浪而去,也沒有在兇險的生活怒濤中沒頂,宛如從狂
這些人,并不遙遠,都是我們熟稔的文學家、詩人,而且都在我們的中間,都是受到廣大讀者擁戴,可親可敬的人!
想到他們,我總是聯想到羅曼·羅蘭筆下的克利斯朵夫。
克利斯朵夫永遠在經歷磨難,在接受磨難;而且永遠在黑暗的生活里追尋藝術的光與熱,他有一股不屈不撓的活力,他說:
“與其靠幻想而生存,毋寧為真理而死滅……可是,藝術,難道不也是一種幻想嗎?不,藝術不應當成為幻想,而應當是真理!真理!睜大眼睛,從所有的空隙里吸取生命底強有力的氣息,看見世界萬物底真面目,正視著人間的苦難——然后放聲大笑!”
這是偉大的生活態度,永遠不屈服于環境,永遠開拓新的生活。但,中國的文藝家,他們的經歷,比之克利斯朵夫來得更迂曲,更坷坎,更攝人心魄,他們受的打擊是暴烈的,不僅僅在精神上,還在肉體上;不僅僅是身心的摧殘,還有政治的迫害……。克利斯朵夫所經歷的,他們經歷過,克利斯朵夫所沒有經歷過的,他們都經歷了。他們之中,不少人具有“死守真理,以拒庸愚”(黃耘語)的大勇主義精神。
如前面提到的,我們的文學家并沒有在苦難的面前倒下,而是煥發出更強大的生命力。七十五歲的巴金還在構思長篇小說;年逾花甲的艾青要求寫出更多更好的詩;端木蕻良在得了冠心病后,還在奮力撰寫長篇歷史小說《曹雪芹》;丁玲雖患了糖尿病、乳腺癌,仍矢志要完成長篇《在嚴寒的日子里》的創作……。他們爭分奪秒地與生命競跑,作出壯烈的沖刺。曹禺說:“對于我們這樣的老人說來,時間,是不能以每一頁日歷來計算,而要以一小時、一分鐘、一秒鐘來計算的。”
正如克利斯朵夫說的:“我是永久的戰斗。”我們的文學家,無愧于文藝戰士的稱號,他們進行永不疲憊的筆耕,為我們的文藝增添更多的資產。
每次看到他們的文章,都使我全身的血液升騰起來。
懷著欽敬的心情,近年在多次的回中國大陸參觀訪問中,欣幸地會晤了一些當代中國畫家,親炙著這一顆顆偉大而火熾的心靈——他們還來不及醫好心靈上的創傷,對新的創作、新的理想、新的生活,已灼灼地燃起熾旺的熱情之火,寫下不少振奮人心的新篇章,令人雀躍、歡快。回來后,曾寫了一些“作家印象記”、“作家散記”和“訪問記”,發表在報章和雜志上。當時發表這些文章,意在將中國作家的一些新動態,及時向海外關心的讀者作一報道,并不預備結集出版的。后來劉以鬯先生一再鼓勵和慫恿,并為之薦引出版社,增添我匯集成冊的信心。劉先生古道熱腸,感人肺腑。
本書所收的文章,大部分都經過作家的親自過目、勘正。在這里要特別感謝巴金先生,他在百忙中為我補上《巴金創作年月表》遺漏部分;蕭乾先生在七九年十二月從美國愛荷華返國經港時,為我和梅子兄提供了不少有關他創作活動的詳細資料,使我們得以編成《蕭乾年表簡編》;著名詩人艾青及其夫人高瑛女士,一開始便給予深切的關注。此外,著名作家葉圣陶、俞平伯、端木蕻良、卞之琳和黃秋耘等,都在繁忙中親自為拙作勘正。
在成書的過程中,還得到范用兄、蘇晨兄和晴野兄大力協助支持。梅子兄曾為這本書的出版,花過不少心力。此外,還有不少遠近的朋友的關懷,在此一并致以深切的謝忱。
最后,尤其要特別提到的是,這本書如果沒有得到昭明出版社呂思齊先生的應允,難以面世,筆者的感激自然也是言之不盡的。
本書的體例不求一致,因為一方面正如前面所述的,開始時并不打算寫成一本書,另一方面也想寫得多樣化和靈活點,以免流于枯燥、刻板。
由于作者識見有限,謬誤在所難免,尚祈文化界前輩、讀者指疵。
一九八○年三月三日于香江
(本書已由香港昭明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