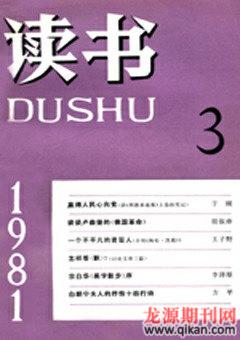割掉“尾巴”
柳 松
一個人如果屁股上真的長出一條尾巴,那該是多么的不雅相?!不消說,他是千方百計也要到醫院請大夫幫他割掉的;一本書如果屁股上真的也長出一條“尾巴”,那又怎么樣呢?當然也不美觀。可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在十億人口的大國,著書立說者當然大有人在。我就發現,幾乎很多書里都拖著一條粗處、長處、顏色……猶如一個模子里脫出來的尾巴。
我是教書的。要當好先生,必須首先當好學生。我的職業使我養成了一個讀書的習慣。每當新書一到手,我總是要先看看“序”或“跋”(有的叫“出版說明”,也有的叫“開頭的話”)。因為它能使我對該書先有一個概括的認識。可是在讀它們的時候,我驚異地發現在文章的末尾,總是要拖上這樣一條尾巴:
“由于時間倉促和限于作者(或編者)水平,書中缺點錯誤,在所難免,敬請讀者批評指正!”
不管該書的體裁、題材如何,也不管該書是洋洋數萬言的大厚本,或僅僅只是寥寥數十頁的小薄本,作者都喜歡人為地給自己的書添上那么一條“尾巴”,好象書的“序”、“跋”、“前言”、“編后”中沒有這條“尾巴”,就很對不起人,“書”也就會黯然失色似的。這究竟是為什么?真叫人百思莫解!
也許有人會說:“這有什么費解的,這‘尾巴正好表明作者(或編者)謙虛的美德唄!”
對這種似是而非的解釋,筆者是不敢茍同的,因為這條“尾巴”,它至少引起我下列幾點疑問:
一、“由于時間倉促……”既然明知“時間倉促”,那為什么不可以“從容”一點,讓“時間充裕”一點,以便深思熟慮、反復修改后再出版,而偏偏要“倉促成書”呢?是上邊硬性規定非得要在某年某月某日以前把書拿出來呢,抑還是作者(或編者)由于“發表心切”而“倉促”出書?
二、既然書中有“缺點錯誤”是由于“時間倉促”這個“客觀”原因所引起,而不是由于作者的“主觀”原因造成,那么,讀者又憑什么要對該書的作者(或編者)進行“批評指正”呢?因為一切后果和責任都應當由“時間倉促”來負才合,理嘛!
三、“限于作者(或編者)水平……”這句話貌似謙虛,實則多余。為什么呢?因為“水平”是沒有止境的,“水平”的高低,都只不過是相對而言。世界上除了“夜郎國王”,相信絕不會再有第二個人敢于狂妄地宣稱自己的“水平”已經達到“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地步了。因而作者(或編者)“水平”究竟是高是低,不同的讀者,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讀后是會得出不同的結論的,大可不必加以申明!
再說,我國的憲法或出版法中,也還沒有“水平低的作者(或編者)不準出書”的規定,那么,既然書都已經出了,又還何必再去談論“水平”的高低和“有限”、“無限”呢?!
三、“缺點錯誤,在所難免”的說法,也無必要。因為人非圣賢、孰能無過?既然已經承認世上沒有十全十美的完人,那么,按照普通的邏輯常識,人們又怎么可能去苛求“非完人”的作者去寫出“完美無缺”的作品來呢?
四、“敬請(或“歡迎”)讀者批評指正”。這句話中的“讀者”二字,也是有點失之籠統。一本書問世后,凡是有責任感的讀者,讀書時一定很仔細,而且善于發現問題,一當發現書中有“缺點錯誤”后,即使你不“敬請”、不“歡迎”,他也要給你指將出來。問題不在于你加不加上“敬請”(或“歡迎”)“批評指正”這一條尾巴,而在于讀者的責任心。責任心強的讀者,你不加這條尾巴,他也會給你“提出批評指正”(如果書中確有“缺點錯誤”的話)。如果碰到只想“隨便翻翻”的讀者,那你就是用大號黑體字印上幾百個、幾千個“敬請批評指正”的話也不頂用。
看來這條“尾巴”在很多情況下只是“正確的廢話”,那么,讀者就完全有理由期望于作者(或編者)今后在寫書或編書時,還是把這種既古老而又“時髦”、雖正確而又多余的“尾巴”給割掉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