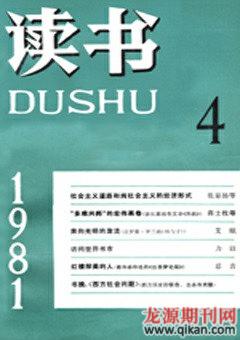一九八○年美國報刊推薦的最佳作品
涇 人
最近,美國《時代》周刊刊登了該刊選擇的美國一九八○年最佳小說和非小說類作品,各五本。
小說類中有托瑪斯·伯杰(Thomas Berger)的超現實主義的喜劇作品《鄰居》(Neighbours)。小說的主人公厄爾·基斯和妻子埃妮德住在遠郊富人區的一條死巷里。厄爾·基斯已過中年,時時為肥胖而擔憂。一次,基斯隔壁搬來了一對年輕的夫婦哈里和拉蒙娜。基斯本來希冀過一個平靜的星期五晚上,不料鄰居拉蒙娜未經邀請便前來登門拜訪。當時埃妮德正在廚房執勺,而這位新來的不速之客卻大膽地毫無顧忌地以色相惑人。他邀請拉蒙娜留下用餐,但家中除凍豆煮新鮮玉米之外,別無佳肴以款待來客。接著哈里也出場了。這位長著一頭金發、身體十分健壯的鄰居立即接受拉蒙娜傳達的留下用餐的邀請。基斯處境十分尷尬。這時,哈里了解到主人的難處,主動提出基斯給他錢和小車鑰匙,由他去購買現成烹調好的食品。但基斯心中有所戒備,不敢輕易將錢和車鑰匙交給一位素昧平生的客人。
不久,客人現出了原形。拉蒙娜無中生有地指責基斯強奸了她,哈里控告基斯曾經想同他搞同性戀。糟糕的是,埃妮德一概信以為真。基斯這時不得不下逐客令了,但客人逐而復來,堅持不走。無奈之下,基斯給老朋友們打電話請求援助,至少先得設法將這兩個惡棍逐出家屋。一位老朋友回答:“我不想那樣做。那會叫我厭煩的,而叫我厭煩的事兒,只要可能,我從來不做。”另一位老友,一個汽車修理工,干脆臭罵了他一頓。這時,他的女兒因偷竊被學校開除回到家來。她非但不同情父親,反而跟著鄰居為虎作倀。這使基斯傷心透了。基斯這時悟出了一個道理:他越請求別人援助,越招來眾多的煩惱。他只是想保護自己,結果卻使自己和整個世界對抗起來。人心的不古和險惡,是這部作品的主題。這場鬧劇就是源出于這一可怕的社會弊端的。
這是伯杰自一九六四年《小小大人物》(Little Big Man)以來,寫得最為成功的黑色幽默的小說。
作家莫臺卡爾·利克勒(Mordeca1 Richler)的第八部、也是他寫得最成功的一部作品《喬夏的昨天和今天》(Joshua Then and Now)名列第二。喬夏·夏庇若是蒙得利爾作家和電視片制作人。喬夏和作家一樣,生長在蒙得利爾底層猶太人聚居區。他父親魯本原先是個拳擊運動員,干過販運私酒的買賣,也幫別人收過債務。他母親曾在夜總會跳脫衣舞,也演過黃色淫穢的戲劇。喬夏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的,他曾經是浪跡街頭阿飛中的佼佼者。后來,他大多數幼時的朋友都混得不錯,成為蒙得利爾富有階層中人,在地毯、掛毯、珠光寶氣之中失去“自我”。
喬夏的嬌妻鮑琳是麥肯齊·金總理內閣閣員的女兒。喬夏在這位政客家里目睹了欺詐、貪婪、淫蕩縱欲的種種穢行。利克勒著意描寫了鮑琳的弟弟,他是費茲杰拉德筆下的那種嬌子,腐朽到了極點。利克勒的小說在三十和四十年代的蒙得利爾,五十年代的倫敦和西班牙之間縱橫馳騁,交替敘述。他描寫了喬夏在倫敦的一位朋友默多克,一個與世毫不妥協的天才作家;年輕的喬夏在伊比扎寫國際旅歷史時認識的農民和漁夫;以及喬夏的靠兩個拳頭吃飯的善良的父親魯本。魯本是這部小說中刻劃得最為成功的人物。
作家通過喬夏的生活,展現了一幅國際社會的壯闊的圖景。他用喬夏的嘴表達了自己的思想:“不要過于苛求于我們。”作品中既有含情脈脈、細膩的感情描寫,也有粗獷的、狂野的生活的敘述:人的生活本來就是復雜的。在這樣一個光怪陸離的世界中混跡到四十七歲的喬夏領悟到一個真理,即人生中最重要的品德便是忠于家庭和朋友,這種美德足以使人處于飄忽不定的亂世而立于不敗之地。
其他三本最佳小說是美國小說家、以一九七○年《丹尼爾之書》(The Book of Daniel)一舉成名的多克托羅寫的《潛鳥湖》(LoonLake);意大利著名作家意大洛·卡爾維諾(Italo Ca1vino)的《意大利民間故事集》(Italian Folktales)和美國南方女作家尤多拉·韋爾蒂(Eudora Welty)的《尤多拉·韋爾蒂小說集》(The Collected Storiesof Eudora Welty)。
在非小說類佳作中,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教授卡爾·肖斯克(CarlSchorske)著的《維也納的世紀末:政治和文化》(Fin-de-SiècleVienna:Po1itics and Culture)是一部寫得很精辟的著作。它由七篇論文所組成。肖斯克試圖在他的論文中表達這樣一個哲理:如果文明是按少數人的意志馴化大部分人的力量的話,那么,人們完全有理由假設少數人的事務就是節制那種時而影響大部分人的黑暗的、不合理的勢力。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那文明本身便會遭到破壞。在作品中,肖斯克縱談了一八六○年到一九一四年維也納的文化革命,以他的博學,分析了上世紀末在維也納盛行的政治上的理性自由主義和藝術上的唯美主義思潮。肖斯克在文章中分析了維也納分離派的活動。古斯塔夫·克利姆特為了反對奧國學院派的保守主義,于一八九七年開創了分離派運動(Vienna Secession)。他主張:藝術要“探索現代人的真實面目”——換句話說,探索一種表達現實的新的藝術形式。和奧地利作家阿瑟·施尼茨勒一樣,克利姆特立志探索“在舊有文化廢墟滋生的精神人”,即本能的人的面目。
肖斯克還談論了維也納的獨特的建筑藝術。他認為,始于一八五七年維也納建筑設計上的改革導致了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維也納政治和藝術的演變。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著名奧國建筑師奧托·瓦格納就主張“需要是藝術的唯一伴侶”。肖斯克十分贊賞他追求建筑——也即藝術——的有效性、經濟和方便的努力。
肖斯克文章之所以引起美國評論界和讀書界的重視,就在于它的獨特的分析和見解。肖斯克著重分析了奧地利作家、小說《埃爾澤小姐》的作者阿瑟·施尼茨勒和奧地利頹廢派詩人、詩劇《提香之死》的作者雨果·馮·霍夫曼斯塔爾的作品和生活。他還闡述了奧地利精神分析學派創始人弗洛伊德的《釋夢》。
在這部著作中,肖斯克描寫和闡述了維也納藝術和科學發達的歷史過程,并指出,在這整個的進程中,同時也布下了奧地利后期專制制度的種子。
華裔女作家馬克辛·洪·金斯敦(Maxime Hong Kingston)近年來引起美國讀書界的矚目。她的作品都是自傳性的,主題旨在描述在美國長大的中國人的價值觀念。她的《女戰士》(The Woman War-rior)被認為是美國七十年代的佳作。現在,她的《中國的男子》(ChinaMen)又成了一九八○年的名噪一時的作品。
作品把讀者帶到本世紀初期的加利福尼亞州斯托克頓城的一家洗衣房里。當洪·金斯敦還是個小姑娘的時候,她時常呆在一旁望著父親洗衣服,干著苦役般的累活。他父親在中國原來讀過些古文觀止之類的書,能吟詩作賦,頗有點文氣,所以,一度陷于這種困境,不免有懷才不遇之感,常常長吁短嘆,心中郁郁不樂,故而脾性暴烈,時時詛咒。他的最狠毒的咒語莫過于辱罵婦女身體的話。這小姑娘懂得這些話的含義,但感到迷惑不解。她一次對父親說,“我們曉得,要養活這一家子人,難為你了。”她接著說,“但我希望你告訴我,這些咒語只是中國人通常罵人的話。你并非是真想污辱我的,使我感到做個姑娘是件叫人羞愧的事。”
作品又突然回敘到舊時的中國。她父親兄弟四個,排行最小。她懵懵懂懂的祖父稀里糊涂將兒子和別人換姑娘。纏小腳的祖母當然不依,將兒子追回,氣憤地對男人說,“死鬼,將男兒換個女奴。傻瓜!”后來,就是這位意志堅強的婦女強迫她丈夫離家去美國謀生。“掙錢去吧!別在家白吃飯了!”
于是洪·金斯敦的祖父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來到內華達山脈修筑中太平洋鐵路。他馬上就被錄用了,據說是因為“中國男子漢的天然的爆破才能”。中國的男子漢們在那兒干著非人的勞動,時刻有送命的危險;美洲大陸兩岸終于被鐵路接通了,而中國男子漢們也就成了多余的人,不再受歡迎了。
洪·金斯敦的一位祖輩于是到夏威夷為人清理土地、種植甘蔗謀生。他最痛恨的是莊園主不許工人工作時講話。洪·金斯敦寫道,“他多么需要放聲大喊,以表示他的思緒啊。中國的男子漢們拚死拚活地干,但他們遠離自己的家,太寂寞了。他們在富饒的甘蔗地里挖了一個大洞,在洞周圍跪下來,凄涼地唱道:“我想家,家,家,家,家,家。”
洪·金斯敦的筆調有時是憤懣的,有時是沉靜的,有時是幽默的,有時又是充滿激情的,那些在美國的中國男子漢們的命運深深地扣動讀者的心弦。
其他三部非小說類的作品是:羅納德·斯梯爾(Ronald Steel)的《沃爾特·李普曼和美國世紀》(Walter Lippmann and AmericanCentury);斯塔茲·特克爾(StudsTerkel)的《美國之夢:消逝的和重新找到的夢》(American Dreams:Lost and Found);以及曾獲得普利策獎的賈斯廷·卡普蘭(JustinKaplan)的《惠特曼:他的生活》(Walt Whitman:A Life)。
另據報道,最近全美書籍評論家協會的二十一名成員評出謝利·哈澤德(Shirley Hazzard)的現代愛情小說《轉運的維納斯》(Transitof Venus)為一九八○年最佳小說;羅納德·斯梯爾的《沃爾特·李普曼和美國世紀》為最佳非小說類作品;弗雷德里克·塞德爾(Fre-derick Seidel)的詩《日出》(Sun-rise)為最佳詩歌;海倫·文特勒(Helen Vendler)的《既有自然,也有我們:美國現代詩人》(Partof Nature,Part of Us:ModernAmerican Poets)為最佳文藝批評作品。得獎作家于今年一月二十二日在紐約領取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