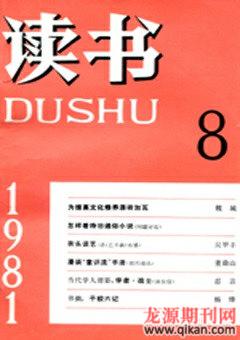魯迅與《良友畫(huà)報(bào)》
馬國(guó)亮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五日,當(dāng)時(shí)任《良友畫(huà)報(bào)》主編的梁得所,邀了畫(huà)家司徒喬同往拜訪魯迅。其時(shí)魯迅和良友還沒(méi)有業(yè)務(wù)上的關(guān)系。梁得所也未正式和他會(huì)面過(guò)。和魯迅早有來(lái)往的司徒喬,卻是常到良友來(lái)走動(dòng)的熟朋友;因此梁請(qǐng)他同去引見(jiàn)。梁素來(lái)崇敬魯迅。作為后學(xué),他想拜見(jiàn)這一位文壇巨匠;作為畫(huà)報(bào)編輯,他想得到魯迅的照片刊在畫(huà)報(bào)上。他帶去了一本畫(huà)報(bào)和自己的一本出版不久的散文集《若草》。和魯迅見(jiàn)面后,交談之余,送上了畫(huà)報(bào)和散文集,順便提出了照片的要求。
魯迅翻看了幾頁(yè)畫(huà)報(bào)后,便笑著說(shuō):“這里面都是些總司令之流的名人,而我又不是名人哩!”
當(dāng)然畫(huà)報(bào)登載的不少是新聞人物,魯迅的話也說(shuō)得很有意思。梁得所避而不談什么名人問(wèn)題,只對(duì)他說(shuō),讀過(guò)他的著作的人,一定都很想認(rèn)識(shí)一下作者的容貌,因此希望能在畫(huà)報(bào)上介紹。
魯迅便說(shuō),“近來(lái)我實(shí)在有點(diǎn)害怕,”他從抽屜里抽出一封信,“這是一個(gè)不認(rèn)識(shí)的人,從杭州寄來(lái)的。信里說(shuō)什么孤山一別……,可是我實(shí)在從未到過(guò)孤山。前幾天又接到北京朋友拍來(lái)的一封電報(bào),說(shuō)是聽(tīng)說(shuō)我死了。我不明白這些話是那兒來(lái)的。若是《良友》又發(fā)表我的照片,我的敵人不免要說(shuō),咳!又是魯迅,而攻擊造謠的更多了。”
話雖如此,梁得所終于說(shuō)服了魯迅。這是很不尋常的事情。因?yàn)椴坏絻蓚€(gè)月后,李金發(fā)曾請(qǐng)魯迅為《美育》撰稿,并向他討照片。魯迅給他回信說(shuō),“……至于將照片印在刊物上,自省未免過(guò)僭。希鑒原為荷。”可見(jiàn)魯迅不是隨便答應(yīng)的。魯迅當(dāng)時(shí)手頭上沒(méi)有現(xiàn)成合適的照片,便約好司徒喬給他畫(huà)個(gè)速寫(xiě)。三天之后,司徒喬再到魯迅寓所,把速寫(xiě)畫(huà)好了。這時(shí)梁又想到,畫(huà)像只能表現(xiàn)本人,照片卻可以反映本人的生活環(huán)境。假使既有速寫(xiě),又有照片,讀者一定會(huì)更為高興。因此他又征得魯迅同意,三月十六晚帶了個(gè)照相機(jī),再到魯迅寓所,給他拍了四張照片,都是在他的書(shū)房拍的。一張站在書(shū)櫥前,其他三張都是坐著的。刊登時(shí)只選用一張。梁當(dāng)時(shí)還請(qǐng)魯迅寫(xiě)一篇自述,魯迅沒(méi)有答應(yīng),卻同意使用原來(lái)在《語(yǔ)絲》刊出過(guò)的一篇簡(jiǎn)傳。這樣,一張司徒喬的速寫(xiě),一張梁得所拍的照片,附一篇轉(zhuǎn)載的小傳,和梁寫(xiě)的一篇訪問(wèn)記,便在同年四月三十日出版的《良友畫(huà)報(bào)》第二十五期刊出。司徒喬的速寫(xiě)像,筆力剛健,很能表達(dá)出魯迅堅(jiān)強(qiáng)不屈的性格。整個(gè)臉部的輪廓,比他本人稍胖,神似多于形似。梁得所拍的照片,則表現(xiàn)了人物生活和典型環(huán)境:魯迅坐在書(shū)桌旁邊的藤椅上,略靠左。姿勢(shì)和神態(tài)都是我們平日最常見(jiàn)到的那樣。背景是一列書(shū)櫥。書(shū)桌放了幾張稿紙。從藝術(shù)上說(shuō),這照片是樸素的;從內(nèi)容說(shuō),卻是給我們留下的與魯迅生前的風(fēng)貌非常接近的肖像之一。
梁得所于一九三三年夏離開(kāi)良友,另行創(chuàng)辦大眾出版社,出版畫(huà)報(bào)及其他期刊。他再度請(qǐng)魯迅給他主編的《大眾畫(huà)報(bào)》寫(xiě)自傳,寫(xiě)他成功的經(jīng)過(guò)。魯迅也沒(méi)答應(yīng),只是后來(lái)給大眾出版社的期刊《小說(shuō)》半月刊(麗尼、黃苗子合編)的扉頁(yè)題詞,寫(xiě)了“明眸越女罷晨裝”一詩(shī)。此詩(shī)最初是寫(xiě)給日本友人森本清八的,這次再為《小說(shuō)》題扉。用后黃苗子將原稿保存,不幸在抗日戰(zhàn)爭(zhēng)中丟失了。現(xiàn)在我們看見(jiàn)的手跡,據(jù)說(shuō)都是從《小說(shuō)》半月刊中翻制的。
到了三十年代,魯迅開(kāi)始和良友有了業(yè)務(wù)上的聯(lián)系。趙家璧主編《良友文學(xué)叢書(shū)》,經(jīng)鄭伯奇的介紹,魯迅把他的蘇聯(lián)譯作《豎琴》和《一天的工作》交給《叢書(shū)》。不久又應(yīng)邀參加《中國(guó)新文學(xué)大系》的編選。另外,還為德國(guó)麥綏萊勒的木刻連環(huán)畫(huà)《一個(gè)人的受難》寫(xiě)序文。一九三六年二月,蘇聯(lián)版畫(huà)在上海展出。這一個(gè)集許多蘇聯(lián)著名版畫(huà)家的作品展覽,轟動(dòng)了上海文化界。在魯迅的鼓勵(lì)下,良友后來(lái)便出版了《蘇聯(lián)版畫(huà)集》。早在醞釀出版的時(shí)候,他曾答應(yīng)編輯該畫(huà)集的趙家璧協(xié)助選稿。四月七日,他如約到良友公司來(lái)。那時(shí)他的身體已不大好,走上我們?nèi)龢堑木庉嫴浚@然很吃力。他也不肯好好地休息,便忙著選畫(huà)。近三百?gòu)埖脑魉灰徽J(rèn)真看完,一面談他的意見(jiàn)。我們站在他的坐椅后面,隨著他翻動(dòng)的畫(huà)幅,聽(tīng)著他的評(píng)語(yǔ)。我算是學(xué)過(guò)美術(shù)的,可是有些作品只在聽(tīng)了他的分析才體會(huì)到它的獨(dú)到之處。
我們都知道,魯迅的身體本來(lái)就不好。經(jīng)常好了又犯病,犯了又好,卻萬(wàn)萬(wàn)沒(méi)有想到,這次他到良友來(lái),竟是最后的一次了。六個(gè)月后,他永別人間!消息傳來(lái),我們都感到非常震悼。原定當(dāng)月出版的《良友畫(huà)報(bào)》第一百二十一期,稿件早已編排好,部分已在印刷中。為了盡快表達(dá)我們的哀思,我們臨時(shí)抽掉其他四個(gè)滿版的稿件,代之以《一代文豪魯迅先生之喪》為題,全面報(bào)道了我們當(dāng)時(shí)所能搜集到的實(shí)況。那是魯迅四面受敵的時(shí)代,他的去世不僅使人們悲痛,也使人們聯(lián)想到他經(jīng)受到的圍剿而激起了義憤。人們給他一個(gè)英雄的葬禮,一個(gè)向敵人示威的葬禮。安葬前兩天,數(shù)以萬(wàn)計(jì)的男女老幼懷著沉痛的心情,到萬(wàn)國(guó)殯儀館瞻仰遺容。守靈的包括魯迅夫人許廣平和兒子海嬰。葬禮舉行時(shí)由章乃器代表各界人民致悼詞。當(dāng)時(shí)的葬地是萬(wàn)國(guó)公墓(一九五六年遷葬虹口公園)。葬禮隊(duì)伍聲勢(shì)浩大,莊嚴(yán)肅穆。自動(dòng)參加行列的達(dá)五千余人。巨幅的遺像和奏著哀樂(lè)的樂(lè)隊(duì)前導(dǎo),工人和學(xué)生組成的挽歌團(tuán),沿途唱著對(duì)這位偉大的導(dǎo)師致無(wú)限悼念的哀歌。挽聯(lián)如林,向這一代勇于向黑暗妖魔投槍的戰(zhàn)士,文學(xué)上的巨人表達(dá)無(wú)盡的眷念和敬仰。蔡元培、宋慶齡都參加了葬禮。宋慶齡獻(xiàn)贈(zèng)的楠木棺,由巴金等十二位作家扶樞走向公墓安葬……所有這些舉世矚目的情景,我們都把現(xiàn)場(chǎng)拍得的照片,連同魯迅當(dāng)年還不能公開(kāi)的寓所,他工作的寫(xiě)字桌、藏書(shū),和他去世前最后的一張照片:十月八日在上海八仙橋青年會(huì)全國(guó)木刻第二回流動(dòng)展覽會(huì)中與青年木刻家們座談時(shí)拍下來(lái)的照片,一并刊在當(dāng)月出版的畫(huà)報(bào)上,及早報(bào)道了這一事件。
三個(gè)月后,許廣平給我們送來(lái)了一份她寫(xiě)的征集魯迅先生書(shū)信的啟事,希望能登在《良友畫(huà)報(bào)》上,廣為傳播。我們把它刊在第一二五期內(nèi)。這個(gè)啟事,不僅是為了征集魯迅的遺書(shū),也概括了魯迅所寫(xiě)書(shū)信的重要意義。今天看來(lái),對(duì)我們閱讀魯迅的書(shū)信集,仍有很大的啟示。全文如下:
“敬啟者:魯迅先生給認(rèn)識(shí)和不認(rèn)識(shí)的各方面人士所寫(xiě)的回信,數(shù)量甚大,用去先生的一部分生命。其中或抒寫(xiě)心緒,或評(píng)論事象,或報(bào)告生活事故。不但熱忱不茍的精神和多方面的人事關(guān)系,將為制作先生傳記的必要材料,而且不囿于形式地,隨想隨寫(xiě)的思想討論和世態(tài)描畫(huà),亦將為一代思想文藝史底寶貴文獻(xiàn)。故廣平以為有整理成冊(cè),公于大眾的必要。現(xiàn)已開(kāi)始負(fù)責(zé)收集。凡保存有先生親筆書(shū)信者,望掛號(hào)寄下,由廣平依原信拍照后,負(fù)責(zé)寄還。如肯把原信和先生的遺稿遺物永存紀(jì)念,愿不收回,當(dāng)更為感謝。此為完成先生的文學(xué)遺產(chǎn)工作之一,受惠者不特一人,想是為諸位所熱心贊助。寄件祈交上海商務(wù)印書(shū)館編譯所周建人轉(zhuǎn)交為禱。
二十五年十二月
根據(jù)粗略的統(tǒng)計(jì),魯迅寫(xiě)出的書(shū)札不下三千多封。啟事登出后,當(dāng)時(shí)即陸續(xù)征集得八百多封。解放后經(jīng)各方面的努力搜求,現(xiàn)共得一千三百余封。并已搜集出版。
本文寫(xiě)到這里,原可結(jié)束。卻想起啟事中提到的“得為制作先生傳記的必要材料”一語(yǔ),頗有感慨。魯迅去世迄今已四十五年,不僅許廣平生前沒(méi)有看到傳記的完成,至今也仍然沒(méi)有一本有代表性的魯迅?jìng)鲉?wèn)世,不能不說(shuō)是憾事。可能有人想寫(xiě)而不敢動(dòng)筆。這種心情,原可理解。不過(guò)魯迅雖是個(gè)偉大的思想家、文學(xué)家,并不是神。寫(xiě)他的傳記不應(yīng)有什么框框。正如有人說(shuō),應(yīng)該可以有許多劇團(tuán)或電影廠,各自別出心裁演出或拍攝《阿Q正傳》、《祝福》,或是其他什么作品,魯迅的傳記也可以有許多人各自去寫(xiě)。和魯迅有過(guò)密切交往的人可以寫(xiě);和魯迅生不同時(shí)的青年作者,通過(guò)各種途徑搜集資料也可以寫(xiě)。傳記不僅記述一個(gè)人的生平,傳記本身也是文學(xué)。只有這么做去,便有百花爭(zhēng)艷、群芳競(jìng)秀的可能。有十種魯迅?jìng)饕膊凰愣唷R话倌旰笠策€應(yīng)有人繼續(xù)研究魯迅的生平,研究魯迅的作品,并繼續(xù)寫(xiě)新的魯迅?jìng)饔洝?/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