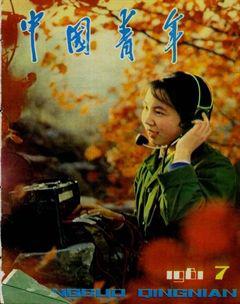“五四”青年及其革命精神
肖超然
五四青年節就要到來了。
六十二年前發生的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偉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主義運動。它作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就一定意義來說,也是一次青年運動。站在這個運動先頭的是幾十萬青年學生,而在運動中發揮了組織和領導作用的也多是當時先進的革命青年。
“五四”的膏年代表人物及其分化
五四時期,群眾愛國運動中的一些主要人物和活躍分子都很年輕。今舉其代表人物列表(見下頁)。
從下面這個很不完備的簡表中可以看出:
第一,表中所列人物都是青年。即便是李大釗、錢玄同、劉半農、胡適等人,當時已是北京大學的知名教授,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知名人物,年齡也不過三十左右。
第二,表中所列人物,在當時起的作用是不一樣的,后來所走的道路也不盡相同,但他們在五四運動中都或多或少起過積極作用。
第三,表中人物從李大釗到譚平山是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青年知識分子。他們是五四運動的中堅,是五四時期一代青年的卓越代表,在他們身上體現了“五四”青年的革命精神。
第四,表中從許德珩到匡互生是五四時期小資產階級的革命青年知識分子。他們都積極參加了五四運動,起過很大的作用。在這些人中,不少人一直堅持革命立場,不斷追求真理與進步。但也有人如張國燾,五四時期雖曾宣傳過馬列主義,并參加發起創建中國共產黨,當時也可說是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卻由于世界觀沒有得到根本改造,后來半路落荒,走入歧途,最后背叛了革命。
第五,表中從胡適到段錫朋是資產階級右翼的青年知識分子。他們參加了五四時期反對封建文化思想的斗爭。在運動的高潮中,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作過很激進的表演,如傅斯年是五四游行示威隊伍的臨時指揮,羅家侖曾代表示威群眾到東交民巷美國使館面交《說帖》等。但是,運動的高潮一過,他們很快就暴露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軟弱性和妥協性,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反對群眾革命運動,成為人民的敵人。
上述三部分青年的不同道路,是一面歷史的鏡子,它提供了值得我們今天認真總結和記取的重要歷史經驗。
“五四”青年革命精神的主要表現
以共產主義青年知識分子為代表的“五四”青年,都有解放思想、尋求真理、反對舊傳統舊教條的精神。他們當中以李大釗、毛澤東最為突出。李大釗在五四運動前夕寫的《晨鐘之使命》《青春》《今》等文,都是富有進取精神的戰斗篇章。他說:“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進于真理”。“茍其言之確合于真理,雖一時之社會不聽吾說,且至不容吾身,吾為愛真理之故,而不敢逡巡囁嚅以迎附此社會;茍其言之確背乎真理,雖一時之社會歡迎吾說,而并重視吾身,吾為愛真理之故,而不敢有所附和唯阿,以趨承此社會。”這是說的何等好呵!真正表現了他那江流不轉、屹然獨立的氣魄。
針對孔學舊教條束縛人們思想的危害,李大釗尖銳抨擊孔子是“數千年前之殘骸枯骨”,“歷代帝王專制之護符”。為了使人們從孔教的迷信束縛下解放出來,他表示“雖冒毀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
毛澤東同樣具有這種為救國救民立志尋求真理的精神。還在俄國十月革命前,他就曾表示決心說:“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無志,終身未得真理,即終身無志。”五四運動高潮中,他再次明確指出:“我們的見解,在學術方面,主張徹底研究,不受一切傳說和迷信的束縛,要尋著什么是真理。”正因為他解放思想,不為舊的教條和迷信所束縛,所以當中國的大多數人還沉睡于宗法封建思想之下,不少知識分子仍迷戀于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時候,他就提出了不僅東方的封建文化思想需要改造,就是“西方思想亦未必盡是,幾多之部分亦應與東方思想同時改造”這樣有真知灼┌──────┬───┬────────────┐│姓名│年齡│身份│├──────┼───┼────────────┤│李大創│30│北大教授│├──────┼───┼────────────┤│毛澤東│26│湖南新民學會負責人之—│├──────┼───┼────────────┤│周恩來│21│天津覺悟社負責人之—│├──────┼───┼────────────┤│鄧中夏│24│北大學生│├──────┼───┼────────────┤│高君宇│24│北大學生│├──────┼───┼────────────┤│黃日葵│22│北大學生│├──────┼───┼────────────┤│何孟雄│21│北大學生│├──────┼───┼────────────┤│繆伯英(女)│20│女師大學生│├──────┼───┼────────────┤│郭隆真(女)│25│天津覺悟社負責人之—│├──────┼───┼────────────┤│鄧穎超(女)│16│天津覺悟社負責人之—│├──────┼───┼────────────┤│陳望道│29│浙江第一師范教員│├──────┼───┼────────────┤│譚平山│33│北大學生│├──────┼───┼────────────┤│許德珩│26│北大學生│├──────┼───┼────────────┤│朱自清│23│北大學生│├──────┼───┼────────────┤│錢玄同│33│北大教授│├──────┼───┼────────────┤│劉半農│29│北大教授│├──────┼───┼────────────┤│張國燾│22│北大學生│├──────┼───┼────────────┤│劉仁靜│18│北大學生│├──────┼───┼────────────┤│羅章龍.│24│北大學生│├──────┼───┼────────────┤│匡互生│28│師大學生│├──────┼───┼────────────┤│胡適│29│北大教授│├──────┼───┼────────────┤│傅斯年│24│北大學生│├──────┼───┼────────────┤│羅家侖│23│北大學生│├──────┼───┼────────────┤│段錫朋│26│北大學生│└──────┴───┴────────────┘見的主張。有根據的懷疑是通向真理的階梯。毛澤東在俄國十月革命后,很快找到并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這個真理,決不是偶然的。
探索并非目的,破舊是為了立新。五四時期的先進青年們在批判舊傳統、舊教條的過程中,一般的都遇到了一個探索道路和尋求真理的問題。當時不少進步團體都發生了關于“主義”的論爭。而一旦這些先進青年認定了馬克思主義是救國救民的真理,社會主義是通向富強的道路時,他們就立即投入了傳播和實踐馬克思主義的戰斗。
由李大釗參與發起成立的少年中國學會,是五四時期影響最大的進步政治學術團體之一。它的許多成員如毛澤東、鄧中夏、黃日葵、高君宇、繆伯英、渾代英、張聞天、沈澤民、楊賢江、鄭伯奇、許德珩、楊鐘健、朱自清、劉仁靜、王光祈、曾琦、陳啟天、左舜生、李璜、余家菊等,當時都是青年。由于成份復雜,這個團體成立不久,就發生了“方向”問題,即所謂要不要“標明主義”。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要不要把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以李大釗、鄧中夏等為代表的共產主義知識青年,堅持真理,為信奉社會主義而積極斗爭。1920年8月19日,少年中國學會北京會員于中央公園(即今中山公園)來今雨軒開茶話會,討論了標明主義的問題。在1921年7月召開的少年中國學會南京大會上,鄧中夏、高君宇、黃日葵等采取一致的鮮明立場,多次發言,要學會改變原來空泛的宗旨,信仰社會主義。當左舜生、邰爽秋等人說什么“本無規定一種共同主義的必要”,并不無威嚇地說:“強定一種共同的主義,必致因大家意見不同引起分裂”時,鄧中夏當即針鋒相對地回答說:“至于規定主義,怕引起學生分裂,我想茍于創進少年中國有益,即破裂亦何妨!”這是何等的明快、果決!它充分顯示了五四時期先進青年為尋求、信仰社會主義真理而一往無前的精神。
第二,他們都有憂國憂民、救國救民、公而忘私的精神。五四時期的中國,正處在帝國主義列強的鐵蹄蹂躪之下,如毛澤東所說,“國家壞到了極處,人類苦到了極處,社會黑暗到了極處”。怎么辦?必須找到一條救國救民的道路。為此,他們都自覺地承擔了艱苦的磨練:或者象蔡和森、周恩來,遠涉重洋,尋求解放祖國的道路。前者一家四口(包括蔡和森年已54歲的母親葛繼豪老人,妹妹蔡暢同志和他的愛人向警予同志),于1919年11月去法國勤工儉學,研究和傳播馬克思主義;周恩來年僅19歲,抱著“蹈海”救國的決心和“破壁”、“濟世”的大志,東渡日本學習本領,臨別與友人約:“愿相會于中華騰飛世界時”。這是多么壯闊的胸懷!或者象毛澤東,留在國內,對“中國這個地盤”加以實地的調查和研究。總之,他們都胸懷天下,意境高遠,把救國救民視為一代青年應盡的責任。這種熱愛祖國、熱愛人民,公而忘私的精神,正是今天志在實現祖國四化的青年一代需要學習、繼承和發揚的。
第三,他們都有踏實勤謹、向工農學習、為人民服務的精神。五四運動以前,毛澤東多次深入農村、工廠,了解工農疾苦,向工農學習,這已是許多人都知道的了。在這里我想著重談談鄧中夏的事跡。五四時期,鄧中夏是北大中文系學生,后轉入哲學系學習,在北大前后六年。他勤奮學習,成績優秀。但他不是書呆子,而是在勤奮學習的同時,熱切關心國家命運,廣泛參加各種進步活動,并踏踏實實地為工人農民服務。那時他不僅是“北京大學馬克斯學說研究會”的發起人之一,也是“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的發起人之一。講演團在闡述它創立的宗旨時說:“平民教育,普及教育也,平等教育也。學校教育惟饒于資財者之子弟始得享受,而寒酸之子弟及迫于生計而中途失學者不與焉,未足語于平民教育。茍乏術以救之,則人民智識必大相懸殊,社會上不平之景象,必層見疊出,共和政體必根本動搖。補救之術維何?厥曰露天講演,刊布出版物,亦所以補助學校教育之所不及者也”,“我們天天鼓吹救國,可是實行下手的地方在哪里?救國的先決問題,是要不要民眾覺悟的努力。那么我們對于平民教育又安可不加以十分的注意。”在這里,講演團雖然還沒有完全跳出教育救國的框框(在舊中國這條道路是行不通的),平民教育的口號,也覺不夠鮮明,缺乏明確的內涵。但是,它著眼于廣大民眾,著眼于饒有資財者之外的廣大“寒酸子弟”和失學青年,著眼于要提高廣大民眾(包括工人農民在內)的覺悟,這無疑是可取的。
實際上,在五四時期,象鄧中夏、黃日葵、高君宇、何孟雄等先進青年,他們在講演團中的活動,主要是組織講演團團員,利用節日假期,到市內的許多鬧區向市民作講演;或到郊區的豐臺、長辛店、海淀等地,向當地的工人農民作講演。他們經常冒著嚴寒溽暑,徒步幾十里或上百里,向廣大工農作宣傳。1920年冬,他們在長辛店創辦勞動補習學校,擠出大學學習時間,到補習學校去為工人及其子弟上課。他們“向工友們講解革命大義,同時對工人生活非常關懷,事無巨細,有求必應,故工人稱學校為工友之家”。工人“不再把教員當成一般穿長褂兒的先生看待”。正是在向工農學習,為工農服務的過程中,“五四”青年中的先進分子日益認識到勞動者的偉大,對共產主義的信仰更趨堅定,成了工農的摯友和引路人。
五四時期先進青年的革命精神,是我國青年運動的光榮傳統。新時代的青年,一定要繼承這種光榮傳統,發揚這些革命精神,讓生命之火燃燒得更加熾烈絢爛,把偉大祖國建設得更加美麗富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