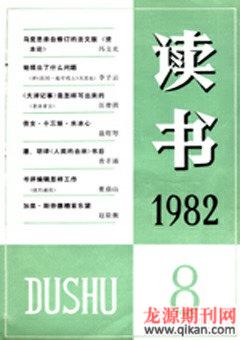民族大家庭的歷史
崔文印
白壽彝《中國通史綱要》的特色是:它力圖說明中國歷史是民族大家庭的歷史
早在三十年前,白壽彝針對舊通史存在的王朝史和大漢族主義傾向,就曾明確提出:中國通史要“以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土為范圍,由此上溯,研求自有歷史以來,在這土地上的先民活動。”他認為,這樣就“可能使本國史成為中華民族共同的歷史,可能使本國史告訴我們這個民族大家庭歷史的由來。”(《學步集》)現在出版的他所主編的《中國通史綱要》,就正是實踐上述見解的一部史著。
“以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土為范圍”來研究中國古代史,首先明確了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即凡今天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各民族,都是中國歷史的主人,都對祖國的開發作出過貢獻。不錯,我國是一個以漢族為主體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但漢族史或漢族王朝史不能等同于中國歷史,它只能是中國歷史的一個組成部分;不管這個組成部分多么重要,只有再加上另一個部分——各少數民族史才能構成一部完整的中國史。正是基于這一看法,所以《綱要》在講述歷代王朝興亡的同時,還十分注意這一時期的少數民族,特別是不在王朝統治范圍內的少數民族的發展情況。例如在《西漢的盛世》一節中,除談了匈奴以外,還提到了居住在今四川、云南、貴州等省的少數民族。在隋代,除談了契丹、室韋、
但是,《綱要》并不回避歷史上的國內民族矛盾。在處理這一問題上,白壽彝先生三十年前就曾提出兩點需要注意的地方:“第一,不要把漢族本身的利益作正義的唯一標準,也要把別的民族的利益算在里面。第二,要把民族斗爭的性質弄清楚。”(《學步集》)《綱要》就正是按著這些要求作的。例如,《綱要》充分肯定了女真首領阿骨打發動的抗遼斗爭的反壓迫性質。同時,,在宋金問題上,也明確指出,金兵最初南下攻宋,“主要目的在掠奪江南的財富和俘虜人口”。這就充分肯定了韓世忠、岳飛等抗金的正義性。《綱要》盛贊了努爾哈赤和皇太極的軍事才能和政治才能,稱他們為“杰出的軍事家”和“杰出的政治家”。對皇太極組織歸順的漢人進行生產,組織蒙漢壯丁為蒙古八旗和漢軍八旗,優禮明的降將等,都作了充分肯定。由于《綱要》明確指出,努爾哈赤建立的后金,“是在中國境內,明皇朝以外的一個獨立地方政權”,因此,書中對清兵入關并沒有異族“入侵”,甚至“亡國”的哀嘆;相反,明統治者的腐朽,和清創建者的朝氣蓬勃,倒使人感到了后者將要取代前者的歷史必然性。這些,都顯然擺脫了大漢族主義的民族偏見。必須指出,在中國古代史的研究中,怎樣處理歷史上的國土和民族關系問題,一直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我國著名史學家翦伯贊、吳晗等都對這個問題發表過很好的意見。可惜,這種帶有民族偏見的錯誤觀點在今天并沒有得到應有的清算,相反,“某些史學家和文藝作家把漢族以外的其他族對中原(中朝)進行武裝斗爭時,叫‘侵略”(李一氓《讀遼史·兼論<四郎探母>》),就是這種錯誤觀點的具體反映。
關于歷史分期,《綱要》認為商周是奴隸制時期,東周初年和春秋戰國是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時期,秦漢是封建社會成長時期,而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直到五代、宋元,則是封建社會發展和繼續發展時期,到了明清,封建社會便進入了衰老時期。這些結論勾勒了我國封建社會從成長到衰老的整個歷程。盡管對于我國歷史分期問題史學界尚有不同看法,但作為一種觀點,闡述的如此清楚則是難能可貴的。
最后,還要提及的是,《綱要》還體現了優良的學風。白壽彝先生在本書《題記》中特別指出:“范文瀾同志的《中國通史》和游國恩等同志主編的《中國文學史》給我們的教益較多。有時,我們作不出更合適的表述,還襲用了一些作品的成文。”這種不自矜、不掠美的老實人精神是多么可貴和值得提倡呵!
(《中國通史綱要》,白壽彝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十一月第一版,1.5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