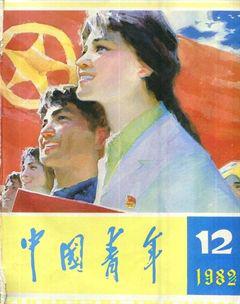兩個對立的藝術形象
高松年 周善賢
普羅斯佩·梅里美(1803—1870)是19世紀法國著名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中篇小說《嘉爾曼》(中譯也有作《卡門》)是梅里美一生創作的為數不多的中短篇小說中最燴灸人口的一部,也是世界著名的中篇小說之一。法國作曲家比才(1838—1875)曾把《嘉爾曼》改編成同名歌劇,以其優美的旋律、濃郁的西班牙色彩,更擴大了《嘉爾曼》的流傳。
《嘉爾曼》的情節,乍看似乎是一起情殺案,實際卻包含著較深刻的社會意義。小說發表于1845年,當時,拿破侖已囚死于圣海倫島,資產階級法律和秩序在法國漸趨鞏固,而曾在法國大革命中鼓舞過法國人民的“自由、平等、博愛”精神,早巳被資產階級拋棄殆盡。小說通過男女主人公的愛情悲劇,贊揚了嘉爾曼熱愛自由,做資產階級社會叛逆者的精神,從而對虛偽、自私的“文明社會”表露了否定和蔑視。
男主人公若瑟殺了人,當了走私犯、強盜,照他自己所說,完全是為了嘉爾曼。但,從他的生活理想、道德觀念和行動來看,卻是處處在維護資產階級社會的法律和秩序。他一時沖動放走了嘉爾曼,被關禁閉后又隨即后悔:后悔自己因為救了一個吉卜賽女人,從此失去了當軍官的前程。即使在身陷囹圄之中,他也仍然沒有放棄向上爬的欲望,不愿用嘉爾曼送來的銼刀越獄。他愛嘉爾曼,是要把嘉爾曼象商品一樣占為已有,他把嘉爾曼當情婦,卻不愿嘉爾曼有情夫。他的性格與心理,正是當時社會里資產階級心理的典型反映。
嘉爾曼跟若瑟截然不同。她是所謂的“化外之民”——帶著幾分野性的吉卜賽人。低下的社會地位使她敢于蔑視資產階級文明社會,珍視個性的自由,為了維護自身自由和信念,不惜以死相爭。在愛情上,她大膽、無私、潑辣、果敢。嘉爾曼對若瑟曾經有過真誠的愛。在若瑟殺死排長后,她緊跟若瑟、保護若瑟、悉心護理若瑟。她說:“你沒有看出我愛你嗎?我從來沒有向你要過錢。”但是,當她看透了若瑟的靈魂,就敢于宣布不愛若瑟。她用兩年的時間,苦心救援被關押的獨眼龍丈夫。當若瑟要殺死她時,她認為作為丈夫有權殺死自己的妻子。這一切,與當時社會里那種虛偽的、以男女互相欺騙為樂事的、純粹是“現金交易”的所謂“愛情”相比,確實有其閃光之處。
唯其如此,在小說中,嘉爾曼的直率、粗獷、放蕩不羈的個性和若瑟自私、虛偽、循規蹈矩的特點,形成了鮮明、強烈的對照。作家把這兩個形象放在一起,并將其置于一種復雜的愛情糾葛中,于是,在強烈的對比之下,小說所肯定與否定的思想蘊含也就顯露得十分明朗了。
當然,梅里美畢竟是一個資產階級作家,盡管他主觀上要把嘉爾曼塑造成一個“文明”的資產階級社會的叛逆者,從而揭露資本主義社會的虛偽和丑惡,但實際上,嘉爾曼身上所體現出來的個性自由,仍然屬于資產階級的思想范疇。作為資產階級作家的梅里美,沒有也不可能脫離資產階級思想的體系。嘉爾曼所追求的超脫于社會法律秩序之外的所謂“絕對自由”,實際上也是不存在的。到了無產階級革命蓬勃發展的時代,這種對“絕對自由”的追求,還具有一定的反動性。同時,十九世紀上半期,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矛盾已經暴露,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已經成為社會的主要矛盾,梅里美卻把自己的同情和理想寄托在一個流浪行騙、搶劫走私、迷信愚昧的人物身上,也表現了梅里美的資產階級世界觀的局限性。因而,嘉爾曼這一人物,既是梅里美對資產階級“文明”社會失望和不滿的產物,也是他自身的資產階級世界觀的一種必然表現。所以,今天讀這部小說,嘉爾曼這一人物形象,就只具有對資產階級社會的虛偽、自私、庸俗的認識意義,而絕沒有任何仿效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