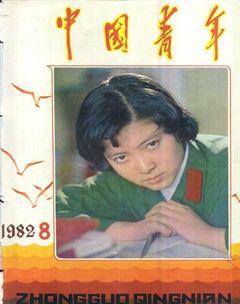“一枝紅杏出墻來”
文郁 華銘
江南四月,草長鶯飛,綠肥紅瘦。我們趁暇走訪了浙江省的一些公社,從一片生機蓬勃的農村春景中,為青年朋友采擷來一枝鮮花。這就是星羅棋布般興建起來的農村文化中心。有詩曾云:“滿園春色關不住,一枝紅杏出墻來。”透過這枝鮮花,人們看到了社會主義鄉村樂園的雛形。
現在,讓我們從一個普通的公社開始敘述吧……
“我們農民也要坐在戲院里看戲”
薄暮時分。炊煙從鱗次櫛比的木板房和爭相豎立的兩層磚瓦新樓間升起。社辦企業的機器聲依然在轟鳴。幾只木船從河上駛來,搖碎一路綠影,吱吱啞啞地鉆進了橋洞。
站在橋頭望去,湖泊象嵌鑲在田野里的鏡子。縱橫交錯的阡陌上,穿流不息的自行車駛向村頭的影劇院,坐在后座上的姑娘甩下一路笑聲……
這是奉化縣南浦公社文化中心一個平常但令人興奮的黃昏。高大的有著幾層大玻璃窗的影劇院前,小賣部卸下了門板,自行車越停越多,性急的小伙子和姑娘們在售票口排起了長隊。文化中心興建以來的每一個夜晚,都是以這種喧騰熱鬧的氣氛,迎接著來自周圍23個大隊的社員群眾。
南浦公社離奉化縣城20多里地。多年以來,全公社只有一臺16毫米的電影放映機,每個大隊平均兩個月才攤上一場電影。要是上城呢?農民群眾說:“上城看場戲,吃看三元幾,誤了生產化了錢,買不到票子還要生氣。”農村青年和社員群眾多次呼吁:“阿拉農民也要坐在屋里看戲!”公社興建文化中心,建蓋了這座擁有1172個座位的影劇院,平均每月放映電影24場,接待各種劇團演出6場。我們在影劇院門口攔住幾個小伙子,問他們建立文化中心后有什么感想?其中一個眼珠一轉,應聲答道:“阿拉南浦從前是窮鄉僻壤,如今好比小縣城啦!”
當我們越過綠色的田野,驅車來到鄞縣邱隘鎮時,首先映入眼簾的,是燈光通明的文化中心樓。樓前運動場上,激烈的球賽已接近尾聲。影劇院前,熙熙攘攘的人群等著電影開場。自行車密密麻麻,從這頭排到那頭。賣各種小吃、零食、水果的小攤生意興隆。我們走進文化中心樓,一樓左首是圖書報刊閱覽室,藏書一千余冊,訂報紙19種,期刊108種,此刻已經坐滿了青年;右首,是兒童游藝室,因為不是節假日,現在在舉辦蛇展;我們沿樓梯拾級而上,二樓的康樂球室和棋室里,觀戰者淹沒了交戰雙方;乒乓球室里,公社繡品廠的年輕人的乒乓球比賽已進入最后一輪。忽地,三樓飄來一陣絲竹聲,原來是公社文宣隊在可容三百人的說書場內排練新節目;而在肅靜的四樓的幾間大教室里,文化中心主辦的業余文化補習班正在考試……
這座實用面積近一千平方米的文化中心樓,和由公社會堂改建的影劇院,被廣大農村青年自豪地稱作“邱隘大世界”。在這個總人口為二萬三千余人的公社,每天來參加活動的達二千人。我們的腦中曾跳出“來者云集”四個字,似乎仍然概括不了“邱隘大世界”的盛況。
依靠集體經濟的力量,在公社所在地,興建一批文化設施,逐步形成以集鎮為中心的農村文化網——這就是農村文化中心的基本涵義。在古老的中國農村,是什么,使這枝鮮花萌生、滋長并綽約多姿地開放呢?
在邱隘文化中心的辦公室里,鎮分管文化的負責同志王秀珠,毫不遲疑地回答我們:“農村富了!農民有錢了!搞責任制以來,今年和1976年比,我們的糧食畝產增加150斤,人均收入增加100元,社辦企業利潤增加128萬元!社員們說,邱隘現在吃穿不比城里差,就是文化生活比城市差得遠。阿拉農民也要坐在戲院里看戲!鎮黨委幾次開會研究,大家說,如今群眾有要求,集體經濟又有錢,干!一拍板就干起來了。”她笑了笑,接著說:“現在看,每天來人交關多,交關擠,農民文化樓實在是蓋小了!”
“阿拉農民也要坐在戲院里看戲”,普普通通一句話,反映了富裕了的農民對文化生活的迫切需求,也道出了文化中心得以興建的基本原因。從省到地區又到縣,一路上,許多黨委和文化部門的領導同志告訴我們:“過去經濟條件不具備,我們要辦這辦那,就會脫離群眾;現在有條件了,我們不辦,不去努力滿足農民群眾的文化要求,也要脫離群眾。”他們認為,這里似乎可以概括黨在農村開展文化工作的主要經驗教訓。而廣大農村青年和社員群眾則說:“農村文化中心是應運而生的,上合國情,下順民心。”所謂國情,就是三中全會以來農村的大好形勢,所謂民心,就是廣大社員和農村青年對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和向往。有了這兩條,農村文化中心才會有如此盛況!
據說,神奇的馬蘭花,能化作上山的梯,過河的橋。那么,萌生于我國當代農村豐厚土壤上的農村文化中心這枝鮮花,是否將成為橫跨在城鄉之間的橋梁?我們真想從心底里歡呼:應運而生的文化中心大有可為,前景燦爛!
“現在,才象社會主義農村的樣子”
臨離開北京前,我們看了電影《被愛情遺忘的角落》。我們掉下了熱淚,卻沒有想去擦一擦。在這個角落上發生的悲劇,除了可以歸結為貧窮與愛情領域里的封建意識外,也是與鄉村的閉塞、愚昧、缺乏精神文明分不開的呵!
這樣的角落,今天農村還有。奉化縣南浦公社下街大隊有四十幾個青年,一到夜間,無所事事。他們便把充沛的精力,寄托到54張撲克牌上。玩撲克,在浙江稱作“柯沙蟹”。“柯”了一陣,仍然不滿足,于是就想出種種刺激辦法,從丟幾支煙、幾顆糖,發展到放上一把把票子,“聚眾賭博”的犯罪道路就這樣暢開了。在肖山縣浦沿公社浦聯大隊,有個聰明、好動的青年,叫虞興堂。他年紀不大,外號卻有兩個:“無窩鳥”比喻他終日不著家,“三角石頭”指的是沒有人能管住他,成天東游西蕩。
這是隨手拈來的例子。對今天的農村青年來說,豐衣足食已不再是唯一的愿望,老一輩農民的那種看著滿囤的糧食,晚上喝點酒,然后心滿意足地上床睡覺的生活,也不再是他們憧憬的藍圖。“白天捏鋤頭,晚上抱枕頭”,這種單調的生活,會在他們心里引起怎樣酸苦的反應,導致怎樣的后果,值得人們加以注意和重視。
當我們來到南浦公社和浦沿公社時,前面提到的這些農村青年,都已成了公社文化中心的常客。南浦公社文化中心上映一場盼望已久的好電影,或是舉辦一次大的活動,那幾十個小伙子總不請自來,主動幫助維持秩序;虞興堂今天成了文化中心的“窩里鳥”,他在圖書室里讀書有味,看戲看電影入迷,打康樂球、下棋更是不忍釋手。不久前,他“照著葫蘆畫個瓢”,按公社文化中心的樣子,幫助大隊修起了籃球場,給俱樂部制作了一副康樂球。我們見到他時,他的胸前別著晶亮的團徽,已被大家推選為生產隊的隊委。
由參加和熱愛健康的文化活動,從中受到陶冶,到逐步形成比較優美、高尚的道德情操,是這些農村青年思想變化的一條重要途徑。不少社、隊團委的同志告訴我們,農村青年是有多種層次的,促進他們的思想成長,需要多種多樣的渠道。興辦農村文化中心,就是從農村青年的現狀和迫切要求入手,為他們提供帶來各種新鮮訊息的渠道,使他們開闊眼界,增長知識,陶冶性情,潛移默化地提高精神境界。浦沿公社、南浦公社、邱隘鎮等文化中心,除了在節假日集中舉辦適合農村青年口味的各種形式的文體活動,如籃球、羽毛球、象棋、乒乓球等體育比賽,書法、攝影、美術、宣傳畫、黑板報等展覽,燈謎、康樂球等各種游藝活動外,還根據農村青年的要求,建立了故事組、教歌組、創作組、報道組、美術組、舞蹈組等青年業余文化組織,建組時舉辦幾天學習班,以后定期集中活動。邱隘鎮文化中心在相繼開辦12個活動項目的同時,還舉辦了包括文化、生產技術在內的多種講座,和農業技術、職工技術、文化初班、高班四個補習進修班。南浦公社文化中心編輯出版了《南浦電影》《南浦文藝》等刊物。這樣,在許多公社,文化中心不僅滿足了農村青年和群眾對文化生活的需求,而且在實際上作為新聞報道中心、文化活動中心、體育活動中心、業余教育中心和科技普及中心,把農村中除正規學校和醫療衛生以外的所有文化工作統轄起來,從而成為在農村建設現代化文化、教育、科學事業的重要陣地。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社會主義的新型的小集鎮雛形,開始在農村大地上逐漸形成,它很可能成為縮小和最終消滅城鄉差別的不可缺少的中心環節。
令人欣喜的是,這些地方的縣和公社團委,敏銳地有遠見地意識到共青團的職責,在農村文化中心找到了共青團的位置,把帶領青年積極參加建設農村文化中心,與團的工作緊緊結合在一起,與抓農村青年精神文明建設巧妙地結合在一起。這樣,一方面,新形勢下的共青團工作出現了新的局面,另一方面,改變社會風氣也尋找到了新的通道。我們所到的公社文化中心,管理委員會主任一般由公社黨委書記兼任,副主任則由團委書記和文化中心站的站長擔任。至于文化中心下面的文化網——各大隊的“青年之家”或“俱樂部”,這些組織的建立和活動的開展,幾乎全由大隊團支部和團員、青年積極分子承擔。共青團和文化中心協同作戰,把絕大多數青年吸引和團結在周圍。廣大青年望著建立文化中心后日漸繁榮熱鬧的公社駐地,情不自禁地對我們說:“這樣建設農村的城鎮,才象個社會主義農村的樣子,我們才看到了希望。”
“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文化中心這枝鮮花越開越爛漫,一個重要原因,是在它確確實實為農村裝點春色,送來春的怡人氣息。
“‘雞娘領著,‘小雞才活絡”
許多事實告訴我們,青年是建設農村文化中心最熱烈的擁護者和最積極的力量,也是從農村文化中心汲取營養,得到歡樂的最大受益者。
一個雨后的黃昏,我們騎自行車,隨浦沿公社文化中心站的小許同志,來到山二大隊,參加音樂欣賞會。
大隊學校的教室里坐滿了年輕人。團支部書記、一個二十歲上下的小伙子,先領著大家唱了幾首新學的歌曲。“相逢開口笑,啊,握手問個好……”“云霧滿山飄,海水繞海礁……”富有朝氣的歌聲,飄蕩在寧靜的村莊上空。歌聲剛止,小許即刻評論起來,指出有哪幾個音符唱得不夠準確,哪幾處節奏不夠妥切。講完后,他笑嘻嘻地對大家說:“這次,我帶了幾首大家喜歡的歌子。”在隨即引起的一陣“嗡嗡”的議論聲中,幾個激動的青年鼓起了掌。小許按下了錄音機的按鍵,頓時,全場靜下來了。錄音機里傳出了蔣大為演唱的《駿馬奔馳在遼闊的草原》,接著,是李谷一為電影《知音》配唱的主題歌。在大家凝神欣賞的時候,小許輕輕告訴我們,這類文化活動,文化中心每月要搞好幾回。在浦沿公社的青少年中,具有小學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71%,農村文化程度的提高,使農村青年的文化素養、對文藝的愛好和需求,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中國農村傳統的文化活動,已遠遠滿足不了他們。浦沿公社的青年,對越劇(浙江素稱“越劇之鄉”)有興趣的不到20%,愛好音樂、美術、攝影等的青年則達到80%,蔣大為、李谷一、蘇小明等,都是他們最歡迎的歌唱家。
確實,從我們此行接觸到的農村青年看,興趣之廣泛,愛好之新穎,實在叫人驚奇。從文學創作、新聞、音樂、美術到攝影、書法、篆刻甚至考古,幾乎囊括了文學藝術的所有種類。不少青年同時涉獵好幾個方面。我們在浦沿公社浦聯大隊結識了故事員湯妙仙,他同時參加創作組。為了講出新故事,他利用工余時間,走訪當地的老農民,創作整理了一些民間故事。和湯妙仙一起同我們交談的,還有虞德喬和虞海燦。德喬愛寫美術字,大隊黑板報的劃版、設計、插圖,全由他一人包了下來。海燦酷愛書法篆刻,現在每天一邊臨顏正卿的大小楷,一邊往返四五十里地,騎車去杭州市一所夜校上書法篆刻課。他倆講話時還帶著少年人的羞怯,但一提到美術和書法,頓時神采飛揚,真叫我們怦然心動。
這情形,已經不僅僅是一般的興趣了。在浦聯大隊俱樂部,張貼著一些名人名言,其中,歌德的“外貌美只能取悅一時,內心美方能經久不衰”和富蘭克林的“懶惰,象生銹一樣,比操勞更能消耗身體,經常用的鑰匙總是亮閃閃的。”這兩段話分外醒目。歌德和富蘭克林走上中國農村的墻頭,這是耐人尋味的,所反映的,正是當代農村青年對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
我們在奉化縣南浦公社看了文宣隊排練越劇《珍珠衫》。飾小生的姑娘,唱腔圓潤,招式瀟灑。她叫張美麗,今年才20歲,從小酷愛戲曲。17歲起在民間劇團唱“路頭戲,不事訓練,沒有定型本子,真可謂“為唱戲而唱戲”。小張一時比較徬徨。公社文化中心成立文藝宣傳隊,她考了進來,幾年來長進很快,初步掌握了越劇尹派小生的風格。據說,幾個民間劇團以一天五元以上的薪金,拉她去演“路頭戲”,她力辭不去。
我們問她是否有這回事?她漲紅著臉,點了點頭。我們又問道:“為什么不去?”她只說了一句:“在這里,藝術上有學頭,有提高。”
在農村青年中蘊藏著一大批各種各樣的人材,他們就象寶石,需要人們去發掘、去琢磨、去培養。許多青年文化骨干說:“我們好比小雞,文化中心好比雞娘,雞娘領著,小雞才‘活絡(有生命力)。”
浦沿公社浦聯大隊23歲的報道員孔松林,就是這樣一只由“雞娘”帶大,現在羽翼豐滿、獨立奔跑的“小雞”。他1978年高中畢業后,總是為學到的東西沒處發揮而悶悶不樂。文化中心建立了報道組,他第一批就報名參加了,在文化中心的培訓輔導下,現在基本掌握了主要的新聞體裁。1980年,他向公社發稿50多篇,被省市報刊采用2篇;去年,他寫了100多篇稿,其中被省市報刊電臺采用7篇,年終時被評為縣優秀通訊員。今年,他的稿件上了《光明日報》的版面。
在南浦公社,文化中心的同志向我們介紹了業余考古通訊員張本富。考古,在農村真難以想象!可眼前的這個高小畢業、中等個頭的青年人,好幾年前就大致上考證了公社所在地的歷史淵源,而最近,又通過考證,發現和保護了一座宋代木橋。我們一起來到木橋邊,橋墩由五塊大青石板豎成,一艘機動船正在橋下通過。橋身為木結構,有頂復瓦,兩邊可開店鋪,橋中寬可通拖拉機。在宋代,該算是相當氣派的吧!由于長年失修,頹敗不堪,縣交通部門打算拆掉,建一座水泥橋。張本富聞訊后,在文化中心幫助下,四處奔走尋覓,終于在一間堆滿稻草的小屋里,發現了幾塊字跡模糊的石碑,經過好幾天的研究考證,才發現這就是橋碑,從而搞清了橋的來龍去脈。小張把考證結果寫成報告,通過文化中心,送到縣里,呼吁不能拆橋,而應維修保護。我們去看木橋的時候,縣、公社、大隊三級已分別籌款,橋正在修繕之中。縣已確定為縣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并向省推薦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馬克思很早就曾預言,在一個健全完美的社會里,“需要一種全新的人,并將創造出這種新人來”,這樣的新人,“能夠全面地發揮他們各方面的才能,而同時各個不同的階級也就必然消失。”這種新人,同樣也應該產生于農村。農村文化中心為發掘、培養和造就農村青年成為全面發展的新型人材,提供了具體可見的前景,這,也許是它具有生命力的又一個重要原因吧!
有預見,才叫領導
在我們踏上歸途的時候,那些生氣勃勃的農村文化中心,象一幅幅圖畫總在腦際縈繞,我們一路上結識的各級黨委和各級文化部門的同志,那些積極參加文化中心建設的共青團干部,那些活躍在文化中心的可愛的農村青年,就更使人難以忘懷。他們,正是他們,開拓著和建設著偉大的農村文化事業,為社會主義現代化農村描繪著斑斕的色彩。
早在1979年6月,胡耀邦同志就在北京召開座談會,主持制定了活躍農村文化生活的文件。同年11月26日,耀邦同志在《上海市金山縣茶館情況的調查》上批示:“隨著農業和農村形勢的不斷好轉,我們需要把全國的小城鎮建設成為政治、經濟、文化的基層中心。建設這種基層中心,不是靠國家投資,而是引導各方面采取集體所有制形式予以解決。但這要有計劃有領導。這件事,許多同志還沒有意識到,我們中央有關部門同志都要有預見。有預見才叫領導。”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耀邦同志對此連續作了六次談話和批示。
浙江省的這些地、縣黨委和文化部門,正是有預見、有卓識,才有邱隘、浦沿、南浦等一批公社文化中心建設的實踐。而這實踐表明:建設農村文化中心不僅能辦到,而且大有可為,其意義也日漸一日地顯現出來。肖山縣委規劃,在目前已建成六分之一公社文化中心的基礎上,三至五年內,把全縣每個公社都建成農村文化中心。那時,肖山是杭州的衛星城,而一個個既是經濟、政治中心又是文化中心的小鎮,猶如肖山的衛星城鎮,星羅棋布地撒在肖山全縣的廣闊土地上……
這是一幅多么誘人的圖畫。可以預期,隨著農村形勢的進一步發展,農村文化中心這枝鮮花,將更加絢麗地開放在祖國廣袤的農村大地。而廣大農村青年,在文化中心的培養陶冶下,將成為我國農村的嶄新一代。那時,曙光召喚而來的,是社會主義現代化農村充滿生氣和活力的早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