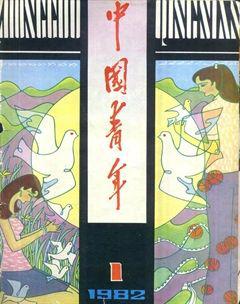有感于當前大學生的讀書愛好
陳保平
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書林》編輯部作了一次讀書調查。翻閱著大學生的讀書調查表,不知為什么,心里頗有點激動。說不清是驚奇,還是感慨,還是興奮;總覺得這些大學生已不是一般地在讀書,求知,完成學業,他們好象總是在思考著什么、尋求著什么。這些大學生讀書之多、之廣、之深,不僅與社會其他成員有所不同,與文化大革命前的大學生也有很大差別。從哲學、經濟學、社會學、美學、心理學一直到宗教、人才學,他們探索的目光幾乎涉及人類知識的各個領域,甚至連那些被恩格斯稱作要象“骨頭”一樣去“啃”的艱深的理論,如馬克思的《資本論》、黑格爾的《小邏輯》、愛因斯坦文選等,也成了他們案頭、床邊的必備書。
在調查表的“您最喜歡的哲學、社會科學書”一欄中,我們看到,填得最多的是西方近代哲學方面的書和馬克思主義的一些經典著作,如羅素的《西方哲學史》、斯賓諾莎的《倫理學》、詹姆斯的《實用主義》、盧梭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薩特的《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等。其中,最近再版的馬克思早期著作《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占了不小的位置。
也許是因為多年來的閉關自守,所以一旦打開窗子,便感到空氣格外新鮮;也許是出于對封建傳統束縛的深惡痛絕,于是對這樣一些具有反封建傾向的西方學說便一見傾心;但我覺得,這里更多的人是因為有過失落,所以才去苦苦地尋求,就象魯迅當年失落了“進化論”一樣。他們想尋求到一種能真正解釋世界、改造世界的新的理論武器。然而,在這過程中每個人看到的、尋求的也并不完全一樣,有人看到了金字塔的悠久、尼羅河的富饒,相信萬里長城和黃河與它們一樣,都是人類文明的組成部分。有人則被盧浮宮的豪華、自由神的耀眼迷惑住了,于是對自己腳下的土地不屑一顧。有人本來就沒有認真地讀過一兩本馬列的書,對馬克思主義的來源、發生發展過程以及它的基本原理也不甚了解。他們接受的馬克思主義無非是“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也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革命搞好了,生產自然而然就上去了”之類的東西,要不就是讓人奉為“啟示錄”一般的神學或者是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的魔術。因此當這一切垮臺后,他們就對馬克思主義產生了一種本能的反感,以為馬克思主義過時了,只有到西方自由主義者的理論中尋找救國藥方。有人則走了一個“之”字形,由開始對馬克思主義的懷疑,動搖,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重又回到了馬克思主義。也有不少大學生一開始就是本著尋求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而去博覽群書的,這從他們的讀書調查表中可以看出,他們既仔細閱讀馬列原著,又不排斥對西方資產階級學者的理論的研究,通過比較、鑒別,進一步認識到只有馬克思主義才是最先進、最科學的學說。正如一位對馬克思主義作了一番深入研究的大學生所說,過去我們在理論上之所以屢屢失誤,并不是馬克思主義不靈了,恰恰是我們對馬克思主義沒有采取科學的研究態度,沒有從事實出發,而是采取了主觀主義的態度,把馬克思主義當作框框去衡量事實是否對號,這本身就是違背了馬克思主義。還有的青年在信中談到,我們一些長輩長年累月,含辛茹苦,用切得細細的,加了各種作料,烹調得好好的馬克思主義把青年喂大,可在不少青年看來,這些“食物”是在保姆的連哄帶嚇下吃進去的。他們沒有經過自己的選擇,并不真正了解它的價值。一個人怎么可能真正堅持那不是由他選擇的信仰呢?這話說得不無道理。事實上,一個真正樹立起信仰的人,都有一番痛苦的選擇過程。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選擇了馬列之前,不也曾選擇過孔孟、老莊、尼采、康德嗎?從某種意義上說,在每個人的思想發展中,選擇的過程是必不可缺的。
如果說大學生對哲學、社會科學書籍的愛好是為了尋求理論武器,那么,從他們對文藝作品的愛好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們是在尋求關于“人”的知識,尋求“人的價值”。在“您最喜歡的文學書”一欄中,《紅樓夢》《簡·愛》《安娜·卡列尼娜》《約翰·克利斯朵夫》《紅與黑》等書占的票數最多,而其中《約翰·克利斯朵夫》與《簡·愛》又如出一手地名列前茅。為什么這兩部在世界文學名著中并不算第一流的作品,能這樣得寵于大學生們呢?顯然,這與作品的強烈傾向性有關。這兩部書的一個共同主題,就是在于指出生命的意義即是為爭取自己做人的權利而戰斗,而真理也是通過這樣的戰斗而取得的。這對在“四人幫”封建法西斯專政統治下,個性曾受到長期壓抑、人的價值完全喪失的大學生無疑是有進步意義的。他們經歷了難以忍受的精神苦悶后,一旦發現了失落的“自我”,意識到人的價值時,就象發現了新大陸一樣激情難抑。從這兩本書中,大學生們不僅認識到,人類對自己所特有的這種強烈的人的意識,是人的全部價值和尊嚴的基礎;同時也進一步認識到,人的價值的充分實現,走約翰·克利斯朵夫和簡·愛的“個人奮斗”的道路還是行不通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奮斗了幾十年畢竟還是失敗了,他臨死時曾痛苦地說:“我戰斗了,苦惱了,流浪了,創造了,什么時候又要為戰斗而復活罷!”
克利斯朵夫苦惱的問題,《牛虻》中的亞瑟、《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的保爾答復了:只有摧毀個人主義,投身到集體主義的戰斗中去,才能復活。脫離群眾,個人是無力的;沒有行動,真理是虛偽的。亞瑟拋棄了他的神父后是這樣行動的,保爾從牢房出來后也是這樣去實踐的。今天,經過苦難的歷程的中國大學生,也正在走這條獲得新生的必由之路。我想,這也許就是在“其中對您的思想有重大影響的書”一欄中,大多數大學生至今仍象五六十年代一樣,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牛虻》奉為自己的生活教科書的原因吧。如果說,克利斯朵夫的“個性解放”曾經給予一代大學生沖破封建傳統勢力的力量,那么,保爾表現出來的思想和對事業的忘我的犧牲精神則更為重要。因為個性的解放首先得取決于整個人類的解放,只有象保爾那樣為個性的全面發展創造條件,為解放全人類去奮斗,個人的價值才能得到充分實現。停留在約翰·克利斯朵夫的思想階段而不前進,或是在個人主義的死巷中作無謂的探索而自以為找到了唯一正確的道路,那既不可能對“人的價值”獲得較為完整的理解,也不可能真正尋求到幸福與光明的道路。
當然,作為青年學習的榜樣,保爾和亞瑟在這兩本書中并沒有被神化。他們有著普通人的歡樂、惆悵;有生的熱情,愛的高潮;他們也失過戀,犯過難以饒恕的錯誤,甚至有過自殺的念頭。他們首先是人,然后才是英雄。正因為他們是在社會斗爭的實踐中逐步克服了個人的弱點,他們才算得上是強者,才為無數普通的青年所愛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