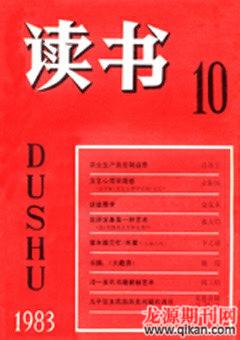文藝心理學隨想
袁振國
金開誠《文藝心理學論稿》讀后
金開誠同志在北大舉辦的“文藝心理學”講座早已喧騰人口,因此我一直翹首期待著他的講稿的出版。讀了《文藝心理學論稿》以后,確實使人得到很大滿足。誠如有的同志所說,它“打破了長期以來籠罩在文藝心理學上的神秘感。”這里,試將我讀此書的一些斷想略述如下,以求正于作者和讀書界。
文藝心理學研究方興未艾
美國《二十世紀文學百科全書》(一九七四年版)提到當今的文學批評有三大世界性流派:馬克思主義學派,結構主義學派和心理分析學派。盡管這種提法我們不一定接受,但從中卻可以使我們獲得一個重要信息:運用心理學于文學的研究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它已經成為世界范圍一種很有聲勢的潮流。加強文藝的心理學研究,早在尼達姆(H.A.Needham)《論十九世紀法國和英國社會美學的進展》一書中就有這樣的呼聲了。他認為,美學應包括三個截然不同、卻又互相補充的部分:第一,抽象的或形而上學的部分,致力于給美下定義;第二,心理學的部分,致力于描述美對于人類心靈的影響;第三,社會學的部分,目的在于確定美在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我國美學家李澤厚充分發揮了這一思想,系統提出了美的哲學、美的心理學和美的社會學的觀點。他認為,美的哲學只是美的引導和基礎,美的心理學則是美的中心和主體,美的心理學的研究是促使美學走向成熟的途徑,是了解美的本質到美的現象的中介。文學的創作和欣賞就是一個立美和審美的過程,因此美的心理學和文藝心理學的關系是顯而易見的。
文學的創作與欣賞,是極其復雜的心理活動,僅僅停留在外部規律的分析上總不免給人不足之感,如果深入到心理活動的內部,則能洞悉幽隱,給人以新的啟示。遠的不說,就說大家熟知的弗洛伊德,這是一位標新立異有余,自圓其說不足甚至毫不顧及理論嚴密性的心理學家,常常把具有一定合理因素的理論夸大到近乎絕對的地步。他的文藝心理觀亦不例外。在他的眼里,作家的創作活動、讀者的欣賞共鳴全然是受到壓抑的潛在的性本能得以“升華”的需要。這種理論自然很難令人首肯。但他開辟的道路卻給后人以啟迪。他的學生榮格師承了他的理論而又有所棄取和發展,延伸了文學心理分析的道路。榮格認為文學創作有兩種類型,一類是“心理型”,它取材于人的意識范圍,可以從生動的生活外表擷取題材;一類是“幻覺型”,這類作品的素材來自人類心靈深處的某種陌生的東西,是人類不能理解的神秘世界的原始經驗,這種經驗世代積累下來,“沉淀”在每一個人無意識深處,是歷史在“種族記憶”中的投影,他稱之為“集體無意識”。他說,每個民族處于混亂危厄的時候,潛藏蟄伏在人的無意識中的原始救世主形象就會復蘇過來,呼喚作家根據古老的神話,創造這樣的形象,引起全民族的共鳴。他有一句名言:“不是歌德創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創造了歌德。”如果我們對榮格這套理論的神秘成分加以揚棄,就可以得到一個重要的啟發:“史詩”式的作品產生于動亂時代之后,要創作出“史詩”般的作品,作家就必須諳熟該民族的穩固心理特征,準確地把握并描繪他們的情緒、意愿和向往。
弗氏師徒開辟的文藝心理分析方法在今天的美國又有了新的發展、并呈現出方興未艾之勢。近來,美國流行著一種被稱為Reader-based的文藝批評方法,就是站在讀者的角度,以讀者的眼光分析作品,這種方法注重研究作者與讀者的雙向心理活動,促進兩者的心理交流。與此相呼應,我國的文藝界、美學界也加緊了文藝心理學的研究。前一段時期關于形象思維的大討論,比起六十年代來有了明顯的深入,一個顯著的標志就是在心理學上的進展。近來運用心理學于文藝分析的譯述文章也逐漸增多,形成雨后春筍之勢。而《論稿》則是一部一馬當先并產生了較大影響的著作。
打破了沉寂的局面
說到文藝心理,人們自然會立即想到朱光潛老先生三十年代著的《文藝心理學》。從時間上說這當然是國內有關文藝心理的最早著作,在當時的文壇上也確實吹進了一股新風,影響很大。但它畢竟是一部兼收并蓄的國外審美心理理論的介紹著作,由于時代的局限,也缺少恰當的述評。此后,文藝心理的研究沉寂了近半個世紀。《論稿》的問世,打破了這一局面。
《論稿》的作者明確認識到,所謂文藝心理學,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和普通心理學原理在創作和欣賞中的運用。在這一認識的基礎上,作者進行了可貴的具體探索。
《論稿》指出,大腦是一個整體,其兩半球的活動彼此制約調節,文藝創作只能在反映客觀世界的基礎上,實現形象、理性、情感三者的統一,而不能把其中任何一個因素絕對化。《論稿》對于心理活動的整體性的強調,為文藝心理研究的健康發展奠定了基礎。現代腦生理學研究證明,人的思維、情感、意志在大腦是分別有控制中樞的,大腦左右兩半球也確實具有側重語言概念和形象活動的不同特點,但它們并非“老死不相往來”,兩半球之間有海馬回、胼胝體把它們聯系起來。其中胼胝體就含有兩億條神經纖維,每條纖維平均沖動20赫,信息總量可達4×10
總之,在某種意義上說,《論稿》不失為我國一部有意識地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進行文藝心理研究的開先聲之作。它對文藝心理學的發展會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但高興、贊美之余,對于《論稿》本身也有幾點想法和疑問。
文藝創作心理活動的本質是什么?
研究一事物的本質,總是要從研究該事物與相對事物的不同之點,即它的特殊性入手。那么以創造典型形象為目的的文藝創造活動的特殊性是什么呢?金開誠同志提出自覺的表象運動是文藝創作的根本特性,所謂形象思維“就是在抽象思維和內部語言的指導和配合下,能動地反映客觀世界的自覺表象運動。”我們感到,這種提法一般地籠統地說,也是可以成立的,但從心理學角度分析起來,就不夠貼切有力了。這里的關鍵是“表象運動”能否反映文藝創作心理活動的本質。所謂表象,就是保持在記憶中的某一事物的形象,它是訴諸于某一種感覺器官的,如視覺表象(色彩、形狀)、聽覺表象(聲音)、嗅覺表象(氣味)等。但活躍在藝術家頭腦中的絕不是某一單一表象,而是在生活中多次接觸、多次感受、多次為之激動的既豐富多彩又高度凝縮了的形象。我稱之為“具象”。它是馬克思講的從具體到抽象再回到具體的第二個具體。這個“具象”不僅僅是感知、記憶的結果,而且打上了作家、藝術家的情感烙印,滲透進了他們的觀察、思考因素。它是生活中無數單一表象綜合以后,經過抉擇、取舍保留下來的,作家、藝術家的創作過程,從心理學上說就是具象的運動過程。具象的運動過程,主要是激發并強化作家、藝術家的情感,與情感相互作用的過程。一旦進入具象運動階段,創造者往往是情不自禁的,甚至是如癡如狂的,帶有很大的不自覺性,很少有抽象思維的參預。具象不是抽象思維的起點,而是抽象思維作用下選取、綜合表象的結果。它和一個人的情感表現一樣,絕不是無緣無故的,就和鹽溶于水一樣,溶進了創作者的認識。但它一旦運動起來,又是很少受理智支配的。從發生學上說,表象、記憶能力是人的低級心理水平,動物也有表象、記憶能力。但動物沒有根據自己的需要、態度、體驗和思想、觀念來綜合、取舍表象形成具象的能力。我們感到這樣分析更符合藝術創作的心理本質,也為批判形象思維是“表象——概念——表象”的錯誤觀點提供了心理學依據。
怎樣建立文藝心理學的體系?
這是個大問題。它涉及到文藝心理學的研究范圍、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要解決這樣的問題,區區短篇,無以勝任。這里僅就《論稿》的體系發表一點感想,提供一點建議。
金開誠同志把文藝心理學分為五個部分:反映篇、表象篇、思維篇、情感篇和欣賞篇。這當然是有一定道理的。反映篇解決的是心理活動與現實的關系問題,表象、思維、情感都是文藝創作的心理要素。但我們能否建立一個更為科學的體系呢?也就是說使之具有更充分的心理學邏輯學依據?
人的心理活動包括認識過程、情感過程、意志過程三方面,這三方面的活動在一個人身上形成穩定的特征,與一個人的先天氣質相結合就構成一個人的個性。表象和思維在文藝創作活動中無疑是具有特殊意義的認識活動,但它們畢竟是認識過程的一個階段,把它們和情感過程并列,不便于分析。順便指出,“思維篇”忽視了一種重要的思維活動——靈感的討論。靈感是創造性思維的花朵,是一切作家、藝術家希冀的曙光。沒有它,一切文學、藝術之花都無法盛開。靈感與思維與想象的關系怎樣,怎樣幫助作家藝術家們獲得靈感,是文藝心理學不能不討論的問題。
文藝創作過程中需要不需要意志努力?從文學、藝術家傳記統計來看,是需要一定的意志努力的。就創作本身來說,自己所創造的形象會違背自己的觀點、態度,這就面臨著是讓他走自己的路,還是把它扼死在搖籃之中的痛苦抉擇;就創作的經歷來說,許多成功的文學家藝術家都有一段披荊斬棘、戰勝挫折所帶來的喪失信心的心理障礙的歷史。在我看來,人才學和文藝心理學應當從不同的角度來研究這個問題。
至于創作與個性的關系,早在古代就受到文學批評家的重視。劉勰在《文心雕龍·體性篇》中說:“是以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云沉寂,故志隱而味深……”由此類推,外表的文辭和內在的性情氣質,一定是相符合的。隋代的文論家王通也說:“鮑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吳筠、孔
文藝心理學不僅要研究創作心理,還要研究欣賞心理。欣賞與創作雖然是不可割裂的,但它們畢竟是兩種不同的心理活動,以個人之愚見,它們應構成文藝心理學的兩大組成部分。在欣賞過程中,起作用的無非也是認識活動、情感活動和個性心理特征。但這要從欣賞心理自身的角度去研究。國外的移情說、距離說、同構說可以給我們以有益的啟示。這些,《論稿》都還沒有來得及討論,看來也需要從理論和實驗兩方面加緊著手研究。
(《文藝心理學論稿》,金開誠著,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四月第一版,1.2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