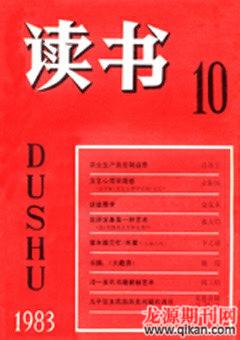批評本身是一種藝術
張大明
讀《李健吾文學評論選》
假如有一天我是一個批評家,我會告訴自己:
第一,我要學著生活和讀書;
第二,我要學著在不懂之中領會;
第三,我要學著在限制之中自由。
《李健吾文學評論選》第4頁
李健吾是文壇上有數的多面手之一。
他寫小說,短篇、中篇、長篇都嘗試過,表現手法上做過多種探討;經過五六十年的大浪淘沙,有的篇什依然能夠耀人眼目。他是戲劇家,創作豐富,有舞臺實踐經驗,還是北京話劇運動的開創者之一。他的散文寫得好,《意大利游簡》、《希伯先生》、《切夢刀》三個集子代表不同的風格。他是翻譯家,人們很難把他和福樓拜的名字分開。如果說,我們讀莎士比亞的戲劇,忘不了吳興華、朱生豪的功勞,讀巴爾札克、契訶夫的小說,贊嘆傅雷、汝龍的高超,那么,我們把玩《包法利夫人》等福樓拜的作品,一定記得李健吾的譯筆之優美傳神。他曾經在大學當教授,后長期從事法國文學研究,是一個方面的專家、權威。他更是獨樹一幟、個性鮮明的文學批評家、鑒賞家。如果我們要寫現代文學批評史,那么,李健吾及其《咀華集》一定會被專門論述。在《咀華集》以原版重印之前,讀到寧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健吾文學評論選》,令人高興,因為“這里收的大多是《咀華集》三種版本的全部文字。”(作者《后記》,第344頁)
他浩瀚,他豐富。見多識廣,獨具慧眼。難得的是評出了自己的風格;他以無可辯駁的實踐說明:批評本身也是一種藝術。
要牢牢記住他給批評家擬定的三條。“學著生活和讀書”,這是文學批評的基礎,起碼條件;“學著在不懂之中領會”,表示苦索,是克服困難,體味;“學著在限制之中自由”,說的是掙脫羈絆,這里有批評家的人格在。
文學批評面對的不是幾篇(部)作品,而是整個世界。這個世界五光十色,瞬息萬變,它每時每刻都是這樣,又不是這樣。你不在這個世界生活,不懂它的聲它的色,看不見它的動它的變,混沌無知,或者手足無措,無法變被動為主動,把白云撕得下來,把萊莉的香味分解得開,就不能認識作家,理解作品,體驗其味。李健吾的經歷不算復雜,卻也不單純。他出生時是清朝的臣民,長大了當民國的百姓;他曾目睹北洋軍閥混戰,更領受過抗日的烽煙;他家先前闊過,但很快就遭白眼;懂得帝都的紅墻綠瓦,熟悉天橋社會的立體交叉;從黃河流域,到燕山腳下,留學歐洲,定居上海,足跡萬里,橫跨幾個社會。這種稱得上豐盈的人生閱歷,為他認識作家作品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因此,他好象把面前的創作看得透,能觸摸到作家的感覺神經,把作品還原成生活,再經過他的再創造,就從本質上領略了作品的滋味。哪怕是他評論文章文筆之生動,比喻之頻繁使用和貼切,這樣細微的表現,都源于他對社會人生這本大書讀得滾瓜爛熟。
誰都佩服他書本知識的廣博。有國學的根基,又在歐洲的書山學海探幽覽勝,飽餐秀色。積學以儲寶,研閱以富才,于是他富有,他自由。他的任何一篇評論都要拉外國作家來幫助自己說話,加強自己的論證。是不是有賣弄知識、掉書袋的弊病呢?沒有。因為所拉來的助手是有思想有才能的,論點論據是新鮮的恰當的,而且又很知趣地做到了適可而止。時下的不少文藝理論批評家做不到這一點。我們缺乏修養,缺乏李健吾那樣的中外古今的文學知識。其實,不獨李健吾,凡是著名的文藝理論批評大師、有特點的作者,亦莫不如此。讀周揚的這類文章,時時就有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車爾尼雪夫斯基出來說話,有王陽明、李卓吾顯身作證,而且還不時捎帶盧卡契。這類文章即或不署名,它的作者是誰,有眼力的讀者也會猜個八九不離十。魯迅、茅盾、朱光潛、何其芳的文藝批評都有這個特點。他們的文筆輕盈、流暢,落筆自然、隨便。他們給你知識,教你方法,除在關鍵地方點一點而外,總是把想象留給讀者。他提供了足夠的條件,只要讀者發揮充分的主觀能動性,再一思索,一定能得到比他們表面所給予的還要多的收益。
論作家作品,他不局限于一人一書,而是將許多作家放在一起進行比較。有時本來要論甲,卻說了許多乙和丙,而真正落實到甲倒反而沒有多少話(指文字、篇幅的數量)。因為有了乙和丙,再將甲之不同稍稍點出,就抓住個性了。在比較之中見異同,尋規律,方能認識這個作家這個作品的特殊面目,并且使認識深化。真金比垮硫化銅,熱能烘托冷。比如,宗旨是論沈從文、何其芳,卻從廢名入手;中心是論巴金,卻先說了茅盾。這種方法,看起來寫得輕松、隨便,實際上大大不容易,它要批評者胸懷丘壑,見識寬廣,善于從文藝思潮、流派、藝術表現技巧等方面提出見解。它要求真正認識這個作家這個作品,對他們的個性了如指掌、爛熟于心,這才抓得準,不致于把衣角當成了衣襟、把敗筆認作長處,不致于把風馬牛扯在一起。
他眼界寬闊,思維和文筆都放得開。他總是從宏觀世界來觀察一個作家的作品,不拘泥于作品本身。因而評論一部作品往往從很遠很遠的地方說起。如他所說,在門外徘徊,正是走入作品的準備。他給予讀者的不是干癟的教條、蒼白的結論,而是引導讀者跟他一起馳騁想象,在藝術王國自由翱翔,在作家作品的精髓之所在棲息下來,讓你自己去吮吸。
他很少正面地、系統地、大學講義式地評論作家作品。常常是這樣:他領著讀者跋山涉水,將自然景物、人情世態盡收眼底;他把騷人墨客的趣聞軼事講給我們聽,把曹丕和福樓拜介紹給我們認識;他讓你時而佇立花前,觀其形,聞其香,時而登上泰山,俯視蒼穹。不知不覺來到藝術宮殿的堂奧。再交代幾句注意事項和著力要欣賞的部分,他就退場;讓你自己去看、去聽、去想,他絕不越俎代庖,絮叨饒舌,好為人師。因為我們已經跟他走了一程,接受過他的指點和開導,結識了有關的朋友,因而就已經有能力獨自去吸取,去發揮我們的聰明才智。
李健吾一再強調要從作家的全人格和全生活出發來批評他的作品。人文結合,由人以衡文,以文返看人。因此,他論的現代作家,大都是與他相識的人,他知道他們的出身、經歷、愛好、性格。(在敘述時,他不平鋪,戒有聞必錄,而是抓特點,在形成個人氣質、影響文學創作、鑄成藝術風格的部分,打上著重符號。)這對他是一種方便。他無須問津,即可進入他們耕殖的藝術園地;縱使阡陌交錯,港灣曲折,他也不會迷失方向。
藝術的堂奧是什么?是風格。李健吾從來不抽象地分析作品的主題思想,也沒有單調地宣示作品的現實意義。孤立地、靜止地、條分縷析地談情節結構、人物性格,容易流于膚淺,落入俗套,不能升堂入室。李健吾有膽有識,有勇有謀,橫沖直撞也好,迂回包抄也.好,總要直抵堂奧,進入核心。
風格是藏于作品人物、情節背后的作者總的情緒、志趣和追求,是一部作品、一個人的創作給讀者的總的印象。它不是明寫在作品的表面的,因此必須從文字之外去感知,去體味,去把握。李健吾在表述這種印象時,全不用概念,不簡單生硬地舉幾個例子,得出“清新”、“俊逸”、“含蓄”、“明快”、“抒情”、“理性”等空洞的結論,而是用形象,用比喻,用情感的跳躍,用觸角神經的顫動。關鍵是不脫離人。有人才有風格。論何其芳的《畫夢錄》,不忘他是哲學士。哲學家的頭腦,藝術家的眼睛。淺顯的邏輯,美好的姿態,追求顏色、音樂、圖案。因此他散文的詩意中含有哲理。論陸蠡的散文,從生活說到取材,從人格講到風格。陸蠡做事認真,作風踏實,剛直不阿,有民族氣節,“本質近于詩”(第191頁)。因為他本身就是詩,化而為文,必定“照亮了人性的深厚”,“蘊借力量于勻靜”(第190頁)。對巴金,說“他有一個敏于感受的靈魂,這靈魂洋溢著永生的熱情,而他的理性猶如一葉扁舟,浮泛在洶涌的波濤。”(第44頁)“熱情就是他的風格。”“他生活在熱情里面,熱情做成他敘述的流暢。”(第17頁)巴金熱情,他善于觀察,精于捕捉,長于敘述,文如水淌,他的小說有一種信仰。主人公為追求這信仰而生而死而戰斗。對信仰的追求就構成人生的內容。巴金不僅寫了封建家族制度的潰敗,一代青年的覺醒,而且視野很廣,題材很寬,一些作品還彌漫著異國情調。同樣,李健吾論沈從文、廢名、李廣田等人的藝術風格都很精到。尤其可貴的是,剛剛登上文壇、才貢獻一部作品的穗青、郁茹、路翎,也引起他的重視,對他們的正在孕育之中的風格都有比較準確的把握,而為日后的事實所證明。
魯迅寫文學史,《中國小說史略》和《漢文學史綱要》是一種寫法,《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和《上海文藝之一瞥》又是一種寫法。茅盾提出,還可以有一種寫法:先簡明扼要地敘述歷史的發展,擺擺情況,再旗幟鮮明地亮出自己的觀點,但不必詳盡分析,末附有關原始論文,讓這些資料自己出來說話。
同樣,文藝批評也應該寫成多種多樣的樣式。
拿魯迅來說,不說不同時期、對不同作家作品的評論寫法不一樣,就是同一時期對同一《奴隸叢書》中的三本小說所寫的序,也都搖曳多姿,各各耐人尋味。序葉紫的《豐收》,只說集子中的小說“都是太平世界的奇聞”,因而“和我們更密切,更有大關系”,卻以更多的篇幅批評“第三種人”,用葉紫的事實說明:“文學是戰斗的!”序蕭軍的《八月的鄉村》,說古論今,好象離題太遠,實則貫穿一個侵略與反侵略的主題。到了談小說的時候,只用抒情的語言,象寫散文一樣,使你急于要看作者是如何在“顯示著中國的一份和全部,現在和未來,死路與活路”的。序蕭紅的《生死場》,說“敘事和寫景,勝于人物的描寫,然而北方人民的對于生的堅強,對于死的掙扎,卻往往已經力透紙背;女性作者的細致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又增加了不少明麗和新鮮。”這真叫一語中的!兩句話把小說的主旨和作品的風格道盡,而且因為顧及書的銷路,用語十分斟酌,連批評都成了好聽的話,三篇序都寫得毫不費力,集中談作品的只有畫龍點睛的一兩筆。它們是那樣傳神,那樣準確,那樣深刻!在現代文學史上,對新人新作評介得最多的,恐怕要首推茅盾。因為是評介,寫法上往往復述、引文較多,但篇篇都有真知灼見,且往往決定那個作者一生的創作風格、創作道路。錢谷融的《<雷雨>人物談》,分析細膩,重在點的深入;那淵博的外國文學知識,增強了文章的說服力。李健吾的“咀華”完全屬于他自己。一件成功的文學藝術作品(尤其是其中的典型人物形象)是作家和評論家共同創造出來的。作家提供形象,評論家通過再創造,發掘出形象的意義。這再創造一般讀者(包括評論文章的讀者)也要參加。李健吾充當了引路人,并在關鍵時刻、關鍵地方給人啟示。乘船出長江三峽,廣播員若不提前講述歷史故事、神話傳說,及時提醒朝哪兒看,怎么看,準確地啟發想象,游客一定會錯過許多勝景,嘆息抱憾。李健吾文學評論、鑒賞文章在寫法上的奧妙即在此。
除了時代背景、作者生平、主題思想、人物形象、寫作技巧、缺點錯誤、現實歷史意義、努力方向,這樣固定的古板的常用的寫法而外,文藝批評應該有多種寫法,應該多有一些人嘗試。單就給人知識、啟發人思索、帶人到學海散步這一點,李健吾的“咀華”就值得重視。
一九八二年春初稿
一九八三年初夏修改
(《李健吾文學評論選》,寧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三月第一版,1.03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