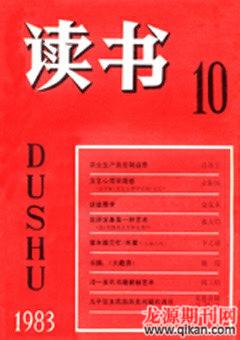名教的破滅
閻步克
近來,倫理思想史的研究日被重視,這是很有意義的。中國古代思想的特點是輕智術而重人倫。古希臘有所謂“智者”,以雄辯和機智取勝。而古中國卻以“圣賢”為最高人格。“白馬非馬”一類名辨,被視為末流小道。自漢武帝“獨尊儒術”,儒家“人倫”經“天人感應”說的點化一變而成“天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設計成了王朝行政的指南,“三綱五常”的道德體系也就具有了無上的權威,成為臣民之行為軌范了。所謂“漢家以孝治天下”,正反映了古中國“倫理政治”的特色,古人則名之為“教化”。
日人巖崎武雄認為,從實踐觀點看,“法是道德的最小限度。……道德上比較輕微的過錯,沒有必要作為法律制裁的對象。可是,由于殺人、盜竊之類事情是極其嚴重的道德過錯,所以必須作為法律制裁的對象。”(《現代世界倫理學》277頁)中國古代的法律并不完善,道德制裁卻作用極大;同時法律又侵入道德領域,違背綱常要受法律制裁,早在《尚書·康誥》中已有“不孝不友……刑茲無赦”語。儒家禮教不但兼有道德、法律、神道三種意味,而它的奉行者,更受到榮祿的褒獎。漢代察舉“孝廉”為官,為國家定制。《廿二史札記》“東漢尚名節”條云:“馴至東漢,其風益盛。蓋當時薦舉征辟,必采名譽,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以赴之,好為茍難,遂成風俗。”東漢統治者格外重視名教禮法,倡導之下,士大夫們爭相以德行相標榜。名教益隆,名節益貴,東漢一朝,蔚成風氣,可稱大觀。對此,后人多有論說。
然而,讀史者亦常常注意到這一問題:世入魏晉,世風卻陡然一變,神圣的名教,忽而一落千丈了。魏明帝以后,社會風氣日趨浮涎。至西晉名士如謝鯤、王澄、阮瞻之流,降而為放蕩不羈、荒誕無恥,一發不可收拾了。史稱當時“風俗湮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老莊為宗而絀六經,談者以虛薄為辨而賤名檢,行者以放濁為通而斥節信,進仕者以茍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放空為高而笑勤恪。”(干寶《晉紀》)“或亂項科頭,或裸袒蹲夷,或濯腳于稠眾,或溲便于人前,或停客而獨食,或行酒而止所親。……皆背叛禮教而從肆邪僻,訕毀真正,中傷非黨,口習丑言,身行弊事。”(《抱樸子·刺驕》)名士阮咸以大盆盛酒,與群豬一同狂飲。名士謝鯤調戲鄰女,被以梭打落二牙,還自鳴得意:這不妨礙我高歌呀!他們“相與為散發保身之飲”,甚至“對弄婢妾”為樂。
兩漢數百年的道德信條,一時被人棄之如敝展,陷入非道德主義之泥坑,不能不發人深思。許多學者對此有多方面的精到論說。但仍有一點值得注意。宋人程顥說:“東漢之士知名節,并不知節之以禮,遂至苦節。苦節已極,故魏晉之士變而為曠達。”說“名節”變成了極端化的“苦節”是其衰亡的原因,這卻提供了一條線索。東漢末年士大夫追逐名利,標榜名節,趨之若鶩,把禮教推崇到極端,這就不能不流入虛偽一道了。恪守名節盡管又難又苦,對于作態求名,卻反為捷徑,甚至不妨走走極端。怪事便應運而生了。一是乖背人情。當時被稱道的,都是在苦孝父母,長期居喪,讓爵于人,讓財于親,不肯作官等事上爭相比賽的,毫無意義。如丁蘭幼喪父母,便刻木人作父母來服事。袁紹說父母死時他尚小,三年居喪不算數,便又補上三年。這皆令人難以接受。二是挑剔苛求。如陳紀喪父,因哀傷而瘦弱,其母“竊以錦被蒙之”,名士郭泰便裝腔作勢大加斥責,“奮衣而去”。如此無聊的吹毛求疵卻被哄然響應,陳家幾個月都無賓客上門。由此可見時風之一斑。當時有所謂“清議”,以許邵的“月旦評”最為著名,專事評頭品足。三是虛偽造作。如趙宣在墓道為父母居喪達二十多年,屢次被請作官而不就,是名動一時的大孝子。后來卻被發現在墓道中生了五個兒子。又如許武被舉孝廉后,與兄弟分家有意多取,兩弟弟便以讓財出名被舉孝廉。許武又宣布自己讓兄弟成名的苦心,又將財產分還兩弟。如此虛偽,卻被“遠近稱之”。
今天看來,這些都悖情違理,虛偽透頂。名教到此地步,就離破滅不遠了。魯迅曾經說過,道德理想“必須有個意義,自他兩利固好,至少也得有益本身”,如果“很難、很苦,既不利人,又不利己”,便當拋棄。這是符合道德規律的。黑格爾也曾指出:“實體性的理性規定,必須通過自由才能成為倫理的信念;——而這樣的自由(在中國人那)是缺乏的。”(《歷史哲學》)他以為在古中國,道德實為一種外在強制,而非個人意愿判斷下的自由選擇。這確實是精辟的議論。封建主義的道德教育,只知樹立一套指導行為的社會規范,叫人死記硬背和盲從,卻無法養成人們自覺的道德判斷和抉擇的能力,因此這樣的道德基礎就不能不是脆弱的。漢統治者推崇禮法名教,以榮祿引誘之,以刑罰懲罰之,以神道欺騙之。而士大夫們競相崇奉,已有宗教迷狂的意味。這種已非理性的、正常的道德情感和道德信念,是決不會有真正生命力的。一旦社會動蕩,這種“苦節”便立趨衰微了。道德至上主義和非道德主義,竟然只有一壁之隔,歷史的辯證法何等無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