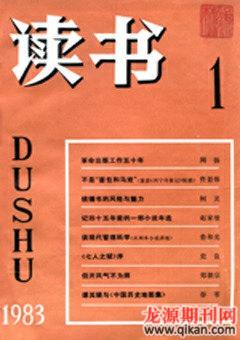不是“面包和馬戲”
瑙姆·嘉博 等
重讀《列寧印象記》隨感
三聯(lián)書店一九七九年再版的《列寧印象記》,是杰出的共產(chǎn)主義女戰(zhàn)士克拉拉·蔡特金在列寧逝世后不久寫的一本回憶錄。書中生動細致地敘述了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二年間列寧同蔡特金的幾次會見和談話,為我們了解十月革命初期列寧的工作、生活和思想提供了極其寶貴的資料。其中列寧談到藝術(shù)和文化建設問題的部分,已經(jīng)收入《列寧論文學與藝術(shù)》一書,成為馬列主義美學和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正是在同蔡特金的談話中,列寧針對當時在蘇聯(lián)出現(xiàn)的一些盲目仿效西方藝術(shù)“時髦形式”的做法,發(fā)表了他對現(xiàn)代派的那個著名評價:“我不能把表現(xiàn)派、未來派、立體派和其他各派的作品,當作藝術(shù)天才的最高表現(xiàn)而加以贊賞。我不懂它們。它們不能使我感到愉快。”也正是在批評了當時蘇聯(lián)藝術(shù)界中的一些混亂現(xiàn)象之后,列寧提出了“藝術(shù)屬于人民”這個經(jīng)典性的表述,明確指出在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之后,藝術(shù)必須深深扎根于廣大勞動群眾的底層,必須團結(jié)他們、提高他們,并喚起和發(fā)展他們的藝術(shù)才能。接著列寧又進一步指出,為了使藝術(shù)可以接近人民,人民可以接近藝術(shù),必須首先提高教育和文化的一般水平;我們的工人和農(nóng)民進行了革命,以空前的犧牲和鮮血保衛(wèi)了自己的事業(yè),他們有權(quán)利享受真正的、偉大的藝術(shù);人民是文化的土壤,在這個土壤上將成長起一種內(nèi)容和形式都好的、真正新興的、偉大的藝術(shù),一種共產(chǎn)主義的藝術(shù);我們的藝術(shù)家只有理解并完成這些極其重要的崇高的任務,才算是對無產(chǎn)階級革命盡了責任,因為無產(chǎn)階級革命也向他們敞開了通向自由的大門,即擺脫《共產(chǎn)黨宣言》所精辟地指明的那種悲慘處境。
列寧在半個多世紀之前為我們描繪的這幅光輝的藝術(shù)發(fā)展圖景,在黨的十二大把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任務提到戰(zhàn)略的高度,確定了黨在這個問題上的根本的理論觀點和行動方針之后,不能不使我們感到格外地親切和備受鼓舞。特別是正當我國藝術(shù)界力求克服極左路線所造成的后果,開闊眼界,大膽創(chuàng)新,同時在對待西方現(xiàn)代派的問題上也出現(xiàn)了某些糊涂觀念之際,重溫列寧的這些教導,很有助于我們澄清對這些問題的認識。
自從進入二十世紀以來,形形色色的新美學、新藝術(shù)層出不窮,藝術(shù)中的“現(xiàn)代熱”此起彼伏,其花樣之多,變化之快,實為既往任何時代所罕見。但是,在二十世紀,究竟哪一種美學和藝術(shù)才是代表時代和社會進步的真正新的美學和藝術(shù)呢?
在西歐和美國,幾十年來出了不知道多少精致考究的現(xiàn)代藝術(shù)和美學著作。人們長篇大套地建立和鼓吹著一個比一個新奇的學說和體系。克羅齊的《美學原理》在一九二八年出了第六版,他要用“直覺”來排除掉藝術(shù)的“雜質(zhì)”,因為“藝術(shù)與真理和道德無關(guān)”,用另一個意大利評論家——塔里亞布埃的話說,他“確立了藝術(shù)的獨立性和純潔性”;英國的“克羅齊專家”埃德加·卡里特并且據(jù)此發(fā)揮說,看一幅油畫如果還要了解它的名稱或主題,那只是“證明著審美上的無能”。科林伍德的《藝術(shù)原理》決心緊跟三十年代的新型詩歌和繪畫,他說,讀者如欲了解藝術(shù)是什么,只要讀一下艾略特的《荒原》就明白了,它反映了現(xiàn)代文明給人所留下的最后一種感情:恐懼。桑塔亞那以他的“唯物主義”與克羅齊的唯心主義相抗衡,一九三九年他在《總懺悔》中重申了早年寫的《美感》和《藝術(shù)中的理性》的人道主義:知識、宗教和藝術(shù)所提供給我們的價值,都是由人的欲望決定的,美的享受的根源是包括性本能在內(nèi)的各種人性。他認為藝術(shù)家創(chuàng)造藝術(shù)是利用僥幸的偶然性,而藝術(shù)理論家的任務則是要揭示出這些偶然原因和各種不同美的類型的肉體本源。
在七嘴八舌、各執(zhí)一詞的爭論之中,唯有精神病科醫(yī)生弗洛伊德和他的學派得天獨厚、經(jīng)久不衰。正如美學史家凱瑟琳·吉爾伯特所說,精神分析學對模糊不清的、下意識的象征所作的解釋,以其為一切神奇玄妙事物所固有的誘惑力而受到廣泛的歡迎,并因此而成為各個對立的流派共同討論和解釋的對象。列奧納多·達·芬奇的名作《蒙娜麗莎》中的“神秘的微笑”,幾乎成了美術(shù)史家們的一個神秘的專題,而弗洛伊德運用他那萬能的“性本能”、“潛意識”和“戀母情意綜”,卻可以輕而易舉地把它一語道破。他說,這女主人公的微笑,可能是反映了過分敏感的私生子同遭到遺棄的單身母親之間的一種特別強烈的相互眷戀之情,也可能是由一個充滿童年回憶的某種幻覺所喚起的。這只是弗洛伊德學說在美學上的一個小小的妙用!正因為它如此神通,所以先前以及后起的各種符號和象征美學、實證主義美學和語義學美學等等,都競相把精神分析學當成一大法寶接了過去,各種現(xiàn)代派文學、詩歌和繪畫,也無不含有它的種子,或拖著它的影
是的,所有這些美學和藝術(shù)流派,除了蓄意否定一切傳統(tǒng)和標新立異的因素之外,在一些具體的美學問題上,在藝術(shù)的形式和風格手法方面,各自也都有所發(fā)明和發(fā)現(xiàn),其中并且不乏可資我們學習和借鑒的東西。尤其從了解資本主義的精神危機來說,許多作品還具有不小的認識價值。因此,對待屬于這些流派的藝術(shù)家和作品,我們都要具體分析,決不能籠統(tǒng)地一概排斥和否定。根據(jù)列寧的教導,我們從中也可以“吸取人類所積累起來而為我們所必需的一切”。
現(xiàn)代派藝術(shù)伴隨了資本主義各國自本世紀初迄今的整個發(fā)展過程,這本身就說明它是藝術(shù)史上的一個重要的和必然的階段,我們必須認真了解、研究而決不可以忽略。問題只是,我們是否應該不分青紅皂白,如列寧所批評的那樣,只是因為那是“新”的,就要把新的東西當作供人信奉的神一樣來崇拜,或者如列寧的另一個說法那樣,在這方面保持一種“藝術(shù)偽善”,對西方藝術(shù)時髦抱著“不自覺的尊敬”?而現(xiàn)在確實存在這一類情況。
無論現(xiàn)代派藝術(shù)有多少值得學習和借鑒的東西,代表二十世紀時代和進步的新美學和新藝術(shù)決不能是強調(diào)本能和尋求刺激、鼓吹荒謬和脫離生活的藝術(shù),決不能是徒具虛名的新形式!二十世紀的新美學和新藝術(shù),必須能夠掌握千百萬人的心靈,成為他們改造世界和改造自己的武器。它們既不能籠統(tǒng)地排舊,也不能盲目地崇新,而應象馬克思主義本身一樣“從全部人類知識中產(chǎn)生出來”。它們應象列寧在《青年團的任務》中論述無產(chǎn)階級文化時所說的那樣:“只有確切地了解人類全部發(fā)展過程所創(chuàng)造的文化,只有對這種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設無產(chǎn)階級的文化,沒有這樣的認識,我們就不能完成這項任務。無產(chǎn)階級文化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那些自命為無產(chǎn)階級文化專家的人杜撰出來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一百多年前就已指出,工業(yè)革命是人的創(chuàng)造力的完全解放的必要前提,未來的共產(chǎn)主義聯(lián)合體必將使每個人都有充分可能從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文化——科學、藝術(shù)、交際方式等等——中間承受一切真正有價值的東西;并且不僅是承受,而且還要把這一切從統(tǒng)治階級的獨占品變成全社會的共同財富和促使它進一步發(fā)展。從這個偉大的社會理想的提出,到列寧在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問世之初,就把藝術(shù)接近人民、人民接近藝術(shù)的任務提上蘇維埃政權(quán)的議事日程,一直到在爭取實現(xiàn)四個現(xiàn)代化的新時期,我們黨又再一次明確規(guī)定了藝術(shù)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根本方針,這是世界美學和藝術(shù)史上的一次最偉大的變革,它把一向被排斥在美的王國之外的千千萬萬人民尊為藝術(shù)和文化的主人。這也是社會主義革命所帶來的一次必然的變革,而不是在書齋、學院和畫室中杜撰出來的。從根本上說,這也是工業(yè)革命或現(xiàn)代化的必然結(jié)果,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的。列寧說得好:“我們關(guān)于藝術(shù)的意見是不重要的,象我國這樣以千百萬人計的人口,藝術(shù)對其中幾百人或幾千人的貢獻也是不重要的。”在資本主義國家,藝術(shù)為少數(shù)社會“精華”服務,在我們這里,藝術(shù)和社會理想、文化和新人的成長,美和真理與道德,是分不開的,一切新的形式也都是按照社會主義的藝術(shù)即“真正新興的、偉大的藝術(shù)”的內(nèi)容規(guī)定的。
在列寧當時的現(xiàn)代派畫家之中,有一個瓦西里·康定斯基。《現(xiàn)代繪畫簡史》的作者赫伯特·里德說,康定斯基和其他現(xiàn)代派畫家對現(xiàn)代藝術(shù)運動發(fā)展所作的貢獻,比任何其他藝術(shù)家的貢獻都要大。他本來是一個俄國人,一九○○年在慕尼黑皇家美術(shù)學院畢業(yè)后一直在法國、突尼斯、意大利和德國各地“漫游從師”,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后回到俄國。十月革命后,從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一年,他先后被任命為重新建立的莫斯科美術(shù)學院教授、教育委員會委員、繪畫文化博物館館長(負責全國畫廊的組織工作)、莫斯科大學教授和新建的藝術(shù)科學院副院長。列寧在同蔡特金談話時曾說:“我們已經(jīng)設立了宏偉的學院并采取了真正良好的步驟,使無產(chǎn)階級的和農(nóng)民的青年能夠?qū)W習、研究、獲取文化。”康定斯基任職的這些機構(gòu),毫無疑問都正在革命政府所采取的那些真正良好的步驟之列。早在一九一○年,康定斯基就寫了一篇“有歷史意義的論文”,陳述了這樣一個信念:人類正在走向藝術(shù)史上的一個嶄新的時代。這篇論文被赫伯特·里德稱為“第一部新的藝術(shù)信念的啟示錄”。那么,這個“新藝術(shù)”的預言家,在革命為真正新興的藝術(shù)和藝術(shù)家們敞開了通向自由的大門之后,在那么多重要而崇高的崗位上,又做了一些什么呢?
在列寧談話的那些年間,康定斯基正繼續(xù)創(chuàng)作著他那些“不拘形式的”即興之作,又叫做表現(xiàn)主義的抽象。這所謂“不拘形式”,就是指從“母題”(如風景和人物)中解放出來,使繪畫“非客觀化”。據(jù)研究家考證,這是康定斯基從筆觸和斑點的苦心經(jīng)營中獲得的“一個驟然的突破”。據(jù)康定斯基本人自述,則完全是一個偶然的發(fā)現(xiàn):他一次回家打開工作室的門,遠遠看見自己一幅斜立著的油畫,只有明亮的色塊,“驚得他手足無措”,于是明白了一件事:繪畫上不需要有什么客觀的東西和客觀物體的描繪,這些東西實際上對繪畫是有害的。當時在莫斯科,還有一個馬列維奇,自稱“至上主義者”,主張藝術(shù)既不必再現(xiàn)對象,也不應要“有意識的觀念”,而是唯以顏色和形狀對感情的刺激作用為決定性的因素,他要以此而使藝術(shù)達到非客觀的表現(xiàn),即一種“至上的境界”,又叫做純粹主義。此外還有塔特林、羅德欽柯、嘉博和佩爾斯奈爾等一批畫家、雕塑家,搞所謂構(gòu)成主義,即把藝術(shù)創(chuàng)作歸結(jié)為各種材料的三度空間結(jié)構(gòu)和生產(chǎn)主義,即主張以制造實物取代藝術(shù),因為藝術(shù)是資產(chǎn)階級唯美主義的東西。所有這些“新藝術(shù)”的大師們,如赫伯特·里德所說,“在大戰(zhàn)和內(nèi)戰(zhàn)的旋風之中,在極端的物質(zhì)困難和政治傾軋(!)之中”,在學院和畫室里,從理論上和具體試驗上,不斷進行著自己的“創(chuàng)新”,把從西歐搬來的表現(xiàn)派、未來派、立體派和其他各派的東西,加上一些有如上述的那種革命詞句,在定期的公開討論會上討論,消除著互相之間的分歧,并因此受到“無產(chǎn)階級文化派”的喝彩。
所以,毫不足怪,列寧不僅對舊政權(quán)使大多數(shù)人受不到教育和沒有文化無比憤慨,對革命后已經(jīng)做的大量文化工作毫不滿足,對一時不可能使廣大人民、特別是青少年和兒童都受到教育和培養(yǎng)深感苦惱,而尤其對當時藝術(shù)和文化生活中的無視人民的各種表現(xiàn),更是表現(xiàn)了那樣不可容忍的嚴厲態(tài)度。他向蔡特金說的下面這段話,今天聽來仍然是發(fā)人深省的:“我知道!許多人真地相信,當前的困難和危險是能用‘面包和馬戲來克服的。面包——當然!馬戲——沒意見!但我們不可忘記,馬戲決不是一種偉大的、真正的藝術(shù),而不過是一種比較有趣的游藝罷了。我們不要忘記,我們的工人和農(nóng)民決不是羅馬的流氓無產(chǎn)者。他們不是受國家供養(yǎng)的,而是以自己的工作支持著國家……”
“面包和馬戲”是羅馬帝國時期的詩人優(yōu)維納利斯的著名警句,它諷刺了貴族用免費的糧食和流行的娛樂(斗獸場的演出)來安撫和拉攏平民即自由無產(chǎn)者的政策,同時也寓有針砭平民胸無大志、安于充當食客和低級娛樂,亦即丹納在《藝術(shù)哲學》中所說的“公民變成庶民”之意。有人曾對列寧的這段話發(fā)生誤解,以為列寧似乎對馬戲或雜技這種藝術(shù)的意義估價過于不足。這段話的意思當然不在于此。馬戲和任何藝術(shù)形式一樣有高有低。列寧引用這個典故的含義,我認為是非常深刻和多方面的。整個說來,它指的是對待藝術(shù)和人民的關(guān)系問題上的一種錯誤的態(tài)度。具體地說,它還包括有對于藝術(shù)家熱衷于時髦,向人民提供低級趣味的東西,或者不顧人民利益和需要另搞一套等等做法的批評,以及革命和人民對藝術(shù)應該提出更高的要求等等思想。
蔡特金聽了列寧的談話后不禁感嘆,有些人居然會把一個如此熱愛人民的人看成是一架冷酷的思考機器。說共產(chǎn)黨人不懂得人和文化的價值,自《共產(chǎn)黨宣言》時起就屢見不鮮。可是讀一讀《列寧印象記》,僅僅這一本小冊子就充滿著對文化、對人、對千千萬萬人民的何等關(guān)心和熱愛啊!有人似乎認為馬克思主義在美學方面沒什么貢獻。別的統(tǒng)統(tǒng)不說,單是《列寧印象記》的第六篇即最后一篇,就比不少美學論著高明。《列寧印象記》這本書值得文學藝術(shù)工作者一讀。
《列寧印象記》,〔德〕蔡特金著,馬清槐譯,三聯(lián)書店一九七九年五月第二版,0.21元)
佟景韓/康定斯基/馬列維奇/瑙姆·嘉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