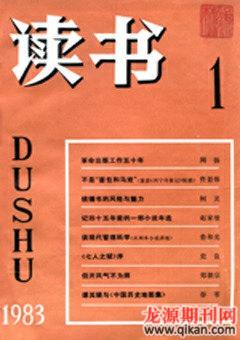古典目錄學津逮
崔文印
我國古代目錄學的成就,除解放前姚名達先生寫過一本《中國目錄學史》外,解放后還沒有人作過系統的介紹。南開大學來新夏先生的新著《古典目錄學淺說》的出版,無疑填補了這一空白。
《淺說》的最大特點,正如它的書名所標出的,就是“淺”。所謂“淺”,即通俗、深入淺出、簡明扼要。為了使廣大讀者,特別是對古典目錄學還不甚了然的讀者便于入門和讀通、讀懂,作者用一章的篇幅,對目錄的概念,目錄學的產生、類別、體制,以及目錄學的作用等基本問題,都作了精辟的說明。很顯然,讀者有了這些基本知識,再讀下去就較容易了。這一章的安排,體現了作者不愧是長期從事教學工作的老同志,的確是循循善誘。
在上述基礎上,作者按時代分別介紹了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的目錄學成就。作者在介紹過程中,抓住了每個時期目錄學發展的特點,勾勒了我國古代目錄學的發展輪廓。我們僅從《淺說》的標題就可以看出,漢代是我國官修目錄和史志目錄的創始時期,劉向的《別錄》、劉歆的《七略》,可說是我國官修目錄的先驅,而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則是我國史志目錄的鼻祖。魏晉南北朝是我國目錄學四分法和七分法并存的時期,前者可以魏鄭默的《中經》、晉荀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介紹這些目錄學成就的時候,并不是孤立的、單純的羅列事實,而是把這些事實放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加以分析、考察,力圖揭示出目錄學發展的一般規律。例如西漢曾進行過三次大規模的求書和圖書整理,產生了我國第一代目錄學著作。這三次求書和圖書整理,一在漢初,二在武帝時,三在成帝時。作者在介紹這些史實時,首先指出:“目錄事業的興起、發展和圖書的聚集有著密切相連的關系”。漢“接受了秦朝毀滅圖書的教訓,‘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使散失的圖書得以適時的聚集和收藏。這都為整理編目工作的開展準備了條件。”(本書第二章第一節)漢初,由于天下初定,百廢待興,急需要定法規立制度,于是“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朝儀”。(《漢書》卷一《高帝紀》)據班固《漢書·藝文志》記載,“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足見這次“申軍法”并“定章程”等確實是在整理秦時留下的圖籍、文獻基礎上進行的。這里,作者顯然并不滿足只是介紹史實,使讀者知其然,而是通過分析,進一步使讀者知其所以然。再如《兵錄》是我國第一部專科目錄,作者對它的產生作了如下分析:特別是“經過‘文景之治的恢復和發展,全國已呈現出一種大一統局面。武帝為了擴展漢帝國,除了在政治上、經濟上采取相應的措施外,對于思想文化方面更提出了‘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口號,圖書也相應地作為實現其加強思想統治的重要工具而受到應有的重視……這時武帝正積極用兵,急需參考軍事圖書,因此就命軍政楊仆首先整理兵書,編制成一份專科目錄《兵錄》”。(本書第二章第一節)
我們從上述敘述中至少可以看出,目錄學的發生和發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有著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等等廣泛社會因素。我們只有透過這些社會因素,才能探求目錄學發生、發展的原因,我們才能解釋在目錄學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各種新情況。比如,隨著社會的穩定和雕版印刷事業的發展,私人大規模藏書有了可能,這時,也僅僅在這時才會出現私家目錄。某部私家目錄的產生也許有一定偶然性,但這類目錄勃興于宋元則是必然的。這就是規律!必須指出,《淺說》主要是講史,而不是一部關于目錄學理論研究的著作,但作者卻能夠以論帶史,使讀者既得到了目錄學史方面的知識,又在目錄學研究理論方面受到很大啟發,這是這部書的一個突出特點。
這部書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持論公允,特別是遇到學術界尚有爭議的問題更是如此。如目錄學是否能獨立為學的問題就屬這一類。目前,學術界尚有相當一部分同志認為只有校讎學,沒有目錄學,目錄學應包括在校讎學之中。宋代的鄭樵,清代的全祖望、章學誠、朱一新,乃至近人張舜徽都持這種看法。盡管來新夏先生不同意這種看法,但他卻能充分地擺出上述諸家關于這個問題的重要言論,然后申以己見。來新夏先生認為:所謂“校讎”,劉向在《別錄》中早有解釋,即“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其謬誤為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為讎”。這說明,校讎只是“指校勘文字篇卷的錯誤”。“它是劉向整理圖書工作的一道工序,不能表明全過程”。(引文見本書第一章第一節)目錄學不只是“記其撰人之年代,分帙之簿翻”,“多識書名、辨別版本”的“書目之學”,而是要“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然后“別集眾錄”而成書。這就是說,全部工作是要“經過整理篇次,校正文字,辨明學術,介紹梗概,撰寫書錄,最后把全過程的成果集中反映為目錄”。來新夏先生強調,“其全部工作過程既用目錄之名來概括,那么,對所以達成最后成果的各個研究環節總稱之為目錄學又有何不可呢?”來新夏先生不強加于人,他把雙方的論點、論據擺得十分清楚,孰是孰非讀者自會鑒別。
還應該提出的是,作者十分注意吸收新的研究成果。如關于書的裝幀問題,古代有一種“旋風裝”,其解釋以前大都采用劉國鈞的說法,即“由印成的單葉粘成長幅而后再折疊起來”,“首尾粘連一氣,因此翻到最后一頁的襯后,便可以連著再翻到首頁。往復回環有如旋風,所以叫做旋風裝。”(《中國古代書籍史話》)一九八一年,北京圖書館善本室李致忠對此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認為,旋風裝就是在卷軸式的底紙上,將書葉鱗次相錯地粘裱,打開時,形似龍鱗,所以稱為龍鱗裝;收卷時,書葉鱗次朝一個方向旋轉,宛如旋風,所以又稱為旋風裝或旋風葉卷子。來新夏先生認為后者明白易懂,有道理,盡管當時《淺說》已發排,但他仍堅持改為后者。他曾對筆者說過,既然已經覺得前說不如后說,就應該把自己認為正確的東西獻給讀者,這一點是再麻煩也要做到的。這些都反映了作者的認真精神和對讀者的負責態度。
寫到這里,很自然使我想起了一個與此相關的問題,就是作者的治學態度十分嚴謹。從《淺說》可以看出,作者不說空話,所有論點,必建筑在豐富的材料基礎之上,而且,每一條材料都注明了詳細的出處(書名、卷數等),使讀者很容易核查。所以,此書雖“淺”,但卻雅俗共賞。普通讀者固然可以通過此書了解我國古代目錄學概況,專業讀者亦可通過此書獲得研究我國古典目錄學的許多材料和線索。
本書還對與目錄學相關的學科:分類學、版本學、校勘學都作了簡要介紹。這不僅使讀者對古典目錄學更加深了了解,而且也給讀者指出了通往古典目錄學的多種門徑。前人有所謂“津逮秘書”,津逮者,入門,且由此登堂入室之謂也。對于有志于古典目錄學研究的讀者來說,來新夏先生的新著《古典目錄學淺說》不正是這樣一部書嗎?
(《古典目錄學淺說》,來新夏著,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十月第一版,0.74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