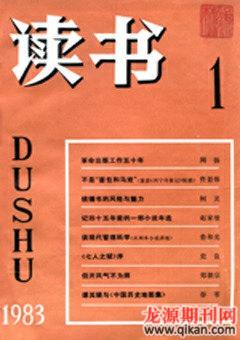他山之助
施 闌
讀《古書畫鑒定概論》
在中國,書畫作偽的歷史,大概也不算太短。但究竟發軔于何時,還不曾確考,僅據現有的資料看,至少在唐代就有了。晚唐畫家程修己墓志中,記有他偽制王羲之書帖的事:“……丞相衛國公聞有客藏右軍書帖三幅,衛國公購以千金,因持以示公(即程),公曰:‘此修己紿彼而為,非真也。”這是唐時書畫作偽的一個實例。再據米芾《畫史》所記,則有:“李成真見兩本,偽見三百本。”米氏是書畫博士,他見到的北宋內府收藏的李成畫跡,贗品竟多至三百幅。照米氏的說法,這些假畫,“皆俗于假名”。其實,高手也同樣“假名”,米芾自己就是一個作偽的專家。不過早期作偽大都出于游戲,顯示作偽者技藝高超,足以亂真。
既有偽跡,必然要有識辨偽跡的方法。但前人卻沒有把這方面的經驗整理成篇,即或有,也只是一些書畫史和公私書畫著錄,真正把鑒別書畫的經驗系統地寫成專書,則是新中國誕生以后才有的。徐邦達先生的《古書畫鑒定概論》正是這樣一種專門的著述。
鑒定,對于歷史文物,尤其是對那些時移世隔的古書畫,無疑是重要的,因為只有經過必要的鑒定,才便于收集、整理、保護、研究,有裨于今用。
古代書畫大都是傳世品,比起鑒別其他文物,要復雜得多。有些書畫即使前人有過著錄,但也相當簡略;加之可以憑借的資料又少,要想有效的辨偽存真、考定年代,只有靠多年積累的經驗。《概論》一書的著者正是以他從事這項工作的實際經驗,就書畫鑒定中的各種問題、有關的知識,分章講述,舉重若輕;把一些比較錯綜的問題、現象,聯系產生這些現象、問題的歷史條件和原因,作了扼要的說明。
《概論》一書特別注重科學性。它反復強調了大量親身接觸古書畫實物對鑒定書畫的意義,并把這一觀點貫串全書。一般人常常把古書畫的鑒定看得很神秘,有的甚至認為古書畫的鑒定沒有什么科學性,可以信口胡謅。這當然是誤解。實際上鑒定古書畫并不神秘,它依靠的就是——多看。這個道理既復雜又簡單。對一個作家的作品看得多了,他的作品的筆法、氣韻、風格爛熟于胸中,作品展開,就能真偽立見。這猶如見到老朋友,無須端詳、思索就可認出。用著者的話說,就是要求“從感性認識提高到理性認識,逐漸區別出某一作家作品的藝術技巧特征,在心目中樹立起‘樣板,以此為以后鑒定此人作品的依據。同時,還要在以后的實踐中加以檢驗、修正和充實對這一作家作品的認識。”《概論》是以“目鑒”作為鑒別古書畫的“要領”提出的,而多看,正是“目鑒”的基礎。
《概論》的科學性,還表現在評騭、辨別作品優劣、真偽的方法上。評騭、辨別作品的優劣、真偽,究竟應該堅持怎樣的方法,這在書中“總論”里也已道及。它說:“一般的講,那些高手作的書畫,其藝術手法、筆墨技巧的確高人一籌,作偽者是不易摹學和達到的。但是,有些書畫家生活年代較長,而作品的藝術技能和水平是發展的,因此,從藝術技巧優劣的角度上來斷真偽,就必須將某一書畫家的作品按其發展情況,分別定出幾個標準,而不能籠統地死守一種標準來衡量。否則,容易把不成熟的早期作品看成贗品。”又說,“還有一些本來是藝術上的高手,因為偶然的原因,遇到不利的客觀條件,如紙筆工具不好,或下筆時精神疲乏、興趣欠濃等等,就不能保持原有的水平;……碰到這樣的作品時,我們必須小心謹慎地從各方面去觀察研究,弄清原因,作出正確的判斷”。從上面引錄的兩段話里,不難了解《概論》在品鑒書畫優劣、辨別真偽中堅持的方法,是進行歷史的、具體的分析。鑒定書畫應該把這樣的精神貫徹到實際工作中去,審慎地加以判斷。這樣的方法,正是構成鑒別書畫“要領”的另一重要內容。
《概論》一書比較系統地講述了我國歷史上主要書畫家的作品、流派以及書體的變革與發展,而且還較廣泛地接觸到我國書法、繪畫中的某些問題。雖然大都是作為一種現象提出的,帶有一定的提示性質,但可以使我們獲得知識、受到啟發,從而加深對這些問題的認識,以便進行深入的研究。下面試舉幾個例子來看:
書中在論及草書的歷代發展狀況時,指出:“隋至初唐的草書,大都不離東晉二王一派。盛中唐張旭、懷素稍涉連綿流暢,但不致險怪。晚唐、五代、北宋初,有一些人在張旭、懷素的基礎上,變出奇險狂怪的風格來,后人不察,往往把旭、素與他們混為一談,那是大大的錯誤了。”
張旭、懷素的草書風范,一般多與后世的狂草混同,今《概論》提出應該加以區別,這是很對的。著者雖未說明他自己用以區別的根據,但我們只要就《苦筍帖》、《草書自敘》作一番研究,并結合前人的評論,便可發現旭、素草書與后來草書的基本差異在于意境。米芾評張旭“字法勁古”,評懷素的字為“古澹”,這顯然是就書法的意境而言的。再看筆意、特征,劉熙載則稱“張長史得之古鐘鼎銘、蝌蚪篆”。從用筆圓轉,全以“氣”勝的特征來看,的確有篆書的意趣。這和后世的草書一味追求四面開張,以荒率為醇厚的那種狂而險怪,則全不相類。
在草書的發展中,由于歷史條件的不同,以及師承、藝術旨趣等原因,各代呈現出不同的面貌。《概論》著者在講述宋代草書發展面貌時說:“宋人一般擅長行書,草法少有發展。”宋人長于行書,究其原因,大概因為宋人學書多以顏真卿、楊凝式兩家為依歸,雖然也參以二王,但是受顏的影響更深。
明代盛行狂草,這是一個比較突出的現象。《概論》說:“明代早、中期狂縱的草書體又大大地流行起來,……晚明、清初還有傅山等人。晚明又有一種參以古草的古今體寫法的草字,代表作家有黃道周、倪元璐等人。”
明代早、中期,特別是中期以后,因受處于萌發狀態的新的經濟因素的影響,在文學、藝術上都呈現出一種與以往不同的面貌,較突出的反映,就是追求個性發展。表現在書法上(包括繪畫)的狂放恣肆,正是一種追求個性抒發的反映,徐渭、陳淳即是突出的代表。明末清初盛行狂草,其原因與明代中葉又有所不同,似乎更為復雜。既有反對那種趨于僵化的書風的因素(包括一部分人提倡寫碑在內),又交織著民族意識;如黃道周、傅山等人都是晚明志節之士,特別是傅山。“書如其人”,不是全無道理。書品、書風,除修養、工力之外,往往也為思想、性格、氣質、情操所決定。就書法本身而言,固然是表達文字的工具,但它完全可以通過書家所賦予的特定的內涵,來表達書家自己的感情,寄托某種思想、意念。而且這種狂放的草書更易于抒泄感情。《概論》對此盡管是作為一種現象提出的,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明代中晚期以至清初在書法藝術上表現的時代特征。
象這樣的書畫發展的歷史知識越豐富,于書畫鑒定越有助益。
如何掌握評騭書畫的優劣標準,不但對鑒別是重要的,就是對通常的書畫欣賞也是重要的。然而評定作品的優劣,卻是一個不大容易說清楚的問題。關于評定書畫的優劣,作者主要是根據通常對“工”與“拙”的看法來談的。他指出,一般評定繪畫作品,多以刻畫工細、逼肖為優,“生拙”為劣;對書法,則以“四平八穩”為優。認為衡量書畫優劣,不能以形象是否逼肖、字型是否平穩論工拙。因為繪畫中技法的純熟,也可以導致“油滑”和“庸俗可厭”;書法的“平穩”只不過是一種“起碼的條件”。作者以中國的“文人畫”為例,說明那些歷史上的文人畫家“往往追求生拙之趣,而不以工能見長”。書法中也有如此情況。《概論》不是一種藝術史論,不可能就這些問題作深入的討論,只能把“工與拙”作為鑒賞中的一例,說明“工”不一定就好,“拙”也不一定就壞,都應作具體分析。
總之,《概論》涉及到書畫史和美學上的一些饒有興味的問題,所以它不只是對古書畫研究者交流經驗,對藝術愛好者也很有啟發。
(《古書畫鑒定概論》,徐邦達著,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五月第一版,3.80元)
施闌
讀《古書畫鑒定概論》
在中國,書畫作偽的歷史,大概也不算太短。但究竟發軔于何時,還不曾確考,僅據現有的資料看,至少在唐代就有了。晚唐畫家程修己墓志中,記有他偽制王羲之書帖的事:“……丞相衛國公聞有客藏右軍書帖三幅,衛國公購以千金,因持以示公(即程),公曰:‘此修己紿彼而為,非真也。”這是唐時書畫作偽的一個實例。再據米芾《畫史》所記,則有:“李成真見兩本,偽見三百本。”米氏是書畫博士,他見到的北宋內府收藏的李成畫跡,贗品竟多至三百幅。照米氏的說法,這些假畫,“皆俗于假名”。其實,高手也同樣“假名”,米芾自己就是一個作偽的專家。不過早期作偽大都出于游戲,顯示作偽者技藝高超,足以亂真。
既有偽跡,必然要有識辨偽跡的方法。但前人卻沒有把這方面的經驗整理成篇,即或有,也只是一些書畫史和公私書畫著錄,真正把鑒別書畫的經驗系統地寫成專書,則是新中國誕生以后才有的。徐邦達先生的《古書畫鑒定概論》正是這樣一種專門的著述。
鑒定,對于歷史文物,尤其是對那些時移世隔的古書畫,無疑是重要的,因為只有經過必要的鑒定,才便于收集、整理、保護、研究,有裨于今用。
古代書畫大都是傳世品,比起鑒別其他文物,要復雜得多。有些書畫即使前人有過著錄,但也相當簡略;加之可以憑借的資料又少,要想有效的辨偽存真、考定年代,只有靠多年積累的經驗。《概論》一書的著者正是以他從事這項工作的實際經驗,就書畫鑒定中的各種問題、有關的知識,分章講述,舉重若輕;把一些比較錯綜的問題、現象,聯系產生這些現象、問題的歷史條件和原因,作了扼要的說明。
《概論》一書特別注重科學性。它反復強調了大量親身接觸古書畫實物對鑒定書畫的意義,并把這一觀點貫串全書。一般人常常把古書畫的鑒定看得很神秘,有的甚至認為古書畫的鑒定沒有什么科學性,可以信口胡謅。這當然是誤解。實際上鑒定古書畫并不神秘,它依靠的就是——多看。這個道理既復雜又簡單。對一個作家的作品看得多了,他的作品的筆法、氣韻、風格爛熟于胸中,作品展開,就能真偽立見。這猶如見到老朋友,無須端詳、思索就可認出。用著者的話說,就是要求“從感性認識提高到理性認識,逐漸區別出某一作家作品的藝術技巧特征,在心目中樹立起‘樣板,以此為以后鑒定此人作品的依據。同時,還要在以后的實踐中加以檢驗、修正和充實對這一作家作品的認識。”《概論》是以“目鑒”作為鑒別古書畫的“要領”提出的,而多看,正是“目鑒”的基礎。
《概論》的科學性,還表現在評騭、辨別作品優劣、真偽的方法上。評騭、辨別作品的優劣、真偽,究竟應該堅持怎樣的方法,這在書中“總論”里也已道及。它說:“一般的講,那些高手作的書畫,其藝術手法、筆墨技巧的確高人一籌,作偽者是不易摹學和達到的。但是,有些書畫家生活年代較長,而作品的藝術技能和水平是發展的,因此,從藝術技巧優劣的角度上來斷真偽,就必須將某一書畫家的作品按其發展情況,分別定出幾個標準,而不能籠統地死守一種標準來衡量。否則,容易把不成熟的早期作品看成贗品。”又說,“還有一些本來是藝術上的高手,因為偶然的原因,遇到不利的客觀條件,如紙筆工具不好,或下筆時精神疲乏、興趣欠濃等等,就不能保持原有的水平;……碰到這樣的作品時,我們必須小心謹慎地從各方面去觀察研究,弄清原因,作出正確的判斷”。從上面引錄的兩段話里,不難了解《概論》在品鑒書畫優劣、辨別真偽中堅持的方法,是進行歷史的、具體的分析。鑒定書畫應該把這樣的精神貫徹到實際工作中去,審慎地加以判斷。這樣的方法,正是構成鑒別書畫“要領”的另一重要內容。
《概論》一書比較系統地講述了我國歷史上主要書畫家的作品、流派以及書體的變革與發展,而且還較廣泛地接觸到我國書法、繪畫中的某些問題。雖然大都是作為一種現象提出的,帶有一定的提示性質,但可以使我們獲得知識、受到啟發,從而加深對這些問題的認識,以便進行深入的研究。下面試舉幾個例子來看:
書中在論及草書的歷代發展狀況時,指出:“隋至初唐的草書,大都不離東晉二王一派。盛中唐張旭、懷素稍涉連綿流暢,但不致險怪。晚唐、五代、北宋初,有一些人在張旭、懷素的基礎上,變出奇險狂怪的風格來,后人不察,往往把旭、素與他們混為一談,那是大大的錯誤了。”
張旭、懷素的草書風范,一般多與后世的狂草混同,今《概論》提出應該加以區別,這是很對的。著者雖未說明他自己用以區別的根據,但我們只要就《苦筍帖》、《草書自敘》作一番研究,并結合前人的評論,便可發現旭、素草書與后來草書的基本差異在于意境。米芾評張旭“字法勁古”,評懷素的字為“古澹”,這顯然是就書法的意境而言的。再看筆意、特征,劉熙載則稱“張長史得之古鐘鼎銘、蝌蚪篆”。從用筆圓轉,全以“氣”勝的特征來看,的確有篆書的意趣。這和后世的草書一味追求四面開張,以荒率為醇厚的那種狂而險怪,則全不相類。
在草書的發展中,由于歷史條件的不同,以及師承、藝術旨趣等原因,各代呈現出不同的面貌。《概論》著者在講述宋代草書發展面貌時說:“宋人一般擅長行書,草法少有發展。”宋人長于行書,究其原因,大概因為宋人學書多以顏真卿、楊凝式兩家為依歸,雖然也參以二王,但是受顏的影響更深。
明代盛行狂草,這是一個比較突出的現象。《概論》說:“明代早、中期狂縱的草書體又大大地流行起來,……晚明、清初還有傅山等人。晚明又有一種參以古草的古今體寫法的草字,代表作家有黃道周、倪元璐等人。”
明代早、中期,特別是中期以后,因受處于萌發狀態的新的經濟因素的影響,在文學、藝術上都呈現出一種與以往不同的面貌,較突出的反映,就是追求個性發展。表現在書法上(包括繪畫)的狂放恣肆,正是一種追求個性抒發的反映,徐渭、陳淳即是突出的代表。明末清初盛行狂草,其原因與明代中葉又有所不同,似乎更為復雜。既有反對那種趨于僵化的書風的因素(包括一部分人提倡寫碑在內),又交織著民族意識;如黃道周、傅山等人都是晚明志節之士,特別是傅山。“書如其人”,不是全無道理。書品、書風,除修養、工力之外,往往也為思想、性格、氣質、情操所決定。就書法本身而言,固然是表達文字的工具,但它完全可以通過書家所賦予的特定的內涵,來表達書家自己的感情,寄托某種思想、意念。而且這種狂放的草書更易于抒泄感情。《概論》對此盡管是作為一種現象提出的,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明代中晚期以至清初在書法藝術上表現的時代特征。
象這樣的書畫發展的歷史知識越豐富,于書畫鑒定越有助益。
如何掌握評騭書畫的優劣標準,不但對鑒別是重要的,就是對通常的書畫欣賞也是重要的。然而評定作品的優劣,卻是一個不大容易說清楚的問題。關于評定書畫的優劣,作者主要是根據通常對“工”與“拙”的看法來談的。他指出,一般評定繪畫作品,多以刻畫工細、逼肖為優,“生拙”為劣;對書法,則以“四平八穩”為優。認為衡量書畫優劣,不能以形象是否逼肖、字型是否平穩論工拙。因為繪畫中技法的純熟,也可以導致“油滑”和“庸俗可厭”;書法的“平穩”只不過是一種“起碼的條件”。作者以中國的“文人畫”為例,說明那些歷史上的文人畫家“往往追求生拙之趣,而不以工能見長”。書法中也有如此情況。《概論》不是一種藝術史論,不可能就這些問題作深入的討論,只能把“工與拙”作為鑒賞中的一例,說明“工”不一定就好,“拙”也不一定就壞,都應作具體分析。
總之,《概論》涉及到書畫史和美學上的一些饒有興味的問題,所以它不只是對古書畫研究者交流經驗,對藝術愛好者也很有啟發。
(《古書畫鑒定概論》,徐邦達著,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五月第一版,3.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