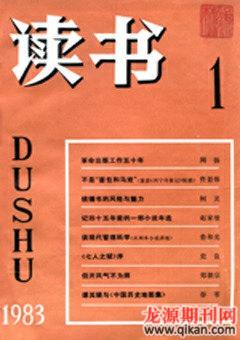鄧之誠(chéng)先生買(mǎi)書(shū)
雷夢(mèng)水 葉祖孚
抗戰(zhàn)勝利以后,我在琉璃廠通學(xué)齋古書(shū)店工作。那時(shí)我經(jīng)常挾書(shū)到燕京大學(xué)去求售,認(rèn)識(shí)了鄧之誠(chéng)先生。鄧先生住在燕京大學(xué)東門(mén)外蔣家胡同路北二號(hào),進(jìn)門(mén)穿過(guò)屏門(mén)可以看到他居住的寬敞的北房。這幾間北房既是鄧先生的書(shū)齋,也是他的會(huì)客室和教室。鄧先生教書(shū)有個(gè)特點(diǎn),往往開(kāi)學(xué)之初,他挾著書(shū)到燕京大學(xué)穆樓教室上一兩節(jié)課,然后就是學(xué)生到他的書(shū)齋來(lái)上課了,書(shū)齋中間有張大案桌,大家圍著桌子聽(tīng)鄧先生講課,顯得既親切又諧調(diào)。書(shū)齋的墻上掛著一些照片,還有清初著名學(xué)者顧亭林先生的畫(huà)像,像的四周密密麻麻地寫(xiě)滿了清代諸名家的題跋。鄧先生尊敬顧亭林先生,國(guó)難時(shí)期,這幅畫(huà)像可以表明鄧先生的民族氣節(jié)和愛(ài)國(guó)熱情。鄧先生也注意搜集關(guān)于顧亭林著述的不同版本,幾乎搜羅殆盡。我曾為先生尋覓到清徐嘉《顧詩(shī)箋注》以及光緒年間幽光閣戴子高家藏潘次耕手鈔鉛印本,與其他版本不同,還搜集到乾隆年間孔氏玉虹樓校刊本《菰中隨筆》等名貴書(shū)籍。先生很高興。一日先生忽然告訴我顧亭林《日知錄》初刻八卷本刻于清康熙九年,版本極稀,從前繆筱珊先生藏有一部,后歸傅增湘先生,他曾屢次借閱而不得,引為憾事,他囑我為他搜羅此本,可惜我一直沒(méi)有搜集到。
因?yàn)榻?jīng)常為先生送書(shū),我比較了解先生的需求,能夠主動(dòng)滿足他在學(xué)術(shù)研究方面的要求。例如“七·七”事變以后,先生用幾年的時(shí)間收藏了七百多種清初人集部,作為他研究明末清初歷史的資料,其中我為先生搜集到的就不少,比較罕見(jiàn)的如:孔東塘《湖海集》、王鳴盛《西
先生還藏有一部傳世極罕的筆記書(shū)《土風(fēng)錄》,清張思撰,刻于嘉慶年間,唯缺首冊(cè),他曾囑我留意為他配齊。數(shù)年后通學(xué)齋收到一批書(shū),發(fā)現(xiàn)其中正好有這本。次日,我就騎車(chē)到成府為先生送書(shū)。先生一見(jiàn)我,就用慣有的那種帶著四川口音的口氣說(shuō):
“夢(mèng)水,你今天又為我送什么好書(shū)來(lái)啦?”
我隨即回答說(shuō):
“鄧先生,我為您配上那部《土風(fēng)錄》的首冊(cè)了。”
這真是喜出望外,他高興地捧著那本書(shū)來(lái)回翻閱,大加贊賞。象這樣事有過(guò)好幾次。
先生除了喜歡收藏古書(shū),還喜歡收藏清末民初的人像、有關(guān)風(fēng)俗以及中外名勝古跡的照片,其中人像和風(fēng)俗方面的照片,為研究民俗學(xué)提供了重要珍貴資料。他談起購(gòu)照片的事,總說(shuō)這些東西大部份是宣武門(mén)內(nèi)小市上辛大個(gè)為他送來(lái)的,這個(gè)辛大個(gè)就是蔚珍堂主人辛金凱,字叔堅(jiān),河北冀縣人,是我的同鄉(xiāng)。
我為鄧先生買(mǎi)書(shū)的過(guò)程,也是我向先生學(xué)習(xí)的極好機(jī)會(huì)。
因?yàn)橄壬鷮?duì)明末清初的歷史有深刻的研究,每當(dāng)我覓到明末清初人集子時(shí)就向先生請(qǐng)教,先生也樂(lè)為講述,諄諄無(wú)倦容。例如我為先生送去清朱彝尊的《騰笑集》,先生就告訴我此集大部分是朱氏重要的作品,為《曝書(shū)亭集》所未收,刻工甚佳,傳本亦稀,誠(chéng)為可貴。對(duì)于清孫枝蔚的《溉堂集》,先生告訴我它分前、續(xù)、文、詩(shī)余、后五部分,唯后集系作者歿后刻的,傳本尤為罕見(jiàn)。關(guān)于清陸隴其所著的《三魚(yú)堂文集》以康熙間嘉會(huì)堂原刊初印本為最善,后印者因?yàn)槲淖知z的關(guān)系已經(jīng)刪掉《答呂無(wú)黨》、《與呂無(wú)黨及附答》、《祭呂晚村先生文》等篇,是不完整的。先生還告訴我清王鴻緒《橫云山人集》康熙間早印本印二十六卷,附一卷;后印本則改印為二十七卷了,等等。這些知識(shí)都是我聞所未聞的,先生的教誨使我在版本目錄學(xué)方面受到很大教益。
因?yàn)榕c先生長(zhǎng)期來(lái)往,先生認(rèn)為我誠(chéng)實(shí)可靠,對(duì)我倍加信任。有時(shí)委托我從城內(nèi)替他買(mǎi)些東西,如到廊房頭條步云齋鞋店去替他購(gòu)雙皮臉鞋及疙疸帽墊等。有時(shí)也委托我與張孟劬、崇彝、李根源、陳慶和諸位老先生借還書(shū)籍或代交信件。每當(dāng)我到先生寓所送書(shū),先生總是親切地叫家人為我沏茶。有時(shí)我趕到那兒正好中午,先生飯后要休息了,他就從箱內(nèi)找出幾冊(cè)稀有的書(shū)籍叫我看,有一次還親自把手書(shū)的長(zhǎng)條本日記搬來(lái)叫我看。先生的日記本長(zhǎng)盈尺,用蠅頭小楷寫(xiě)成,筆法遒勁,他在日記里提到我時(shí)親切地叫我“書(shū)友”,對(duì)其他書(shū)店同輩則叫“書(shū)賈”,這是對(duì)我極大的鼓勵(lì)。我是一個(gè)普通的書(shū)店職員,能夠熱愛(ài)古舊書(shū)籍工作,并且終身從事這項(xiàng)工作,這與鄧之誠(chéng)先生等前輩的親切教導(dǎo)是分不開(kāi)的。
一九四一年末太平洋戰(zhàn)爭(zhēng)爆發(fā)后,鄧先生及洪煨蓮先生等被日本憲兵隊(duì)逮捕入獄,半年以后獲釋。先生在獄中曾寫(xiě)詩(shī)若干首,表明他對(duì)日寇的憎恨和崇高的民族氣節(jié)。先生將這些詩(shī)于一九四六年編印《閉關(guān)吟》一卷,聽(tīng)先生說(shuō),此書(shū)只印百冊(cè),贈(zèng)送朋友留念。先生贈(zèng)我一冊(cè),也毀于十年動(dòng)亂,令人痛惜。
先生的字寫(xiě)得極好,他曾手寫(xiě)同鄉(xiāng)《汪悔翁先生詩(shī)續(xù)鈔》一冊(cè),影印問(wèn)世。我去送書(shū)時(shí),常見(jiàn)他為朋友寫(xiě)字,我也有意敬求墨金,只是不敢啟口。先生的二弟之綱先生看出我的心意,就主動(dòng)對(duì)我說(shuō):“大爺愿意為你寫(xiě)點(diǎn)字,你拿張紙來(lái)吧!”
就這樣,我請(qǐng)先生寫(xiě)過(guò)中堂、對(duì)聯(lián)、扇面等幾件字跡,大部份毀于十年動(dòng)亂,只有一九四七年(丁亥)先生為我書(shū)寫(xiě)的扇面,因藏于箱底,幸存下來(lái)。扇面寫(xiě)的是黃癭瓢詩(shī),字跡秀麗工整(見(jiàn)本文前圖版)。現(xiàn)在打開(kāi)扇面,猶如見(jiàn)到先生。
先生亦善治印,先生的名章(“鄧之誠(chéng)文如”、
先生身材魁梧,身穿常服,短發(fā)蒼白,上唇留著一髭花白短須,雙目炯炯,令人感到有點(diǎn)威嚴(yán),但和他接觸之后,卻又感到和藹可親。先生的弟弟之綱先生說(shuō),之誠(chéng)大哥自幼聰敏過(guò)人,讀書(shū)過(guò)目不忘,有神童之稱,至老不衰,所以在歷史教學(xué)方面能獲得卓越的成績(jī)。
鄧之誠(chéng)先生,字文如,江蘇江寧人,清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年)生于四川,民國(guó)初年至北京。歷任國(guó)史編纂處編纂員、國(guó)立北京大學(xué)史學(xué)系教授、燕京大學(xué)教授。一九六○年病卒,享年七十三歲,著有《中華二千年史》、《明清史》、《骨董瑣記全編》、《桑園讀書(shū)記》、《清詩(shī)紀(jì)事初編》、《東京夢(mèng)華錄注》、《護(hù)國(guó)軍紀(jì)實(shí)》、《閉關(guān)吟》等書(shū)籍。東莞?jìng)愓苋缦壬缎梁ヒ詠?lái)藏書(shū)紀(jì)事詩(shī)》稱贊鄧之誠(chéng)先生:“翳君便是老骨董,瑣記何時(shí)又續(xù)成,此外當(dāng)編今世說(shuō),笑嬉怒罵總文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