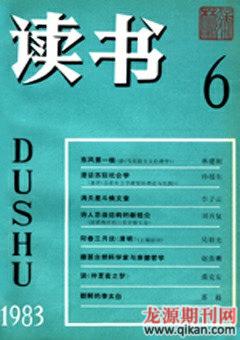一百多年來的勃朗特姐妹研究
楊靜遠
在英國文學史上,勃朗特三姐妹是一個奇特的現象。她們既作為璀燦的星座而閃耀,又作為單獨的巨星而發光,至少就夏洛蒂和艾米莉來說是如此。經過一百多年時間的考驗,《簡·愛》和《呼嘯山莊》已經在世界文學寶庫中占據了不可動搖的地位,而安妮作為三星有機體的一員,也被帶進了不朽者的行列。
三姐妹發表的成熟作品只有七部小說,一本詩集。七部小說中,夏洛蒂占四部:《簡·愛》、《雪莉》(中譯本名《謝利》)、《維萊特》、《教師》。艾米莉只有一部:《呼嘯山莊》。安妮則有兩部:《艾格妮斯·格雷》和《懷爾德菲爾府的房客》。數量雖不多,成就卻很可觀。這些作品,以深刻的思想內容和獨特的藝術魅力,吸引了世世代代的文學愛好者。她們同時代不少更顯赫更多產的作家早已湮沒無聞,而她們卻迄今傳誦不衰。自三姐妹署名“貝爾”的三部小說于一八四七年秋冬出版以來,直到今天,評論和研究她們作品的文章和書籍數以千計,同她們的寥寥數本作品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這些論著不但數量龐大,而且觀點紛繁。“貝爾”們的作品的誕生,絕不是風平浪靜的。《簡·愛》剛一問世,就遇到評論界截然相反的反應:一方面是熱烈的歡迎和贊譽,另一方面是惡意的詆毀和中傷。絕大多數評論對它評價很高,公正地指出了它在思想和藝術方面的“深刻”、“真實”、“新穎”、“獨創”、“有力”、“感人”,肯定了作者卓越的才華,雖然也指出了寫作技巧上的不夠成熟、情節的不大可能、感情上的夸張等缺陷。但有極少數評論(如伊麗莎白·里格比和《基督教醒世報》上的評論)嗅出了這顆橫掃世俗陳腐觀念的彗星對現存秩序的危險性,不遺余力地對它肆意詆毀,斥之為“粗野”、“叛逆”、“反基督教”、“道德上的雅各賓主義”,甚至進行人身攻擊。他們人數雖少,但代表了某些權勢階層,因而影響頗大。但是,無畏的夏洛蒂·勃朗特并未屈服。她在同出版者和一些評論者的通信中,義正詞嚴地申述自己的立場,并在《簡·愛》再版序中公開作答。她得到廣大讀者和大多數評論者的支持,而反動階層和教會頑固勢力的代言人對《簡·愛》的責難,恰恰從反面證明了這本書的進步意義。
艾米莉和安妮的遭遇卻很不相同。《呼嘯山莊》出版后,遇到的是普遍的冷淡和少數幾篇評論的嚴厲貶抑。這本小說中桀驁不馴的人物性格,異乎尋常的強烈的愛、恨和復仇意識,為時人所難容,被指摘為陰森可怖、病態心理、不道德和異教思想。這使得生性內向的艾米莉陷入更深的沉默,竟至郁郁以終。她死后兩年,才出現了錫德尼·多貝爾那篇高度贊揚《呼嘯山莊》的文章《柯勒·貝爾》。安妮被認為是三姐妹中才氣較平的一個,她的《艾格妮斯·格雷》只受到有禮貌的接待,第二部小說《懷爾德菲爾府的房客》雖獲暢銷,卻因它如實地描繪了酗酒放蕩的危害,受到猛烈抨擊,被斥為感情不健康,低級趣味,題材不是婦女所應涉及的,等等。安妮悲憤之余,寫了該書再版序,痛斥評論界對男女作家采用兩種標準的不平等待遇。
夏洛蒂的第二部小說《雪莉》,走出了描寫個人的激情和內心生活的狹窄圈子,試圖轉向廣闊的社會畫面,處理工人運動和勞資沖突的重大題材。這是她在創作道路上的一個重要發展,但這一點并未受到應有的重視。評論界因這本小說在藝術上有缺點而表示失望。第三部小說《維萊特》則因回到寫個人內心生活的題材,受到普遍歡迎,被譽為夏洛蒂最成熟的作品。這個時期的評論較初期深入一步,對作品的思想和藝術進行綜合的分析。正是在這個時候,卡爾·馬克思毫不猶豫地把夏洛蒂·勃朗特同狄更斯、蓋斯凱爾夫人和薩克雷并列,稱為“當代杰出的英國小說家”。喬·亨·劉易斯,一位具有洞察力的作家,最早看出夏洛蒂作品的真正價值在于其現實主義的因素。《普特南月刊》繼而指出了她小說中的現實性和民主性(寫普通人)兩大特色。女作家瑪格麗特·奧利方特歡呼夏洛蒂在婦女問題上先進的平等解放思想。具有激進思想的青年作家錫德尼·多貝爾則發現她在老派的外衣下面表現出“光榮的異端思想”,稱贊她用想象力豐富和發展了歷史。另方面,由于夏洛蒂的三本小說都包含著批判宗教偽善和精神桎梏的激進內容,激怒了宗教界權威人士,再次招致《基督教醒世報》的抨擊。
一八五五年夏洛蒂的逝世,一八五七年蓋斯凱爾夫人揭示三位女作家凄涼身世和卓絕才華的《夏洛蒂·勃朗特傳》的出版,掀起了勃朗特姐妹評論和研究的新高潮,并使之帶上了作家研究中罕見的個人悼念的感情色彩。評論者們已不限于就書論書,而是結合三位作家的生平和背景,進行全面的考察。一八七七年夏洛蒂第二本傳記(威姆斯·里德著)、一八八三年艾米莉第一本傳記(瑪麗·羅賓森著)的出版,標志著勃朗特評論的新階段。英國著名詩人史文朋的《簡論夏洛蒂·勃朗特》(1877)和《艾米莉·勃朗特》(1883)兩篇著名文章,對兩位女作家作了極高的評價。他把有才氣的作家分為第一流的“天才”作家和次一等的“才智”作家兩類,認為夏洛蒂·勃朗特堪稱“天才”作家,而當時聲譽已躍居夏洛蒂之上的喬治·艾略特只是“才智”作家。他把《呼嘯山莊》同《李爾王》對比,稱頌艾米莉為“悲劇天才”。他還比較了姐妹二人的藝術,認為二者的區別是:姐姐所有的作品都富有詩意,而妹妹的作品本身就是一首詩。從他開始,此后數十年中勃朗特評論的特點是,艾米莉的聲譽蒸蒸日上,而夏洛蒂的光輝卻相對地顯得有點黯淡。
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博學的女作家瑪麗·沃德對勃朗特姐妹的文學成就作了五十年歷程的回顧。她第一個從民族傳統、文學淵源和比較文學的角度,系統地分析了她們的創作特點,指出夏洛蒂作品的特征是凱爾特民族性格、英格蘭民族精神與法國浪漫主義因素(特別是喬治·桑和雨果的影響)的結合,而艾米莉則是同樣的素質與德國浪漫主義因素(特別是霍夫曼的影響)的結合。但她斷言夏洛蒂不是一個社會叛逆者,這個論點卻未必中肯。夏洛蒂滿懷激情地向不合理的社會現象和陳規陋俗挑戰,不論在對社會、宗教、婦女和愛情婚姻問題或文學藝術問題的態度上,都表現出鮮明的叛逆精神,雖則這種叛逆精神受到時代和社會以及她本人的出身、教養、環境等方面的局限,時常處于矛盾沖突的狀態。
二十世紀以來,評論界對夏洛蒂和艾米莉厚此薄彼的態度尤其明顯。一些評論者對夏洛蒂那較為淺顯的社會批判和思想內容不感興趣或不合口味,而對《呼嘯山莊》那謎一般的耐人尋味的思想內涵和表現形式則興味無窮,涌現了形形色色的“索隱”,形成了“艾米莉熱”或“《呼嘯山莊》學”的潮流,到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才開始逆轉,對夏洛蒂的興趣重新抬頭,出現了一些有價值的評論和傳記作品。
二十世紀的一些評論者,繼續從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巧妙結合來剖析夏洛蒂創作的特色。吉·凱·切斯特頓認為,她的巨大的貢獻在于通過最低的現實主義(寫中下層人的生活),達到最高的浪漫主義。凱思琳·蒂洛森詳盡地追溯了夏洛蒂的創作道路,聯系她的家庭和身世的背景探索她從幻想到現實主義的發展過程。哈麗特·比約克從夏洛蒂的書信和作品中分析,她平行地提出了婦女問題和工人問題,她的女性的抗議同對藝術上的陳腐積習的叛逆精神相交織。帕特里莎·湯姆森聯系喬治·桑和法國浪漫主義運動的影響,探討了夏洛蒂在婦女及婚姻問題上力圖掙脫封建桎梏和清教意識束縛的解放思想。羅伯特·海爾曼從夏洛蒂小說中的哥特因素,探討她把舊哥特體改造成“新”哥特體的超現實主義創作手法。戴維·洛奇認為,她通過塵世原素(火、氣、水、土)的意象,把日常生活的世界和神話世界,社會生活的現實世界和自我意識的浪漫主義世界融為一體。蘇聯的研究者則重視她的作品的批判現實主義性質和意義。另一些評論者強調夏洛蒂小說中的主觀主義因素。弗吉妮亞·伍爾夫認為她和哈代一樣是一個主觀主義作家,把她的創作主旨歸納為一個公式:“我愛,我恨,我痛苦。”勃朗特評論中影響頗大的戴維·塞西爾認為,她是第一個主觀主義小說家,是普魯斯特、詹姆斯·喬哀斯等個人意識小說家的鼻祖。他說,正如薩克雷在英國作家中第一個把小說當作有意識地批評生活的工具,夏·勃朗特則第一個把小說當作披露個人情懷的工具。他歷數了她創作上的缺點(有些批評顯然是過火的)后,認為她的成就和魅力只在于她獨特的個性、強烈的激情和豐富的想象力,她所創造的世界僅僅是她內心生活的世界。但他沒有看到,夏洛蒂的靈魂是現實主義的;盡管她偏重寫內心生活和個人激情,其中卻明確地反映了現實的社會思想,根本不同于那些遠離現實生活、專寫“純”心理的“主觀主義”作家。還有一些評論者,從弗洛依德的性心理分析出發,對她的創作動機和作品涵義進行解釋。著名小說家薩默塞特·毛姆認為,勃朗特姐妹創作的動機是為滿足受壓抑的性饑渴。他在夏洛蒂的作品中看到赤裸裸的色欲。七十年代有些研究者進而把夏洛蒂的心理根源解釋為對早亡的母親的負罪感和戀父情結(羅伯特·基夫:《夏洛蒂·勃朗特的死亡世界》),甚至把夏洛蒂對弟弟的感情視為“心靈上的亂倫沖動”(海倫·莫格倫:《夏洛蒂·勃朗特:自我表現》)。
對艾米莉和《呼嘯山莊》的各種“新”解釋更是層出不窮。有的說,艾米莉是個神秘主義者,小說中男女主人公的愛情不是人間的愛,作者的經驗是靈的經驗(梅·辛克萊;莫里斯·梅特林克;戴維·塞西爾);有的說,《呼嘯山莊》的主題是“不道德的主題上升到道德的光輝境界”(馬克·肖勒)。有的說,《呼嘯山莊》是作者童年夢境的繼續(瑪格麗特·萊恩)。關于《呼嘯山莊》有無社會意義的問題,存在著壁壘分明的分歧意見。馬丁·特奈爾認為它是一本社會小說,表現了兩種不同的生活方式的沖突,是對近代文明的控訴。阿諾德·凱特爾從階級斗爭觀點出發,認為凱瑟琳和希思克利夫的感情的基礎是受壓迫者的階級感情,她嫁給林頓是對希思克利夫的背叛,希思克利夫的復仇則是以壓迫者的手段還報壓迫者。與此相反,戴維·塞西爾認為《呼嘯山莊》不是一本社會小說,它是艾米莉的自然哲學的象征性表露,其中的沖突不是人間善惡是非的沖突,而是宇宙間“風暴與寧靜”兩種力量的沖突。多蘿西·凡·根特認為,《呼嘯山莊》與人類社會倫理觀念毫不相干,它表現了一種泛靈論的觀念。喬治·英什則認為,《呼嘯山莊》的意義在于人同大自然——荒原——的斗爭。弗洛依德學說應用在艾米莉身上也同樣離奇。薩默塞特·毛姆認為,艾米莉創造了一對狂暴地相戀的男女主人公,是受淫虐狂的驅使,而她一生最大的精神創傷則可能是一次遭到拒絕的同性戀。還有人解釋說,《呼嘯山莊》暗示了亂倫的沖動和禁忌,因為凱瑟琳和希思克利夫很可能是同父異母兄妹。這就近乎穿鑿附會的猜謎游戲了。有的評論則流于煩瑣考證,例如,被譽為艾米莉評論的一個里程碑而多次重印的C·P·桑格的《<呼嘯山莊>的結構》一文,對故事中各個事件發生的準確時間和地點進行推算,排出時間表,并用當時的法律來說明兩個家族的繼承權問題。這顯然已越出文學批評范圍。
總的來說,二十世紀的勃朗特評論脫離了空泛的一般性毀譽,轉入細致具體的分析,從各個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對作品的主旨、藝術技巧、手法和特色進行探討,出現了不少有份量的和富于啟發性的論著。但隨著各種現代批評流派的興起,也出現了一種脫離作家和作品的實際、隨心所欲地進行解釋或臆測的傾向,以及一種離開思想性與藝術性的有機聯系而孤立地談論藝術或純技巧的形式主義傾向。
對三姐妹的生平和創作進行全面深入的研究而做出重大貢獻的,要數英國勃朗特學家溫妮弗萊德·蓋林于六十年代前后出版的四本翔實的傳記。
勃朗特評論和研究論著數量如此龐大,內容如此駁雜,那怕作一簡略的介紹,也非筆者所能企及,更不用說加以述評,以上聊作盲人摸象之舉,以見一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