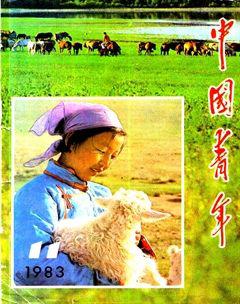中國之鶯
一只夜鶯,翱翔在聲樂藝術的廣闊天穹。她放開婉轉動人的歌喉,以火一般的熱情,唱起一支支雖然語言不同、風格迥異,但在世界音樂寶庫中具有同樣不朽魅力的藝術精品——從世代傳唱的新疆民歌,到西洋古典歌劇的著名詠嘆調。
掌聲、鮮花、握手、請求簽名……不同地區、不同國籍的人,用各種方式表達著對她的祝賀。
迪里拜爾·尤努斯——這就是“夜鶯”的名字。八年前,她還是個沒受過任何專業訓練的維吾爾族姑娘。她的成長就是一支歌:充滿昂揚的音調,奮進的節奏,曲折的情趣……
喀什初鳴
迪里拜爾的家鄉喀什,素稱“歌舞之鄉”,小迪里拜爾吮吸著新疆民間音樂的乳汁長大。她天資聰穎,能歌善舞,對音樂有著敏銳的感受力。她那夜鶯般的歌喉,比哈密瓜更甜美,比葡萄汁更醇厚。從小學三年級起,她在學校宣傳隊里就一直是挑大梁的角色。隨著年齡的增長,迪里拜爾不再滿足于邊歌邊舞了。她開始學手風琴,學獨他爾,從廣播里學唱新歌。沒有老師,全靠自己摸索。天資和勤奮,使她無師自通。不久,她便肩背手風琴,手拿獨他爾,活躍在業余會演的舞臺上。
聰明而刻苦的迪里拜爾,用歌聲送走了童年和少年時代。她的歌唱逐漸脫盡天真與稚氣,變得成熟起來,并且越發動聽了。就在這時,某專業團體來到喀什招收學員。在親友的鼓動下,她帶著美麗的憧憬前去應試。招考老師對她的聲樂才華極表贊賞,但又用十分惋惜的語調說:“迪里拜爾,你的個頭太小……”剛打開一道縫隙的命運之門,砰然一聲,關得更嚴實了。音樂女神仿佛在開玩笑。一次,兩次,三次,同樣的機會,同樣的回答,同樣的結果。迪里拜爾望著穿衣鏡里自己的身影發問:莫非我報考了籃球隊?
1975年,迪里拜爾高中畢業,下鄉接受“再教育”。聽說自治區歌舞團前來招生,迪里拜爾按兵不動。她不想再去聽招考老師惋惜的語調。然而,她卻被歌舞團老師強拉著去唱了幾首歌。她的新疆民歌唱得美極了,老師們不再認為她那身材是個障礙。可是一到政審,爸爸的所謂“重大歷史問題”,又使錄取的希望立時化為泡影。倔強的迪里拜爾經受不住這殘酷的打擊,一回家就撲到床上大哭不止,苦澀的淚水打濕了被單。她沒有想到,素不相識的招考老師,正在為她四處奔波。招生組經過調查證實:所謂“重大歷史問題”,其實是夸大其詞(后來證明是子虛烏有)。為了不讓這樣一個難得的人材被埋沒,招生組打報告給文化局。局領導批示:錄取。
年輕的迪里拜爾終于踏上了專業藝術道路。
烏魯木齊放歌
迪里拜爾來到自治區首府。歌舞團聲樂班名額已滿,她不得不占著樂隊的編制,一邊唱歌,一邊學艾捷克。開朗好學的迪里拜爾,幾乎立刻就愛上了艾捷克,成天躲在琴房里,象著了魔似地演奏它。她渾然不覺,自己正處在藝術生涯的岔路口上,然而郭凌弼老師卻清楚地意識到了。這位忠誠于祖國聲樂藝術的教師,象一個經驗豐富的舵手一樣,幫助迷航的迪里拜爾撥轉了船頭。
一場意義深遠、氣氛嚴肅的談話正在進行。郭凌弼指出迪里拜爾嗓音條件的優越性,詳細分析了她在演唱中的長處與不足,并要她立即放下艾捷克,集全力于歌唱。接著,郭凌弼提出一個大膽的土洋結合的教學方案。教學目標是:通過三年重點培養,使迪里拜爾既能不失風格地演唱新疆民歌,又能自如地演唱難度較高的西洋古典歌曲。
迪里拜爾生來第一次面對如此嚴肅的談話,第一次聽到對自己的聲音條件如此鞭辟入里的分析。雖然她暫時還不能全部理解這一方案的獨創性意義,但它卻喚醒了她內心深處強烈的創造欲望與奮進精神。她只覺得眼前一亮——自己一生應該為之奮斗的目標,竟是這樣清楚,這樣明確!
“這是一項極其艱苦的試驗,隨時都可能失敗。”郭凌弼鄭重地提醒她。
“我能吃苦,不怕失敗。”迪里拜爾堅定地回答。
郭凌弼教學方案立即得到歌舞團領導的批準,并成立了由黨支書親自掛帥的五人小組,專門負責教學計劃的實施。郭凌弼是迪里拜爾的主課老師,為了引導迪里拜爾越過藝術探索道路上的種種障礙,三年中他付出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才華。
迪里拜爾不愧是我們時代藝術探索的猛士。整整三年,她幾乎沒有給自己放過一天假。她慢慢了解到,走土洋結合的道路是我國聲樂界幾代有識之士的共同理想,但由于主客觀條件的限制,我們的教訓多于經驗。這是一項艱難的開拓性工程,每前進一步都需要雙倍的勇氣、智慧和辛勞。一張張日歷上,記載著前進與后退,失敗與成功,喜悅與痛苦,迷惘與徹悟。在這不尋常的一千多個日日夜夜當中,既有暗自垂淚、低聲飲泣,也有雀躍鼓舞、笑語歡歌。在藝術探索的崎嶇小路上,迪里拜爾不畏勞苦并卓有成效地攀登著。
1978年,迪里拜爾以優異成績在學員隊畢業。在自治區文化局和音協為她舉辦的學習匯報獨唱音樂會上,她演唱了新疆民歌、創作歌曲、西洋古典藝術歌曲和歌劇詠嘆調。專家和同行們驚喜地發現:發聲上的一些主要技術難點,迪里拜爾已經順利解決;她的音域整整擴展了一個八度,而音色則更為純凈圓潤;高難度的花腔技巧,她運用得靈活自如;對歌曲的藝術處理細膩完整,感情表達真摯動人。兩結合唱法的試驗,取得了令人振奮的成功!
新疆之鶯羽翼漸豐,應該展翅奮飛了。
奮飛在北京
郭凌弼的眼睛盯著明天。他看到,在迪里拜爾身上蘊藏著巨大的潛力,前途未可限量。新疆有悠久的文化傳統,但畢竟地處邊陲,條件受到局限。三年學習已經告一段落,她應該到更廣闊的天空中去搏擊。
三年合作使兩顆心息息相通,迪里拜爾完全理解老師的苦心。是的,在達到聲樂藝術的光輝頂點之前,決不能停下攀登的步伐。烏魯木齊成果已成過去,新樂章的奮飛主題,應該從北京開始。
就在她振翼待飛的時刻,中央音樂學院沈湘教授來到新疆講學。沈湘是聲樂界很有造詣的前輩,也是郭凌弼的老師。郭凌弼懷著誠摯的敬意,把迪里拜爾托付給自己的老師。他相信,只有經過大手筆,才能把初具規模的半成品,雕塑成晶瑩剔透的完美珍品。沈湘教授深知郭凌弼教學試驗的價值,對迪里拜爾的成績極為珍愛。他欣然從郭凌弼手中接過接力棒,運用自己豐富的教學經驗和淵博的學識,帶領迪里拜爾在兩結合的跑道上繼續向終點沖刺。
在沈湘的直接指導下,迪里拜爾先在中央音樂學院進修了一年。爾后,經歷一番周折,考入歌劇系,繼續在沈湘班上學習。同時,跟隨李晉緯老師學習聲樂。學院系統正規的專業訓練和文化教育,對迪里拜爾來說,既新鮮又繁重。入學第一年的十二門功課,哪一門都要全力以赴才能學好。她克服了難以想象的困難,象來到百花園中的蜜蜂一樣,不知疲倦地采集著知識的花粉,去構筑自己的藝術修養之宮。學年終了,迪里拜爾以驚人的毅力把十二門功課全部拿下來了。沈湘教授按照當初迪里拜爾的計劃,問她還想不想跳級。迪里拜爾誠懇地說:“我各方面的知識都很貧乏,越學越覺得不應該跳級。我來北京為的是學知識學專業,不是為了拿文憑。我要成為歌唱家而不是匠人。自己只有半桶水,我的歌聲又能給人民什么呢?”這番話,正是迪里拜爾理想和性格的真實寫照。
如今,迪里拜爾已讀完了三年級。她作為青年花腔女高音演員,開始出現在國內外的舞臺上。去年,作為中國青年代表團成員,訪問了中東五國。今年,又隨中國音樂家演出團到香港演出。歌聲才落,掌聲四起。她被朋友和同胞們熱情地譽為“中國之鶯”。在贊譽聲中,迪里拜爾十分清醒。她對溢美之詞并無好感,她的眼睛總是盯著明天。
奮飛吧,中國之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