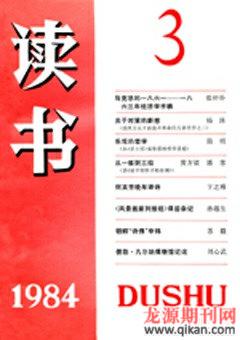《〈資本論〉要略》前記
雪 葦
《資本論》,國際布魯塞爾大會決議里稱之為國際無產階級的“圣經”(一八六八年九月六日——十三日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關于學習《資本論》的決議)。這就是說,《資本論》的思想,是國際工人階級解放斗爭思想指導的理論基礎。列寧說,在《資本論》以前,馬克思主義的學說還是一種假設,雖然是最好的假設;自有了《資本論》,這個學說就不是假設了,是等于經過實驗的科學定理了(參見《列寧選集》,一九七二年版,第一卷,第6—10頁).
《資本論》,首先固然是指導社會主義革命,即如何變革舊社會的書;但是,在一定意義上,也是指導社會主義建設、即如何組織新社會的書。前一道理,大家都明白:它發現了資本主義社會產生、發展、滅亡的規律,并給予十分充分、顛撲不破的論證,從根本上徹底摧毀了資產階級思想家們為資本主義社會所作的一切辯護,而且取得了敵對的思想家們也無法非議的成功,這就給無產階級革命這一整個事業奠定下思想前提。后一道理,跟前者相比,雖然還要闡明,不過,也是容易理解的:由于馬克思這里不僅分析了問題的社會性質,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帶來的內容,而且同時也分析了問題的物質性質,即前者依之為基礎的一般的客觀依據,所以后者便不能不成為組織新社會經濟生活的直接指導。比如一開始(第一卷第一章),作為商品二重性(使用價值和價值)物質內容的勞動二重性的分析,即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的分析,(這也是馬克思的發現。)就是社會主義經濟即計劃經濟的思想出發點。沒有抽象勞動的概念及其實質的規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沒有這一出發點,任何經濟計劃就是不可能的。還有,就是在分析資本主義生產——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的地方,由于社會主義生產——社會主義經濟結構,既是它的革命又是它的繼續這種關系,《資本論》的解剖也對我們建立新社會的經濟體制有直接參考作用。如第二卷分析兩個部類(生產資料的生產和消費資料的生產)比例關系的規律性,第三卷分析貨幣經營資本(“金融”資本)的機制及其運動方式等等,都應作如是觀。社會生產底兩個部類關系的原理,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要絕對遵循的,不能“比例失調”。
《資本論》的意義如此重大,但講到讀《資本論》,我們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讀者和歐洲的馬克思主義讀者卻有不同情況。比如當年俄國,人們在參加革命的準備時期,沒有讀過《共產黨宣言》的人不少,但是沒有讀過《資本論》的人卻幾乎沒有,列寧本人就是在做中學生時讀的。我們呢?當年傾向革命和準備參加革命的人們,首先讀的是《共產黨宣言》,但《資本論》,直到革命已經接近勝利,讀過的人還是不多。第一個《資本論》的中文全譯本——郭,王譯本,就是一九三八年才出版的。這時,已是十月革命后二十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十七年了!這種情形,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者們也不例外。記得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上海“神州國光社”的《讀書雜志》開展“中國社會史和中國社會性質論戰”時,參加“論戰”的學者們,還以“你讀過《資本論》沒有?”相譏。有的承認第一卷沒有讀完;只讀完第一卷的,用“馬克思自己也說第一卷有獨立的價值”的話作辯解,認為依此研究中國社會性質問題也夠了;而當時三卷《資本論》都讀完了的李季先生,則顯得是“鶴立雞群”,——幾乎在參加“論戰”的學者中只他一個。這種情形,固然是中國革命的政治特點使然(急迫地需要實際的革命行動),也是中國社會文化落后的特點使然(懂外文的人少);然而,《資本論》本身的偉大結構和近二百萬字的巨量篇幅(如計算第四卷進去是近三百萬字),不能不承認,即令今天,對我們一般同志說來,仍是個重負。這也說明了,為什么在有了再二、再三次的中文全譯本后,尤其是在革命取得了全國性勝利,和平環境,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也已大非昔比之后,閱讀《資本論》的情況仍是很不理想。這里存在著不是不重視讀,而是難于具備讀完它的條件的問題。
但是話應說回來,全國解放以后,我們大家讀《資本論》的必要性是更加強了。因為過去是政治斗爭、特別還是武裝斗爭第一,這以后是經濟建設第一。特別是黨和國家正以全力進行“四個現代化”的今天,經濟建設更是黨和國家的中心課題。這樣,我們大家更應該有健全的“經濟頭腦”,而這個所謂的“經濟頭腦”,第一個打基礎的工作便是讀《資本論》。《資本論》,對于我們連所謂“社會經濟結構”是什么回事都感到生疏和不理解的人們,就具有新的、特殊的意義。
讀《資本論》是萬分重要的,讀它,又有分量太大等的困難,怎么好呢?本書編輯者有感于此,懷著一種心愿,從四十年代在延安時開始,說來也有幾十年了,這就是想:有一部《<資本論>要略》,內容全是馬克思的,即還是馬克思自己在說話,編輯者外加的一般限于連接詞,并且也照恩格斯的樣,用括號標出來。《資本論》的原貌、它內含的思想照樣保留,主要是略去對前人的評判、引證和事例,于是沒有那么大的分量,二十五萬字左右,約占原書近八分之一,任何人都比較容易讀完。《要略》不代替《資本論》,也不是《資本論》的“通俗”講解,它是《資本論》的“縮本”性質。對讀《資本論》原書,它有引導和輔助作用(比如幫助抓住要點和理解原意);對一時無力讀完原書的人,它也能滿足了解《資本論》概要的要求,對《資本論》有個較為可靠的認識。這心愿,實現起來,在我可不容易。因為我以前的工作崗位不是研究工作,更與經濟無干;抗戰勝利,離開延安以后,敵后環境加全國解放,緊張的本職工作使我長時期無法去摸它,雖然通過封鎖線時都背著《資本論》走,從來沒有離開過。意外地,(幸乎不幸乎?!)無辜的災難使我失去自由,特別是十年內亂,監中生活倒給予實現這一愿望的絕妙機會了。經過這一次的再研讀和對在延安時做的舊筆記仔細審查,使我開始有拿出來的信心。
劉歆作《七略》,是為了給皇帝節約讀書時間;我這個《要略》,則是給讀書時間有限的同志們節約讀《資本論》的時間和緩和讀《資本論》的困難。這是一個新的意圖。馬克思也說過“凡事起頭難”,新意圖的開始,總是難于完善的。于是,我要請讀者同志們、特別是共鳴于這個意圖的讀者同志們,閱后給予指教,以便改進,使其能更好完成它應負的使命。
本書使用的譯文,除個別例外,采自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一九七五年出版的譯本。
一九八一年的十一月二十日,是為記。
(《<資本論>要略》,劉雪葦編著,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