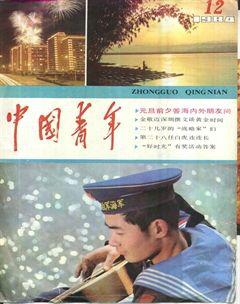楊振寧談治學(xué)
今天有機(jī)會在這么多年輕人面前,談一下我?guī)资昴顣⒔虝慕?jīng)驗,我很高興。
廣博的知識與扎實的根基
1938年夏天,我少念一年中學(xué),以同等學(xué)歷考入西南聯(lián)大。我在聯(lián)大物理系念了四年,得到了學(xué)士學(xué)位。
當(dāng)時聯(lián)大的條件比較困難。可是那時聯(lián)大讀書的空氣非常濃厚,學(xué)生非常努力,老師教書非常認(rèn)真。我們圖書館的書很少,而且期刊也常常要半年到一年的時間才到。可四年之間,我鉆在圖書館里學(xué)到了很多東西。
那時候我用的筆記本的紙是非常粗的,可并不因為這而減少了筆記的用途。直到今天我還有一個四年級念王竹溪教授量子力學(xué)的筆記本,還時常查看它,因為王先生教量子力學(xué),對特殊函數(shù)有很多的描述。
那時,西南聯(lián)大云集了清華、北大、南開三個學(xué)校的教師,教師陣容非常強(qiáng)大。我還清楚記得,我們大一國文就用所謂輪流教學(xué)法,就是每一個教授教一兩個禮拜。通常這種辦法是不好的,因為會產(chǎn)生大的混亂。可是那時西南聯(lián)大國文系的教師陣容非常強(qiáng),所以我們那一年之間就聽過朱自清先生、聞一多先生、羅常培先生、王力先生和其他許多知名學(xué)者的課,使我們對文史方面的知識有了廣泛的接觸。這是在當(dāng)時特殊條件下所創(chuàng)造出來的辦法。
那時物理系的教師陣容也非常強(qiáng)。我的大一物理是跟趙忠堯先生學(xué)的;大二力學(xué)是跟周培源先生念的,電磁學(xué)則是跟吳有訓(xùn)先生念的。那時候我們念書,和今天在美國大學(xué)念書有相當(dāng)不同的地方,那時的教師非常之認(rèn)真。所以,我當(dāng)時在中國所念的課都是相當(dāng)深、相當(dāng)廣、相當(dāng)詳細(xì)的。后來我到美國念書的時候,發(fā)現(xiàn)凡是我在中國念過的課,在美國聽時就沒有在中國那樣詳細(xì)、深入和廣泛。
科學(xué)研究與獨特風(fēng)格
我在西南聯(lián)大念了四年以后,又進(jìn)了聯(lián)大的研究院念了兩年,1944年得到了碩士學(xué)位。在聯(lián)大的最后兩三年,我開始了自己的研究生涯,在這里我特別感謝吳大猷教授和王竹溪教授。
那時西南聯(lián)大大學(xué)畢業(yè)需要寫一篇學(xué)士論文,所以我就去找吳大猷先生。“您可不可以做我的導(dǎo)師,指導(dǎo)我寫一篇論文?”他說:“可以。”吳先生當(dāng)時研究分子動力學(xué)非常有成績。他給了我一本《現(xiàn)代物理評論》,說:“你去把書中這篇文章研究研究,看看有什么心得。有心得的話,就可以寫論文。”
我把這篇文章拿回去給父親看。我父親是研究數(shù)學(xué)的,他對分子動力學(xué)沒有什么了解。可是他對群論是非常熟悉的。他翻看了一下文章,說:“你需要知道一些群論的知識。”他就給了我一本狄克遜寫的小書。狄克遜是我父親在芝加哥大學(xué)念書時的老師,他在當(dāng)時世界代數(shù)界是有名的。他的這本小書叫《近代代數(shù)理論》。這書中有一章,一共只有20頁,把群論中“表示理論”,用一個非常簡單、可是深入而美妙的方法進(jìn)行了描述。我看了幾天以后,得到了很深的印象。因為我吸取了這本書上講的一些精神。而且,這本書非常合我的胃口,它簡潔而又深入。
我通過這本書上講的群的數(shù)學(xué)結(jié)構(gòu),再去看《現(xiàn)代物理評論》,我漸漸地了解到這個群的表示,在物理里有非常美妙的應(yīng)用。后來,我就寫了一篇論文。這篇論文對我的一生有非常大的意義,倒不是它的內(nèi)容本身是那么重要,而是因為寫這篇論文的經(jīng)過,使我對群論,對對稱原理,發(fā)生了濃厚的興趣。而對稱原理是我以后物理研究工作的一個主干方向。
王竹溪先生是一個治學(xué)、做人都非常謹(jǐn)慎、努力的人,他的精神使我們當(dāng)時的同學(xué)都非常佩服。我做了研究生之后,就去找王先生,希望他指導(dǎo)我作碩士論文。他那時剛從英國回來,他在英國研究的是統(tǒng)計力學(xué)。在王先生指導(dǎo)下,我寫了一篇碩士論文。這篇論文對于我的一生也有非常大的影響,因為我一生中研究工作的第二個主干就是這方面的內(nèi)容。
我要和大家提一件事情,就是作科學(xué)研究是有所謂風(fēng)格的。也許有人會說,科學(xué)就是科學(xué),科學(xué)講的是事實,跟文學(xué)、藝術(shù)、音樂不一樣,事實有什么風(fēng)格?物理學(xué)所要研究的是自然界的一些物理現(xiàn)象和規(guī)律,把這個規(guī)律掌握住,就會發(fā)現(xiàn)它有很多美的地方、妙的地方。每一個人對于不同的美和妙的地方,會有不同的感受。同一個美的東西,不同的物理學(xué)工作者感受是不一樣的。通過每一個人不同的感受,他對于一些現(xiàn)象、理論、結(jié)構(gòu)就有偏好,通過這些偏好,他就發(fā)展出了他的風(fēng)格。這個風(fēng)格影響到他將來作研究工作取題目的方向,影響到他將來研究問題的方法。所以,風(fēng)格有決定性的作用。如果你去看一些重要的物理學(xué)家的論著,就會發(fā)現(xiàn)他們的風(fēng)格是很不一樣的,他們之間文章的差別跟不同文學(xué)家文章的差別是一樣的大。一個年輕人達(dá)到了他自己能夠掌握住風(fēng)格,了解到自己所使用的風(fēng)格,這就是他在研究工作發(fā)展中成熟了的表現(xiàn)。
我在西南聯(lián)大的七年很幸運(yùn),學(xué)到了很多東西,并且掌握住了一些杰出的物理學(xué)家的風(fēng)格。當(dāng)時我最佩服、直到今天我還是最佩服的近代物理學(xué)家有三個人:愛因斯坦、費米、狄拉克。這三個人的風(fēng)格是不一樣的,不過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能夠在非常復(fù)雜的物理現(xiàn)象里,抓住了精神。物理現(xiàn)象通常是很復(fù)雜的,這是和數(shù)學(xué)不一樣的地方。可是在這許多復(fù)雜的現(xiàn)象里,你如果能抓住精神,這個精神卻常常是很簡單的。而他們?nèi)齻€人都有這個能力,在非常復(fù)雜的物理現(xiàn)象里抓住精神,并把這個精神用很簡單的、常常是很直接的而又非常有力的數(shù)學(xué)方法表示出來。這就是他們所以是大物理學(xué)家的道理。
完善研究方法與選擇正確方向
1945年我從昆明動身到美國去進(jìn)研究院。到了紐約之后,我就到哥倫比亞大學(xué)去找費米教授,因為我聽說他戰(zhàn)前是在那里當(dāng)教授。后來我又聽說費米要到芝加哥大學(xué)做教授,所以我就申請了芝加哥大學(xué)的入學(xué)許可,1946年初進(jìn)了芝加哥大學(xué)。在那里我念了兩年,1948年夏天得到了博士學(xué)位。
我在芝加哥大學(xué)學(xué)到了另外一些非常重要的東西。那時物理系對我影響最深的教授是費米和泰勒。和他們兩位接觸多了以后,我了解到,原來物理學(xué)跟我在中國所念的物理學(xué)不完全一樣。物理學(xué)有另外一個天地。可以說,我主要從他們兩位那里了解到,物理學(xué)里除了平常在中國所熟悉的演繹法以外,還有歸納法。演繹法是先講出一個原理,然后推理;歸納法是先講出一個現(xiàn)象,然后從這個現(xiàn)象歸納出原理。這兩個方法當(dāng)然是相關(guān)的,可又是不同的重點研究方法。如果說,我在中國學(xué)的主體是演繹法的話,那么在芝加哥大學(xué)學(xué)的則是歸納法。譬如泰勒教授,他對于現(xiàn)象的掌握是很多的,而且他的主意非常多。每一個現(xiàn)象一講出來,他就有一個想法,說這可能是什么原理。他的這些想法90%都是錯的。不過這沒有關(guān)系,只要他有10%是對的就行。而且給我非常深的印象是,他隨便什么時候都有很多的見解,他不怕講出什么錯誤的見解。這也是和中國的教育方法不一樣的。中國的教育方法是,如果你不清楚的話,你最好不要講話。我非常幸運(yùn)在中國學(xué)了一個很好的演繹法,到了芝加哥以后給打亂了,說是我們從現(xiàn)象開始,現(xiàn)象才是物理的源泉,從現(xiàn)象開始你才能了解到這些原理是什么道理。
我最近這些年常常來到中國,發(fā)現(xiàn)中國的教學(xué)對于學(xué)生的壓力非常大,到處聽說“四大力學(xué)”。“四大力學(xué)”給我的印象就象四座大山,把人壓得喘不過氣來。你要問我“四大力學(xué)”是不是重要呢?是不是物理的精華呢?那我當(dāng)然承認(rèn)是。不過我要和大家特別講的,就是只有骨干的物理學(xué)是沒有生命的物理學(xué)。要有生命,除了有骨干之外,還要有血有肉。那么一個人如果只念“四大力學(xué)”,他所學(xué)的只是個骷髏。
我另外一件幸運(yùn)的事情,就是我在不知不覺之中走進(jìn)了一個領(lǐng)域,這個領(lǐng)域今天叫做高能物理,或叫基本粒子。基本粒子物理是從我做研究生的時候開始,漸漸地變成了一個重要的領(lǐng)域。象我這個年紀(jì)的一層人,可以說是和這個領(lǐng)域一起成長的。這是有關(guān)鍵性的。
我常常跟我們學(xué)校的研究生說,你到一個很好的學(xué)校,假如你是一個很好的研究生,這就必定代表你是有相當(dāng)能力的,要不你不會來到這里。可是象這樣成千有能力的人,過了幾十年以后,你就看出他們的成就差得非常遠(yuǎn)。這是什么道理?粗淺的道理是有些人走到了正確的方向,有些人走到了不正確的方向。走到不正確的方向,你再聰明,你再努力,也是做不出成果來的。你如果走到合適的方向,那么你在其中就可以大有發(fā)展;假如你走的方向恰恰是一個年輕的方向,是一個你可以和它一塊成長的方向,那么你是最幸福的。我奉勸所有要想做研究的人,不僅是科學(xué)研究,還有做其他任何研究的人,都要在年輕的時候,隨時給自己一個警惕,這是人一生做研究工作最最重要的一條。
回顧與總結(jié)
1949年秋到1966年的十七年,我是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工作;之后的十七年,即1966年到1983年,我又到了現(xiàn)在的紐約州立大學(xué)石溪分校。
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是一個有名的、非常成功的象牙之塔。所以,我離開時,很多人問過我:你離開那么好的環(huán)境的象牙之塔,而你又在那里做了你一生中最最重要的一些研究工作,你離開以后是不是后悔呢?我也問過自己,回答是:“不后悔。”因為象牙之塔雖然是重要的,可是象牙之塔不是世界上唯一重要的。創(chuàng)建一所大學(xué)是對社會作重要的貢獻(xiàn),一個人能在這樣的事業(yè)里做一些工作,他自己也可以覺得滿足。
1982年我六十歲了。我回想起自己幾十年的生活。千千萬萬在中國和我同年紀(jì)的人,在生活上有著無數(shù)困難的時候,我接觸到了自己能夠發(fā)揮能力的學(xué)術(shù)方向。我得到了中國良好的教育傳統(tǒng)給我打的根基,又接觸到了美國的非常良好的跟實際的物理發(fā)生關(guān)系的傳統(tǒng)。我有過很好的合作者,又有過很好的學(xué)生。我有十七年的功夫在最好的象牙之塔中工作,又有十七年的時間離開象牙之塔,投入社會,投入大學(xué)。我覺得其中幾乎每一件事,我都是最幸運(yùn)的。那么我得出的結(jié)論是:我還應(yīng)該繼續(xù)努力。
楊振寧教授1983年12月27日下午,在中國科學(xué)院研究生院作了題為“讀書教學(xué)四十年”的講演。此文根據(jù)楊教授講演錄音摘要整理,題目為編者所加。
——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