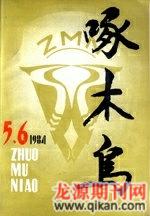別是一番天地
韶 華
回來了,回來了,經過四十多個春秋,我終于又踏上了這片土地!
汽車沿著豫北安陽通往中原油田所在地濮陽市的柏油馬路奔馳著。兩個小時之后,到了滑縣的白道口鎮。我讓汽車停下來,站在黃河古道的北大堤上。堤內是無垠的沃野,秋播的麥苗為大地鋪上了翠綠的毯子。堤外一片片棗林已落盡了葉子,鐵青的枝椏直刺著翠藍的天空。那么,白道口鎮的南寨門在哪里?我的戰友,當年高陵縣第三區區委書記李明德的墓碑在哪里呢?
一九四一年從滑縣到濮陽就有一條公路。這條公路構成了日寇封鎖豫北抗日根據地的封鎖線。白道口鎮是這條封鎖線上的一個重要據點。我那時才十四、五歲,由于個子矮小,常常奉命穿越這條封鎖線,做些傳遞密信工作。有一次,當我從這里通過的時候,南寨門上釘著一個人,四肢成大字型,釘了四根粗釘。鮮血把寨門都染紅了。他的臉面已血肉模糊,舌頭已被割掉,但口內仍然發出咕咕嚕嚕的聲音,他還在罵。門旁站著幾個持槍的兇神惡煞似的偽軍。通過寨門的老鄉,都低著頭。我悄悄斜視了一眼,從他那憤怒的目光中,我心頭一陣戰栗:這不是我們第三區的區委書記李明德同志嗎?
……李明德同志一直在寨門上釘了七天七夜,才停止了呼吸。那是一九四一年秋天,他才二十三歲!
我詢問了幾個老鄉,終于找到了李明德同志的墓碑。墓碑就在他當年犧牲的地方。但寨墻已經平了,寨門也沒有了。在殘留的一片土崗上,有一個磚砌的墳墓。墓前是一座兩米多高的石碑。上面刻著“李明德烈士之墓”。這里居高臨下。李明德同志:你該看到了吧!往南,百里沃野一片翠綠;往西,棗林里的樹木挺著不屈的枝丫;往北,鎮內新蓋的樓房簇擁而起;往東,一排農民賣棉花的大小車輛,擁塞著公路。你能看到吧?這一切不是都浸透著你的血跡嗎?安息吧,我的好戰友!我們的鮮血已經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開花結實了。
我在李明德同志墓前低頭默站了幾分鐘,思念著那些艱難、殘酷的歲月。然后驅車沿著寬闊的柏油馬路,向濮陽古城奔馳。
太陽已經落山,晚霞把兩半天都染紅了。然而,東方也是一片火光,一閃,一閃。隱約可以辨認出那高高的鉆井架,象頂天立地的無數巨人。那火光,是采油聯合站的火炬。火炬把東半天映照得象旭日即將東升。這火光又把我帶到了四十二年前。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二日,日寇對我們的抗日根據地進行了大掃蕩,實行了野蠻的“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掃蕩”過后,我們又回到這片根據地。啊!所有的村子都在燃燒,大地彌漫著焦糊的氣味。我們從一座大房子中,挖掘出四百二十具尸體。在一口水井中,日寇填進去七十二名無辜群眾,丟進炸彈,壓上石頭……然而,人民并沒有屈服。房子在燃燒,斗爭的烈焰燃燒得更旺。
現在,采油站無數火炬,映照著拔地而起的幢幢樓房。它們是屬于鉆井指揮部的?采油指揮部的?油建指揮部的?地質指揮部的?我不知道。但地面的萬家燈火,使星星顯得暗淡無光。她們含羞帶怯,在天空中退卻,躲閃,自愧不如。
夜晚九點,汽車停在一座大樓門前。大門上掛著一個牌子:“中原油田招待所”。
次日,在油田一位同志陪同下,我參觀了“文南”勘探前線,訪問了三二七七英雄鉆井隊和幾個聯合采油站。同時,按蹤尋跡,拜謁了“四一二”大掃蕩紀念碑和文留集二十八烈士紀念碑。離紀念碑不遠,有一個采油站的火炬,這是慰念烈士的照天長明燈!
通向范縣的一條大路上,我們碰上了一條“封鎖線”。汽車不得不停止下來。這是農民們售賣余糧的車輛把道路堵塞了。
由于油田剛剛開發不久,道路建設跟不上去,油田的汽車、農民賣糧、賣棉花的車輛,常常堵塞道路。我們的汽車司機走下車子,往前走了一段,看看可否擠出一條道路。然而,農民的馬車、牛車、人力架子車,前不見頭,后不見尾。有的已經在這里等了兩天。他們干脆帶著被子,在路旁躺下睡覺等著,也許兩三天以后,才能輪到糧站收購自己的糧食。以前,我只在報紙上看到“人民來信”呼吁解決農民“賣糧難”和“賣棉難”的問題。而今,是一次直接的觀察體驗。道路已經完全堵塞,但各種車輛還在往前擁擠,越擠越不能通過。我們的司機笑著說了一段順口溜,形容車輛擁擠的情況:“大老爺(汽車)橫沖直闖,二老爺(牛車)搖搖晃晃,三老爺(架子車)見縫就鉆,四老爺(自行車)寸步不讓!”啊,真正的“封鎖線”。
眼前的“封鎖線”又使我追憶起四十二年前一次穿過“封鎖線”的情景。
一九四一年日寇對豫北的滑縣、清豐、南樂、濮陽進行“四一二”大掃蕩以后,那年又是一個顆粒未收的荒旱之年。到四二年春天,據調查,抗日根據地的人民,每人每天只能吃到幾錢糧食。人們走著路,來一陣風刮倒就起不來了。經常遇到躺在路旁的餓殍。沒有力氣,沒有種子,眼看土地要撂荒了。當時,魯西的范縣,觀城,濮縣有些糧食。抗日人民政府決定:從這一帶地區背糧給豫北根據地人民救荒。誰種上一畝地,發給誰一斤糧食,并免費供應種子。當時,日寇從濮陽到清豐修了一條公路,路旁碉堡林立。要從魯西把糧食運到豫北,得通過這條“封鎖線”。抗日民主政府,動員了幾百輛大車和一支部隊掩護,把糧食運過去。我們宣傳隊的隊員也參加了。每人背一、二十斤糧食,傍晚從范縣的某村出發,半夜通過濮(陽)清(豐)公路。一路之上,只有小聲的口令“往后傳:跟上!”“往后傳:不要掉隊!”一夜行程百二十里。在天亮到達目的地的時候,我一躺下,再也站不起來了。
兩次過“封鎖線”:那次是“吃糧難”,眼下是“賣糧難”。同樣是“難”,難的性質有多么大的不同呀!
我決定找一位當年在此地戰斗過,如今又在這里開發油田的同志談一談。我找到了油田的副局長胡振民同志。這是一位五十多歲的老八路。墩實的身材,樂觀的性格,談話中不時爆發出爽朗的笑聲。從五十年代,他已經轉業到石油戰線。艱難的歲月,戰斗的歷程,在他黑紅的面龐上刻下條條皺紋。中原油田第一口油井在七五年七月八日噴油。胡振民副局長,正在南陽油田(當時濮陽勘探區隸屬南陽油田領導)。他聽到第一口油井噴油的消息,回家提了個牙具袋,坐上汽車就直奔濮陽。他和司機替換開車,一夜行程八百公里,他要在這里組織開發油田的第一個戰役……
現在,中原油田的開發已經初具規模。當前的任務是不斷擴大勘探區域,找到更多的地下儲油構造。胡振民同志已到離休年齡。“我想,在離休前再給國家找一個油田。”他說。目前,他已經接到去黃河以南東明縣勘探區去的命令。因為我的采訪,特地多留了一天。這天,我們談過話,驅車來到黃河大堤上。大堤變成了一條公路,車水馬龍,川流不息。有不少攤販在這里售賣熟食。這個地方名叫李橋。堤上立了一個碑:上寫“劉鄧大軍過河處”。一九四七年夏季,劉鄧大軍就是從這里渡過黃河,開辟了新戰場,扭轉了整個解放戰爭形勢的。
“愿你此番過得河去,打開中原油田勘探的新局面!”我說。
“是的!”胡振民同志笑了“過去我們過河是去消滅國民黨;現在過河是要找到新的石油儲量。無論哪一個任務,都要求一支鋼鐵隊伍——豆腐渣隊伍不行!我們這支隊伍無論過去和現在,都是有戰斗力的!哈哈!”他爽朗大笑了。
回到油田招待所,心潮起伏,夜不能寐,填詞一首。
中原油田抒情
——調寄東風第一枝
光陰如飛,
彈指四十,
我今信手帶住。
足踏戰斗蹤跡,
追憶狼煙遍地,
河山破碎。
念村砦,墻殘壁斷,
尸橫野,腥風血雨,
國仇家恨永記。
轉瞬間,鉆塔如林,
指顧中,霞光火炬,
染紅天際半壁,
高樓春筍拔起,
五彩映趣。
看黃河急浪奔濤,
穿地層,噴金吐玉,
別是一番天地。
一九八四.八.二○沈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