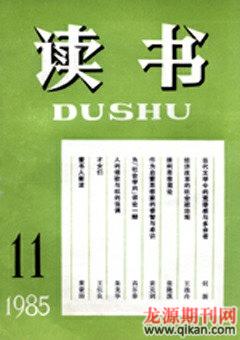作為啟蒙思想家的睿智與卓識
黃克劍 丁 聰
也許只是到近代,時間和空間意義上的機運的捕捉,對滯后的中國才是那樣地契合:它怎樣走向世界,它也怎樣走向未來。在西方文明以最野蠻的方式震撼東方之后,希圖自己民族繼續體面存在的中國人,在歷史給定的極有限的選擇余地內,就自己民族命運問題投下無限思慮和才智。選擇總是以比較為前提的,時代就這樣把中西文化比較研究——這個在西方被更早注意的課題——提示給中國思想史。
中西文化比較研究在中國的發萌,或可上溯到西學東漸的初始,但它被作為一個急迫的社會問題提出,卻是鴉片戰爭以后的事情,因為只是在這時,兩種文化的愈來愈擴大和深入的接觸才引發出早就孕育著的社會沖突。魏源的《海國圖志》開啟了近代中西文化比較研究的端緒,此后,馮桂芬、王韜、薛福成、馬建忠、鄭觀應等早期改良主義思想家,對他們的變法救時的“盛世危言”的申述,都無不以中西文化問題為出發點。“危言”的積極方面,做了戊戌變法的前導,消極方面則為張之洞為代表的洋務派所摭拾,嬗變為一種所謂“中體西用”的中西文化觀。“中體西用”是處于末世的中國封建階級可能提出的最明智的見解,它表征著這個階級的胸懷和視野的極限。當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寄希望于政治維新,試圖尋求一種“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文化形態時,他們成為第一批超越這個極限的人,但新階級的中西文化觀的締造,卻是由它的啟蒙思想家——被魯迅稱做“十九世紀末年中國感覺敏銳的人”——嚴復著手的。
歷史成全了值得成全的人,在近代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相繼東漸之后,西方資產階級的經典世界觀經由嚴復合乎邏輯地來到中國。這個比千百個江南制造局或更多個北洋艦隊重要得多的事件,標志著西學東漸的一個相對完整時期的結束,它帶來的是近代科學意義上的中西文化比較研究在中國的真正開始。先前所做的,至多只是一種準備,現在開始的,才具有真實的結果;這最初的收獲,薈萃在嚴復的《論世變之亟》、《原強》、《主客平議》、《救亡決論》、《辟韓》等論著和《天演論》、《原富》、《孟德斯鳩法意》等譯述中。
時過八九十年,名作再讀,書中的憂患、抑郁、昂憤之感和抗爭的勃勃意氣,依然激撞著學人的情懷。在那文字深處,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曾經攀上時代峰巒,為一代改革作過啟蒙吶喊的人的睿智卓識。
一、“中之以世為日退”和“西之以世為日進”——中西社會發展觀的比較作為民族文化潛在意向的理性顯現的社會發展觀念,往往以傳統意識的形式,調整并制約一個民族的文化脈搏的節奏。辨析民族的社會發展觀,是破譯民族文化心理、確定民族文化時代價值的契機所在。嚴復的中西文化比較研究,從中西社會發展觀的比較得到的是一個富有科學價值的起點。
《周易)、孔、老以降,中國哲學幾乎無不確認變易為事物的常則,但變化觀念始終缺少進化的意味。《易經》的所謂“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老子的所謂“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直至清代龔自珍的所謂“萬物一而立,再而反,三而如初”,都把變化解釋成一種沒有質的超越,也沒有宏觀上的確定方向的循環往復。這種變化觀用于審視社會,則有中國傳統的歷史循環論,孟軻的“五百年必有王者興”,鄒衍的“五德終始”說,董仲舒的“三統循環”論,都是這種歷史循環論的程式化。千百年來,這種社會變化觀以理性、潛理性的方式由一代延續到下一代,形成一種頑固的傳統意識。這種意識,即使象王夫之那樣的杰出思想家也難以脫其羈絆,他的別具一番精神的哲理,曾經象“昭蘇天地”的雷聲震撼過無數學子的心靈,但一談起社會嬗變,卻只有“治亂循環”之類的迂腐平庸之論。
嚴復比他的同時代的任何人都更深刻地看到中國文化的痼疾所在,他把中西在社會發展觀上的懸隔,認作是中西文化的本質差別之一。他指出:“中之人以一治一亂、一盛一衰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進無疆、既盛不可復衰、既治不可復亂為學術致化之極則。”(《論世變之亟》)前者是基于天人感應的循環論,后者是訴諸人的奮爭、創新的進化論。同這兩種社會演變觀相表里,中西對古今價值的不同判別生出兩種不同的歷史態度:“中之人好古而忽今”,沉溺于祖先的業績,不重當下的努力;“西之人力今以勝古”,不為前賢所拘,只是一味執著地向前追求。嚴復認為從這兩種態度出發看待社會的發展和治理,在中國人那里常常是“今不若古”,世道日退;在西方人那里,則是“古不及今”,世事日進;前者處事安于循規蹈矩,后者處事注重革故鼎新。
歷史循環論不可能從宏觀的角度認識社會演化的總進程;對這個總進程作出某種階段劃分,只有歷史進化論才可能做到。嚴復本諸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進化理論,以社會的進化比之人身的童少壯老,認為各民族的社會無不“始于圖騰,繼以宗法,而成于國家”(《社會通詮序》),并以此斷定英法等西方民族在一二百年前就已經進到國家階段,而中國直到今天“籀其政法,審其民俗,與其秀桀之民所言議思惟者,則猶然一宗法之民而已矣”(同上)。他從社會進化的角度,把中國同西方的文化差別歸結為古今時代的差別,把唐虞以迄文武周公這些為人們千古尊崇的圣人,稱做宗法社會的圣人,把被后人理想化了的這一時期的制度典籍,稱之為宗法社會的制度典籍。在嚴復那里,那些曾經為民族帶來成功和驕傲的人和事物,不再被作為未來的楷模,而只是被敘述為已逝的歷史。強烈的時代感和相對科學的社會歷史觀,構成嚴復的中西文化比較研究的真實生命,在他的克服并超越了“中體西用”論的“中西古今”說中,我們所領受到的是一個啟蒙思想家帶給中國以希望的時代精神,是一個一定程度觸摸到“現代化”神經而為之奔走呼號的“改革者”的苦苦用心。
二、“自由既異,于是群異叢然以生”——中西價值觀的比較相對于發展觀念,價值觀念屬于民族文化更深的層次。嚴復的中西文化比較研究最有價值也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他對中西價值觀的比較。近代西方價值觀念的核心是“自由”。對“自由”的珍重和畏忌被嚴復看作是中西價值觀的根本差異。嚴復指出,在中國,堪與西方的“自由”比擬的觀念是所謂“恕”和“
作為價值觀念的“自由”,既不是哲學認識論領域相對于必然的范疇,也不是政治或一般社會管理領域的相對于紀律的范疇,嚴復對這個觀念的意蘊,從多方面作了較為準確的剖析。他的最值得注意的一個界說是:“自由者,各盡其天賦之事,而自承之功過者也。”(《主客平議》)“各”和“自”,強調的是以個人為本位,“盡其天賦之能事”,說的是人生義務,功過“自承”,指的是社會責任。這里涉及到對個人作為有價值的主體的確認,也涉及到個人對社會的義務和責任,這是符合西方近代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對他們所一再伸張的“自由”觀念的理解的。由于嚴復是在中國的現實下談自由的,他在許多地方更多地強調自由在否定人的奴隸地位方面的意義,在同一意義上,他談論自由時還論及“自主”、“自立”、“自治”等同自由意義相通的觀念。所謂“身貴自由,國貴自主”(《原強》),是嚴復在十九世紀末年所作的啟蒙吶喊的重心所在。
“自由既異,于是群異叢然以生”(《論世變之亟》),嚴復抓住中西價值觀的根本差別,對體現在政治、道德、財用、社交、學風、民俗等方面的價值觀念作了全面的對比。他指出:“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國親親,而西人尚賢;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國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國貴一道而同風,而西人喜黨居而州處;中國多忌諱,而西人眾譏評。其于財用也,中國重節流,而西人重開源;中國追淳樸,而西人求歡虞。其接物也,中國美謙屈,而西人務發舒;中國尚節文,而西人樂簡易。其于為學也,中國夸多識,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禍災也,中國委天數,而西人恃人力。”(同上)“重三綱”、“親親”、“以孝治天下”,其基本出發點是封建的等級本位和宗法的血緣世系,“明平等”、“尚賢”、“以公治天下”,則以個人本位和人的“政治解放”為前提;“尊主”、“多忌諱”、“一道而同風”,表現了重“一”輕“多”、崇拜偶像的民族心理,“隆民”、“眾譏評”、“黨居而州處”,則反映著厚“多”薄“一”、個性自由的價值要求;“重節流”、“追淳樸”,恪守的是“止足為教”、“安于樸鄙”的節欲信條,“重開源”、“求歡虞”,則以“日進無疆”、避苦求樂為人生信念;“美謙屈”、“尚節文”屬于等級倫理的外在禮儀,“務發舒”、“樂簡易”則是對個性實現的直率追求;“夸多識”緣于學術上的守成和依傍,“尊新知”則崇尚學者的獨樹和創新;“委天數”是面對自然力的自輕自賤,“恃人力”則顯示著人對當下環境的超越本質。上述差異都出于對人的自由價值的褒貶揚抑,質言之,都出于人生價值觀的不同抉擇;重自由是近代人道主義的價值觀,賤自由是中世紀“精神動物學”的價值觀。
嚴復注意到,民族的價值觀是民族文化的神經中樞,他把“自由不自由”這一中西價值觀的根本差異,看作是中西文化根本精神的差異。嚴復認為,西方的“汽機兵械”,不過是西方文化“形下之粗跡”,就是先進的近代“天算格致”之學,也只是其“能事之見端”,只有學術方面的“黜偽而存真”和刑政方面的“屈私以為公”的原則,才是這種文化的命脈所在。他看到這兩個原則同中國文化起初之所求并沒有多少區別,它們在西方行得通,在中國卻行不通,其緣由所在“則自由不自由異耳”。無疑,嚴復是對的,以中國哲學的傳統范疇——“體”——來說明其地位的“自由”,是近代西方又化的真正靈魂。
三、“君主”和“民主”———中西社會“治制”的比較“有牛之體,則有負重之用,有馬之體,則有致遠之用”;有異若霄壤的中西文化之“體”,就有判然兩途的中西文化之“用”。見于政治、法律的“用”,被嚴復稱做社會“治制”。嚴復認為,西方勝于中國有“有法”勝,有“無法”勝;勝之于自由平等等價值觀念的,是“無法”勝,勝之于社會治制的,是“有法”勝。相對于“無法”、“有法”的社會治制的比較,構成嚴復中西文化比較研究的又一個重要方面。
自由,平等,自主,民主,——在嚴復那里是層次不同的概念:“言自由者,則不可不明平等,平等而后有自主之權,合自主之權于治一群之事者,謂之民主。”(《主客平議》)在社會治制相對于價值觀念的關系的意義上,他斷言近代西方是“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原強》)。現代中國人往往以“民主”為“集中”的對應范疇,這樣,“民主”便只剩下褊狹的(領導或管理)方法上的意義;嚴復所說的“民主”是一種社會治制的基本精神,同這種精神相對的是“君主”和“專制”。嚴復把近代中西社會治制的差異歸結為“民主”與“君主”(乃至“專制”)的差異,在比較“民主”與“君主”的治制時,他注意的是“平等”的觀念。
“中國君主也,而有三綱,美洲民主也,而父子兄弟平等。”(《孟德斯鳩法意》案語)“三綱”是對人與人的宗法等級關系的格律化、神圣化,它的內核是認可人對人的等級依附和等級統攝,它的外飾則是所謂“禮讓為國”。中國的“君主”治制因此也可稱做“人治”(就其內核論)或“禮治”(就其外飾論)。“平等”是為自由的價值觀所要求的另一種人與人的關系,它否定血緣宗法對人的社會地位的派定,而訴諸被西方啟蒙思想家詮解為“契約”的“法”:在“法”面前,每個人的被承認是以自己而不是以家族或等級的名義,西方的“民主”治制因此也稱之為“法治”。“人治”和“法治”,這兩個分別注有不同時代內容的概念,至今使許多中國人困惑不解,而當年的嚴復卻一定程度地觸到了它們之間的差別的實質。誠然,嚴復并沒有真正道出歷史的底里:君主治制的“人治”的秘密是“人的依賴關系”,民主治制的“法治”的秘密是“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馬克思)。
嚴復沒有忽略西方與中國在“法”的觀念上的差別,他看到近代西方之法是“治國之經制”,其“既立之余,則上下所為,皆有所束”,而中國所謂“法”,“直刑而已,所以驅迫束縛其臣民,而國君則超乎法之上,可以意用法易法,不為法所拘。”(《孟德斯鳩法意》案語)在西方,法是政治權利平等的衡準,在中國,法僅僅用于“督責”;前者保證著治制的民主性質,后者則常使“君主”治制趨于“專制”。所以嚴復在有的地方徑直說:“中國以政制言,則居于君主專制之間”——“運隆則為有法之君主,道喪則為專制之亂朝”(同上)。
君民關系是嚴復比較中西治制時悉心考察的一個方面。他指出,西方立憲國家中的君民,是真正的君民,這是因為他們都有權,在立法上總是“君民并主”的;中國則不然,君與民“世隆則為父子,世污則為主奴,君有權而民無權”。這一點,在他看來,正是“東西治制之至異”之處(同上)。立于法學世界觀的立場,嚴復從君民關系的角度,對中國的封建專制制度作了激烈的批判,他稱秦以來的君主是“最能欺奪者”、“大盜竊國者”,而稱民為“天下之真主”,認為這些君主的多如
任何一種有一定歷史地位的思想,都可能在思想的歷史上找到某些貌似相類的“原型”,但這并不就是精神的“返祖”。嚴復對中國封建治制的批判,有些言詞頗近于黃宗羲,而對孟軻的名句“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援引,更給人一種儒家“民本”思想的印象,但事實上,嚴復的批判是“既通西學之后”對中國傳統治制的“反觀”,這里一方面有西方“民主”治制作參照系,更重要的則是他用以判斷事物的理論座標已經是法學世界觀。“民本”所針砭的只是封建治制的特殊形式,“民主”所否定的是任何形式的封建治制。黃宗羲的“把許多青年的心弦震得直跳”(梁啟超)的激憤之詞雖不無民主色彩,卻畢竟未能沖決作為封建治制之體的中國文化的傳統價值觀,而在嚴復用以同“君主”對立的“民主”后面,則是近代西方治制基礎的“科學”和作為民主精神之體的“自由”。在黃宗羲那里,現時的批判還沒有關于真正超越現時的未來的設想,在嚴復那里,作為批判的歸宿的理想藍圖——君民共主的立憲國家已經觀念地存在著。
四、“貴獨獲創知”和尚“述古循轍”——中西治學精神的比較同人類動物時期的中世紀決絕的西方,學術第一次贏得了它的獨立價值和榮譽,過去乞求上帝啟示的一切,現在“一一皆本諸學術”。和“屈私以為公”的刑政一起,“黜偽以存真”的學術成了西方近代文化的命脈。“屈私以為公”的底蘊在于民主,“黜偽以存真”的底蘊在于科學;在嚴復看來,后者同前者一樣,作為西方文化之“用”,它所對應的“體”依然是“自由”。學術自由不是外來的賜予,而是一種內蘊的精神,嚴復關于中西治學比較的用心之處,也許正在于由“用”到“體”的反思。
西方“貴獨獲創知”,中土尚“述古循轍”(《天演論》案語),這個在嚴復的著述中再三致意的觀點,是他對中西治學精神的基本差異的表述。治學是諸多社會事業中最具個性化特色的活動之一,它的不竭的生機在于對以往學術界限的超越和既得知識系統的揚棄。“貴獨獲創知”就是尊重學者賦有個性色彩的創造機制,并以此肯定人類理性的永無休止的進取。盡管嚴復對“獨獲創知”的理解遠不如現代學者們體會得那么深切,但他對近代西方治學精神所作的這個概括是無愧于他的時代的。嚴復也有這樣的說法:西方治學“以格物致知為學問本始”,所得學理“一一皆本于即物實測”(《原強》);這些治學原則很有些“從實際出發”的意味,因而似乎更根本些。但這一方面還只是對西方經驗派的治學原則的歸納,另一方面,原則的實現也還有賴于“獨獲創知”的治學風尚的倡明。“貴獨獲創知”,才不致真理為權威所屈或新見為成說所抑,因而也才可能在學術界做到每個學者“各盡其天賦之能事,而自承之功過”,做到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嚴復所謂西人授教,必使受教者“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貴自得而賤因襲,善疑而慎信”(同上),是他從一個側面對“貴獨獲創知”治學精神的一個有意味的說明,“自竭”、“自致”、“自得”、“善疑”、“慎信”,都深寓著對于學術生命最可寶貴的個性“自由”。新的程式化的思維,常常使人們更多地把近代西方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以至哲學的繁榮同社會的經濟和政治原因聯系起來,但“貴獨獲創知”這個發人深省的具有價值意義的原因,卻往往被忽略,而這一點,嚴復早就提醒過缺少自我意識價值觀念的中國人。
有鑒于西學的“貴獨獲創知”,嚴復對中國好“述古循轍”的傳統治學風習作了痛切而深沉的反省。嚴復指出,“中國由來論辨常法,每欲求申一說,必先引用古書,詩云子曰,而后以當前之事體語言,與之校勘離合,而此事體語言之是非遂定。”(《名學淺說》)他認為以這種方式求學致知,無異于一桶水從這個桶傾進那個桶,傾來傾去,還是那么多水,新的知識既無由取得,就是古人的東西也未必能夠真正理解,因為古人的道理原是有是有非的,如果不分是非地一味篤信,對其中的非無所辨識,那么對其中的是也就無從理解其所以為是了。
“述古循轍”的風習影響到思維,必然是演繹的抽象化和歸納的被輕蔑,而一意于詞章記誦和注疏訓詁,又必然導致以思維規律思維形式為對象的邏輯學的衰微。嚴復對中國治學“偏于外籀(演繹),于內籀(歸納)能事極微”(同上)的指出,對中國邏輯學“古人發起端,而后人莫能竟其緒;古人擬其大,而后人未能議其精”(《天演論》自序)的品評,都可看作對“述古循轍”的一種批判,而他對與之相長的八股之風的鞭撻,尤其表達了他對舊的治學習尚的深惡痛絕。
“述古循轍”是學術上的“好古而忽今”。它同自然經濟、宗法政治一樣,遵循的是動物學的邏輯:動物通過遺傳本能把本能遺傳給下一代,精神的動物通過訓詁注疏留給下一代以動物式的精神;人的精神的高貴原在于它著意引導人們對既定的精神界限的不斷超越,而“述古循轍”的學術卻讓人的精神自己囚困自己——嚴復雖然不曾把這個邏輯合乎邏輯地昭示在他的著述中,但這個邏輯的被體味,不正說明著引發體味的那些著述,至今仍不失時代價值的啟蒙作用么?
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八日于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