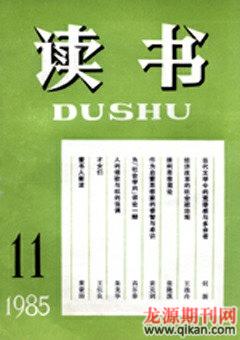梁啟超如何評價崔述
傅卓犖
蔡尚思先生的《中國文化史要論(人物圖書)》“歷史學與地理學上的代表人物和主要圖書”一節論崔述與《考信錄》說:
“是古代史學上疑古派的一個代表,但還不足稱為集古代疑古派之大成。因為他不僅不敢疑經,而且以經為其他一切的標準,這種疑古,還是一種信孔尊經的疑古,連王充、劉知幾、李贄等也不如了。梁啟超以崔述‘經書以外只字不信為‘豪杰之士,荒謬!”
蔡先生在這里先指出不敢疑經,反以經為衡量其他一切的準繩,是崔述的主要缺點;而后說梁啟超先生以崔述為“豪杰之士”的原因,即在他“經書以外只字不信”這一點——無疑是說梁啟超把崔氏的主要缺點當做主要優點了。倘若真是這樣,那梁先生固然是可以并且應該被斥責為“荒謬”的了。但事實上,蔡先生在這里所據以指斥的引語,與梁先生的本意不無距離。這幾句話,都出自梁先生的《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一文,該節原文是這樣的:
“嘉慶間,則有從別的方向——和馬宛斯正相反的方法以研究古史者,曰崔東壁(述),其書曰《考信錄》。太史公謂‘載籍極博,猶考信于六藝,東壁墨守斯義,因取以名其書。經書以外,只字不信,《論語》、《左傳》尚擇而后從,《史記》以下更不必論。彼用此種極嚴正態度以治古史,于是自漢以來古史之云霧撥開什之八九。其書為好博的漢學家所不喜;然考證方法之嚴密犀利,實不讓戴、錢、段、王,可謂豪杰之士也。”
很明顯,梁先生在這里提到“經書以外只字不信”,旨在紹介《考信錄》的得名之由與著述體例;而所以贊賞崔氏為“豪杰之士”的原因則主要在于崔氏把“自漢以來古史之云霧撥開什之八九”的考史成績,以及他“實不讓戴、錢、段、王”的“嚴密犀利”的“考證方法”。“經書以外只字不信”與“豪杰之士”之間,決沒有如蔡先生所組截的那樣直接的因果關系。
固然,在同一文中,梁先生還說過崔述“對于先秦的書除《詩》、《書》、《易》、《論語》外幾乎都懷疑;連《論語》也有一部分不相信。他的勇氣真可佩服。”其意也不過是因為崔述所處的時代,“實在那時信古的空氣已壓倒了疑古了”(顧頡剛先生《崔東壁遺書序》語),所以認為崔述能夠這樣疑古,已屬不易,并非因他只信經書,所以才佩服他。設若崔氏能更進一步地大膽疑經以求古史之真的話,則梁先生對他當會因此即摒斥呢?抑或是更加贊賞呢?我認為我們更有理由同意這后一種推斷。請看梁先生在《古書真偽及其年代·總論》中論及崔述的一節:
“同時出了一位名聲很小的辨偽大家,就是著《考信錄》的崔述。他把春秋以后諸子百家傳說的古事,一件一件的審查辨別哪是真的,哪是假的,使得古史的真相不致給傳說遮蔽。……他雖然迷信《五經》、《論語》、《孟子》,卻也不能不疑其一小部分。他辨偽的方法,除了‘考信于六藝以外,還有許多高妙的法門。他解釋作偽的原因,能夠求得必要的條件。尤其是他那種處處懷疑、事事求真的精神,發人神智,實在不少。”
從這段話,我們可以知道梁先生對崔述的三點態度:一、崔氏對《五經》、《論》、《孟》的態度為“迷信”的;二、對崔氏的辨偽方法,除“考信于六藝”以外的其他“許多高妙的法門”是贊賞的,并不要求以六藝為唯一的衡量標準;三、最欽佩崔氏的地方,即在“他那種處處懷疑、事事求真的精神”以及他認真嚴密的辨偽方法。
更明白的,是在我們開頭引的梁先生論及“豪杰之士”的那段文字之下,梁先生更接著寫道:
“第一問題中春秋前史跡之部分,崔東壁所用方法自優勝于馬宛斯。雖然,猶有進。蓋‘考信六藝固視輕信不雅馴之百家為較有根據,然六藝亦強半春秋前后作品,為仲尼之徒所誦法,仲尼固自言夏殷無徵,則自周以前之史
這再一次說明梁先生所贊賞崔述的,主要是他懷疑、求真的治史態度和認真、嚴密的考證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