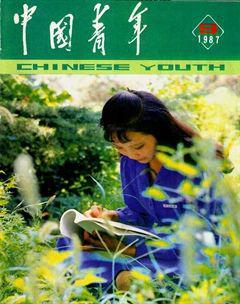部長那天沒來(小說)
我不知道那輛車上坐的是另外一個人。直到今天我還搞不明白,他們為什么要那樣做。反正我覺得自己被涮了。我一想到那天的全部壯舉(如果那還稱得上壯舉的話),就象一只被踩扁的氣球,活脫脫一副如喪考妣的表情。
當那輛有可能載著一個海瑞或包公的上海牌小轎車輕盈地泊在我們鑄鐵車間前的花園時,我就熱血沸騰,心兒跳得如同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后要去見面的那個人。我之所以用人世間所有的光棍漢都會向往的那件事類比,絕不是有意褻瀆人類最美好最純真的感情。簡言之,我有時候有損一個男人的形象,如同少女尋找男子漢那樣來尋求部長的保護。可我沒想到事情會是這樣的。那輛車上坐著的是我們寇廠長(自從王翠花吞藥水后,我就稱他為寇廠長了。其實他姓冠,叫冠什么來著)。當然我這是后來才知道的,要是我知道那上面坐的是寇,就是給我一千塊大洋,我也不會去冒那個險。
既然我已經提到我們這個寇廠長,就不得不羅里羅唆地給上他兩句。假若我用涼水沖沖頭的話,我會夸張一點地說寇廠長真是個山圪瘩里的喬廠長。有一個時候,喬光樸是很有點市場的,特別是象我們這個人心浮動、靠貸款發工資的山菲山柴油機廠。自從受了蔣子龍的影響后,幾千來號職工就象得了相思病似的,尤其是那些正在向超短裙牛仔褲迪斯科奮進的小妞們動不動就是要是咱廠來個喬廠長如何如何。這真叫我們這些不姓喬的男子漢嫉妒。反正人心思喬,猶如久旱渴雨,就在這個當口寇廠長來了。他用什么方法將我們這個瀕臨倒閉的柴油機廠起死回生,我就不多說了,因為楊在葆在那部叫《血,總是熱的》片子里已經代替我說了,更何況蔣子龍的版權我無法侵占。我只是想告訴讀者一句,后來,在他沒乘那輛上海牌小轎車來我們車間之前,他對那些帶長的小“柴油機”們說過這樣一句話:“誰要是對我不仁,就別怪我對他不義。”當然,這只是聽說,他又沒有親口這樣對我講。不過這已經大大地激起我的胃口了。我干嗎不給他捅捅?我真的就被這一句流言嚇倒了嗎?
可我并不是想揭露在部長到來之前我們廠是以怎樣誠實的心情來整改的,我也不想光提為了歡迎檢查團僅僅油漆錢就花了好幾萬元的那些事。頭頭們有他們的苦衷。他們大把花錢沒有什么讓人談偏的動機。再說,我也是這個廠子里的人嘛,企業上了等級,我不也可以撈上個半拉一級的?不過,即使這樣,也并不妨礙我等部長下來的時候,和他好好談一談。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我忘了說,它極大地影響了我的情緒。當那輛上海牌小轎車還沒影兒的時候,不早不晚,王翠花在這個節骨眼上撒手去了。我沒想到她會這樣,盡管我知道她這樣活著不是個事,可我沒想到她會去得這么早。其實我對她印象還是蠻不錯的。盡管有人說她是個破貨,在d縣的重工業局里工作時被六個男人干過。這或許是捏造,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即使她身子真的不干凈了,象這樣的女孩我敢肯定一定是遭人害了。我知道,在我們山菲山柴油機廠說她破貨的人盡管對她大吐唾沫,罵她賤啊騷啦什么的,假若人家真的是個那樣的,他們是不會放過機會的。我想說她是破貨的人,很少不想順手在她梨花帶露的臉上擰一把,或者在豐滿高聳的胸房摸一下的。我得說自己對她也有過這一類的念頭,當然我這樣說并不是想去沾她一點便宜,我只想正正經經地和她軋朋友。在我們玩過多次惶亂而興奮的跳開與接近的眼睛游戲的特寫鏡頭里,只因為隱現著意味深長的同情和關切而不是鄙視和仇恨,使得我們差點發生那件千百年來讓人們津津樂道經久不衰的熱門話題。
那幾乎就是在兩年前的一個中午,也就是我們車間實行承包制的那個冬季,我擱下飯碗就奔向車間。那天山道上似乎刮著大風,很大的風嗚咽著,沿路上卻有不少披棉襖著單衣的小伙子興沖沖地向煙囪和廠房的集聚地奔去。干什么去哦?干革命去。你中午不困困嗎?現在都什么年月了,革命去!革命去!人們對承包制的熱情反響我認為實在再也找不到比這更形象的別的詞兒。而創造性地運用這種說法的人也許是些曾經拖著懶洋洋的步子說過報到去下放去鍛煉去勞改去的混混們。感慨萬端伴我踏過車間大門,一件事情引起了我的好奇,卻沒有引起我的足夠重視。惹得我好奇心大發的是在一張已經風雨飄搖的計件合同承包制的布告下面立著一個火紅的人,那個穿紅色鴨絨服的人不用猜當然就是王翠花。她那樣抿著嘴唇,紅蘋果一般的手一筆一畫地在那個攤開的本子上描著什么。我走過去,她馬上就將那本子掩了起來。這使得我對她增添了一種盲目的好感和通常人們所說的對異性的神秘向往情緒。一般來說我對那些愛看書的,耍筆桿子的少女特別“感冒”,這次我也無話找話地說:“你想翻天啦怎么著?記起變天帳來了。”那女孩只有在我面前才放松的臉一紅,后來便點點頭,那雙曾是憂郁屈辱的眼睛里似乎在等待什么,而又什么也沒來得及,便又默默地走了。那豐盈窈窕的倩影叫人好懊惱好沖動。可是一想到那個什么的流言我就熊蛋了。我們畢竟是個注重名聲的國度,有時候名譽比愛情更金貴啊。不是常有人為了臉面大打出手,甚至出人命的嗎?盡管我在心里拔高她拔高她,卻經不住一句輕言慢語的襲擊。我沒法改變人們的看法。就在藥水侵蝕了王翠花悲憤的腸胃后,某些光喜歡朝那方面想的人還說她竟然能忍受無數人指指點點活了那許多日子才想到這招。她被那六個男人脫光了后,為什么就沒有想到,河里有水,坡上有繩子嘛。他們感到奇怪。只有我知道她并不是為那件事而質本潔來還潔去的,直覺告訴我,她之所以在部長要來時那樣做,和我是有某種背景的,這就是我要向部長說的那件事。
很明顯,關子應該在此打住了。我知道過分斟酌什么話該說什么話不該說就什么話也說不成。我縱然不是個頂天立地的漢子,我還是得說出來,盡管有點抖抖縮縮,用我在知青點學會的一句話叫“慌魂”了。
如果不算犯禁的話,我得說我們有限制地罷工了,雖然按那班人的說法是曠工了或者是怠工或者是磨洋工。明擺著我們沒有組織,也沒有喊過口號宣言什么的。當然寇廠長他們知道這是怎么回事,除非白癡才裝傻。就在他們宣布從×月×日起再一次降低工時加大工作量裁減獎金(從最初的每噸鑄件70塊銳減到55塊)時,我們不干了。廠里這幫坐辦公室的真是一群毛驢子,說東的也是他們,說西的也是他們:什么獎金不封頂啦,什么調動人的積極性啦,可一看到你獎金拿得多了,就渾身不自在啦,全不提這些活是怎么干出來的。只說你錢拿多了,工時定得不合理。減減減,紅頭文件念得你一愣一愣的,猛一下人的心被減得涼了半截。他媽的,老子不干了,老子不干了。整個柴油機廠溢滿了火藥味,可是我們說不出裁減工時、壓低獎金的不合理性,誰也不敢提當初說定的合同,就是提起了誰還搞得清這合同究竟是幾年,就是合同上的簽字也是班頭或者更大的官兒替我們代勞的。都以為這是當官的事,當初就怎么不留心一下子呢?縱有一千個不情愿,還是一句話乖乖地干吧。8個小時不多不少,這就是我們一點可憐的反抗權。當然寇廠長他們是不會答應的,車間戴前進帽的費主任他們陪著笑遞著煙說著好活滿車間給我們打下手,可我們一等他們走開便扔下造型機。您想想過去的16小時現在的8小時呀,早知道這樣就是勒緊褲帶也不會沒日沒夜地玩命啦。多少次我曾想振臂一呼:弟兄們跟我找當官的論理去啊。可是我又害怕應者寥寥,我懷疑我的魄力,我在20多年的生命中連班頭這樣的銜兒也沒扛過。我決沒有以此顯示自己懷才不遇的意思。相反,我倒是覺得自己處處不如人家。連王翠花都不如。真的。當我奮力操開里三層外三層的人群進入車間辦公室時,我的臉一定和周圍的人一樣閃現著麻木關切明哲過癮的神情。盡管那個被圍觀者說出的話正是我想說又不敢說的話。為此我衷心希望王翠花能擊敗費主任,這樣我們的日子可能好過些。正因為那個敢犯上的人是王翠花,我才小心翼翼地豎起耳朵。“我對咱廠的做法有意見。”那個我渴望聽到而又被我極力壓抑在心中的聲音說。“有意見?你忘了當初我們廠發不出工資的時候啦!冠廠長不會錯。”那個我想對他板臉可又不得不對他擠出一絲笑的人說。“可你不看看大伙都沒勁了嗎?”“誰說的?過去沒獎金大伙還不是照樣干活!你們說是不是啊?”費主任的眼光瞟向我,我的眼睛無法承受掃向一邊,我聽見前排的幾個弟兄牙齒猛烈咬嚙的格嘣聲,我看見幾張憋成青紫色的臉和惶然四顧的眼睛,倒是后面有幾位哥們變著嗓子喊:“我們堅決要求履行合同。恢復70塊,打倒55。”費主任把嘴撇了撇:“站出來說嘛。”沒有人站出來。我們全都象扔掉了嘴巴挺在那里。王翠花見狀,擺擺手說:“費主任不談這些,不談這些,上次咱們車間不是和廠里訂了合同嗎?”“合同到期了。”“真的嗎?請看這是什么?”王翠花掏出一個我似曾相識的本子:“合同是5年呀,怎么兩年不到就變了呢?”“合同我們能訂也能改嘛。現在廠里形勢發生了變化,鋼材生鐵和焦炭都漲了價,合同就不興變化?”費主任也不是泥捏的。“可是可是合同當初就應料到的呀。白紙黑字白紙黑字啦好意思改嗎?”王翠花也不是吃干飯的。“聽你的還是聽冠廠長的。”費主任一臉鍋灰相:“合同是死的,人是活的嘛。”“我聽廠長的。”王翠花的回答至少不是我想象那樣的。“聽廠長的還羅唆什么?回去寫個檢查吧。”費主任習慣性地把手背起來。我一下子垮了,因為我聽見幾聲不無歹意的哄笑。卻沒想到王翠花的反問完全出人意料:“別忙,費主任。我聽廠里的,廠里聽誰的?”“笑話。廠里聽誰的,還用得著我來說?丫頭,別胡攪蠻纏了,快去把檢查寫出來,認識要深刻一點。”“這個檢查我寫不好,因為有一條我沒法寫,我究竟違抗了哪一級的指示精神啦。我不知道廠里該聽誰的,無法上綱上線。所以,費主任您還是得告訴我廠里聽誰的。”“唉!你這個娃娃呀真不聽話,廠里聽誰的,不是聽局里的嗎?局里呢,聽部里的,部里呢聽中央的嘛。聽清楚了吧,快去寫檢查吧。”轟的一聲大伙全笑了,那笑聲空空的聽來特別刺耳,看樣子王翠花這個檢查是非寫不可了。圍觀的人包括我都露出快快的神色準備散去。誰知道王翠花把最厲害的一手留在了后面,這使我忍不住要喊拿啤酒瓶子。王翠花說:“大伙別散,大伙別散。”她的眼睛卻是沖著我的。“費主任我再說一句,只一句。既然廠里聽局里的,局里聽部里的,部里呢,聽中央的,那么中央再三申明現行政策15年不變,可你們呢?想想吧主任,現在還來得及。”費主任紅了臉又白了臉,又惱怒又悲傷,半晌吐不出一句話來。結果他就操起了電話。他那慌急的樣子不象是他所說的要個冠廠長反倒象要個保衛科消防隊什么的。費主任不到萬不得已從不使出他的兩大法寶:一是檢討,二是電話。每次使用總使他美滋滋地背著手在辦公室來回地走。他擱下電話,坦然直視我們的樣子,我猜他一定又得到了一個什么高招。果真他眉飛色舞地說:“冠廠長說了,改革總不是直線前進的,它總要偏離一點合同的縱坐標,不知者不罪。領頭鬧事耽誤生產的嘛……王翠花,你你是個什么東西!什么玩藝兒嘛,人家清清白白的人都規規矩矩的,而你,你抻什么頭啊?罰你三天寫檢討,寫檢查的這三天不算出勤算曠工。嘿嘿。現在不是廠長責任制嗎?冠廠長還沒有從廠長的交椅上退下來吧不是?”王翠花一下子把拳頭伸進了嘴里,紅著眼瞅了瞅我,我沒有挺身而出的姿勢,我想我大概是被那句話擊倒了還是想不出什么話來。王翠花猛地捂著臉跑了,大伙作鳥獸散,唯恐最后一個離開。后來就傳開了大家可能猜得出我卻怎么也想不到的事。
王翠花吞藥水了。
這個震駭人心的不幸選擇真不是時候。很多人嘴巴癢癢著還沒來得及張開就被部長將要到來的緊張湮沒了。
我聽到這個消息就死了娘老子一樣往醫院跑,眼淚刷刷地吞進肚里,我覺得自己是世上最不值得女人喜歡的孱頭,我狠勁掐自己的大腿和人中,但我見了她不死不活地給甩在醫院床板上靠葡萄糖維系生命的樣子又無話可說。盡管我不斷地叨咕著我們的要求是合理的,給我的破膽子打氣;我還對自己說:去吧,去握住她的手,她的憔悴并沒有什么好嚇人的,她值得你為她兩肋插刀。除了我拎來的水果,不是還有幾瓶罐頭放在她的床頭柜上嗎?但我還是沒有足夠的勇氣旗幟鮮明地站到她一邊。我只是顯得心事重重地朝她點點頭,說些好好養病之類不關痛癢的話。她瞧著我,眼淚籟籟地流濕了雪白的脖頸。“你們就會說這些嗎?”她抽抽搭搭地說:“部長來的時候部長來的時候……”她將幾張我不敢正視的紙交給我,我吱吱唔晤地說:“你聽誰說的,沒有的事,沒有的事。”一邊就將那幾張紙掖在了她的床板下。王翠花一下子止住了眼淚。她的眼睛好大好美麗,艱難地從我的身上挪向窗戶外的什么地方。我不知道我做了蠢事。我認為她在等待什么,嘴里還喃喃地說:“多么難啊多么難啊,要是能找到一個辦法……”我默默地退了出去。那個初春的黃昏多么美麗,蝴蝶的舞姿把油菜花的氣息帶進了病房里,布谷從遠近的松林里傳遞來春的呼吁;在我逃離沉重氛圍中的一剎那,身后的病房傳來一陣壓抑的哭聲。我狠狠心踉蹌著離去。
我已經無顏再敘述下面的故事。我是說王翠花在部長來的那段時間拔掉針頭,她的死將使我終身抱憾。如果我還忍辱偷生地當縮頭烏龜,我的良心將永遠得不到安寧。于是我便守株待兔地在車間花園前懷著僥幸等著部長。雖然處在悲壯之中,我還是忍不住正告自己嚴肅點,你帶著什么樣的感情談論我們的部長,我們的部長說不定抗日戰爭吃過糠,解放戰爭扛過槍呢!不過千言萬語一句話,甭管兔不兔的,只要能見到他就中。而結果呢?
那輛上海牌轎車又橫沖直撞碾在我的心坎上,象這樣漂亮的車子我們廠里還有一輛。我還沒有走到那個海瑞或包公的車前,就被一群武保人員操開了:“干什么你?你來湊什么熱鬧!”“我我我……”見到武保人員我的勇氣不翼而飛,連我自己都有點懷疑自己是否對部長圖謀不軌了。馬上我就被請進了車間政工辦公室,紅色油漆的門砰的一聲將我呼喚部長的聲音擋了回來。四月的陽光懶洋洋地照在窗外那堵落了鎖的圍墻花園里,我的命運呢?“對你這種對我們企業不忠誠的危險分子,在模擬檢查完畢之前,只好委屈你半天了。”費主任說這話的時候背著手在窗外踱來踱去,叫人突然想哭。
部長終于沒有來。柴油機廠卻得了個企業合格證書。除了兩個極端破壞分子,說不清是哪些人往上浮動了半拉一級。可王翠花在時車間的那種熱氣騰騰的局面再也沒有出現過。寇廠長他們有什么招?每天上午不到9點工人是不干活的,下午3點后,人們便三三兩兩地聚在一塊閑聊偶爾有人冷不丁說一句:“王翠花死了快半年了吧?”便有幾個人長的短的嘆幾口氣。我聽見這些便受不了,就想朝誰發泄一通。當然這只是我腦子里一廂情愿的想法,嘴往往不聽話,在需要它火山噴發的時候,它卻只能苦澀地吞咽,這樣您就不會懷疑我在鴨棚酒店里,醺醺之中的那股飄忽的思緒了。我想部長也許來過又走了。也許他曾表示過要來。忽然我又想要是他真的來了,那又怎么樣呢?!(插圖:姜吉維)
作者簡介石明華,男,1961年9月生,江漢油田技校畢業,現為江漢油田三機廠一車間開爐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