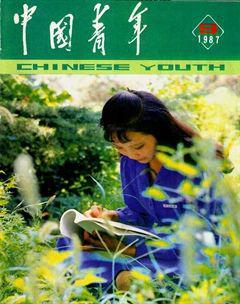創作,需要正視靈魂的勇氣
雷達
我不想故作高深地挑出幾處“不足”來顯示自己作為評論者的雍容風度。我要說,我很喜歡這篇可以稱作是“改革題材”的處女作,它絲毫沒有鉆進時下“改革文學”的模式里慘淡效顰的印痕,而是“我手寫我心,我心忠于我雙眼”,真實地敘述了“我”所在的一家工廠里,改革的實行與封建家長式的官僚主義管理相夾纏所造成的“我”和“她”(王翠花)的精神痛苦。生活既然在作者筆下是如此不加文飾地展露出來,且帶著個人獨白的不無偏執的聲音,于是便顯出一種尖銳的真實來。
我們應該注意到,這篇處女作內蘊強烈的藝術感染力,是離不開作品里那種直面靈魂的勇氣和懺悔的基調的。這是一種很有吸引力、充滿感情的調子,它時時在尋覓自我的價值,在竭盡全力試圖恢復人的尊嚴和心理的平衡。作品直接用于寫改革的筆墨并不多,只是用筆精簡地突出了那個不露面的冠廠長的封建家長式的專橫和他那句令人聞之悚然的“誰對我不仁,我就對他不義”的口頭禪,還有那個靠“一是檢討,二是電話”兩大法寶來管理工人的費主任的狐假虎威,勾勒了這個廠所謂“改革”的虛假和形式主義的表象。小說中的男女主人公生活在這樣的氛圍里,怎不感受到莫大的精神苦悶呢!這樣的氛圍必然伴隨著對人的價值的毀損和流言的滋生蔓延。年輕而果敢的女工王翠花被污言穢語包圍,就足以看出這里多么缺乏對人的尊重,多么缺乏與現代化的經濟改革相適應的精神狀態了。然而正是這個遭受名譽暗殺和輿論涂污的姑娘,竟敢于“犯上”,帶頭質問領導者違背改革精神的行徑。當然,結果是加倍的慘痛。姑娘以服毒自殺的決絕相抗爭但這依然沒有震醒顢頇的領導者和麻木茍且的“大伙”,姑娘原本還有一線生之希望,她還在渴盼“部長來的時候”。可是“我”不敢接過姑娘在病床上交出的“紙片”,這才使她真正絕望了。這一切,作品都是以“我”的反省、自譴、自剖敘述的。有覺悟才會有懺悔,作品中“我”的貫徹始終的悔恨對于提高作品的意蘊很重要。這懺悔之中萌動著對于改革中人的價值、尊嚴的呼喚,也包含著對于明哲保身的怯懦、對于寄希望于海瑞式清官的依賴心理的批評。其實,讀這樣敢于正視生命和鮮血的作品,觸發起懺悔之情的應該不限于“我”,還應該包括我們所有的人吧。所以,與其說作品寫了“改革”,不如說它寫的是不能適應改革的心理狀態,正象姑娘臨死前呼喊的:“多么難啊多么難!”
我之所以喜愛和肯定這篇尚很稚拙的初作,正是因為它以真誠的心寫了真實的人生。與此相關,它在創作上最突出的優點是,作者一開始就不肯小心翼翼地鸚鵡學舌,就不拘囚在別人鑄定的模式里,相反,筆調很自由,有自然流轉、盡情傾訴之妙。這就正象小說里有句話所說的:“我知道過分斟酌什么話該說什么話不該說就什么話也說不成。”事實上,這也就是對任何初學創作者最重要、最根本的東西:正視靈魂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