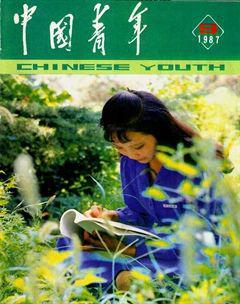野鴨子(小說)
祁述權
山溪叮叮咚咚拐進了夾香溝,清冽的溪水從鴿蛋大的卵石上滑過。蘭香把赤裸的腳浸泡在水中,半躺在草棵間,一只臂肘支托起頭,呆呆地瞅著面前的大山。
山真多,一層層似海浪從天邊拍涌而來;山也真高,一群野鴿子繞著山腰飛翔,象是山頭上有人灑下把碎紙屑,輕飄飄地在半山腰悠蕩。那鴿群飛過去又飛過來,好象總飛不出高高的大山,蘭香已經瞅著這群野鴿好久了,心想:這鴿兒真傻,飛高點兒不就越過大山了?
崖那邊傳來悠悠的山歌:“妹在河邊飲牯牛*,哥在山上打石頭喲,石頭落在牯牛背呀,看你抬頭不抬頭哎—”溝底頓時亮出女人的嗓音:“哥有心來妹有心啦,哪怕山高*水又深喲;山高那個也有人走路*,水深也有那個擺渡人嘍。”
幽幽山谷,不見人影,只有這古老動聽的山歌在回蕩。迎面山上一個攔羊的漢子遠遠地瞅著溪邊的蘭香,扯開宏厚的嗓門唱道:“哥是高山小陽雀唻,有處飛哇無處落喲;哪個小妹心眼好*,給把草來理個窩喲—”蘭香明白這調情山歌的含意,她的舌根下也有許多對應巧妙、好聽的山歌,然而此時她的心滿是凄愁,她背過身不理睬那攔羊的漢子。蘭香把手中尚未完成的繡鞋扔在一邊,揀起把石子,一顆顆朝那繡鞋砸去。
再過幾個月,蘭香就要出嫁了,但她卻絲毫沒有將要當新娘那種羞澀和興奮的心情,倒象是樁需要她付出極大犧牲的事在等待著她,她想竭力抗拒,卻又感到力不能濟。
村上幾個同時要出嫁的姑娘這半年來,把一切可以利用的空閑都花費在做鞋上。新娘要做許多鞋,男人的女人的、老人的小孩的、繡花的不繡花的、單的棉的,誰鞋做得越多,做工越細,誰就能光光鮮鮮地出門,就是山里人喜歡的能干媳婦。這是山里古老的風俗。
蘭香媽把一堆布料和一捆麻線攤放在她面前,蘭香噘起小嘴說:“媽,如今店里鞋子多著呢,各式各樣好漂亮,買幾雙穿就是,用得著花功夫自己一針一線做么?”媽用指頭點著她腦殼,說:“傻丫頭,姑娘家不會針線女紅買鞋穿,也不臉紅。這些日子地頭活你少做點吧,把鞋做好,別讓人家笑話咱們家出去的閨女粗料一根。”
結婚,嫁給山那邊的石匠哥,生娃,再就是當婆婆抱孫子,直至入土,山里女人的人生歷程就這么千篇一律,這么單調乏味。這種活法真沒勁透了。蘭香這些日子說是做鞋,可怎么也做不下去,一坐下來腦子就走神。“蘭姑娘,這么好看的繡鞋也不要啦?”一個身上沾滿煤屑的年輕漢子走到溪邊,沖著蘭香說話。
這漢子是猴子嶺小煤礦上挖煤的焦哥,他每天黃昏都要到溪邊來洗洗抹抹,蘭香認識他。蘭香心正煩,咬著唇不答理。
“你好愜意,成天兒沒事看風景。生在山里,長在山里,還沒看夠山嗎?”漢子說著趴下身,將頭悶進水,暢快地擦洗。
“閑得慌,不看山看啥咧?”
“你不會找點賺錢的營生做做?這山跑不掉,用不著你日日來看守。”“凈會挖苦人。這山里除了石頭還是石頭,能做啥咧?”“到山外去嘛,山外天地大著呢,還怕找不著事做。”“自古出門都是男人的事,哪有女人滿天下野跑的?”
“自古的東西就不能變變?我當兵的那地方,姑娘媳婦一幫幫地出門跑碼頭,比男人本事還大呢。”
“騙人。那兒的女人又沒多長顆腦瓜,就那么能?”“騙你是這個。”焦哥翹起小姆指,“喂,你想不想進城逛一逛?”
“逛縣城?不去!”
“去吧,看看熱鬧,管你比大山好看。”
“你說有啥好看的,不就是人看人嘛。”
“人看人也有看頭的,你看了準丟魂。”
“你那張嘴巴凈會吹,才不信有那么神。”“晤,我知道,你準是怕石匠哥要鬧,不、敢、去。”焦哥調笑道。“爛舌根的。”蘭香嬌叱著,撿起石子砸去,“告訴你,下次不許你在我面前提起他。”
“是是。那明兒你去不?”
蘭香一昂頭道:“去就去!”
縣城里正逢大集,人象潮水似的,買的賣的什么都有。地攤上滿是五顏六色的時髦商品:帶銅牌的牛仔褲、蝙蝠衫、太陽鏡、長筒絲襪;行道樹間拉著的繩子上懸著花花綠綠的美人畫片,閃著光的仿制項鏈,女人的乳罩和男人的領帶一同在飄舞。賣油炸干、鴨湯面、酒釀元宵、熟藕、餛飩的小食攤滿街都是。各家店鋪都開著大功率收錄機:“姑娘十八一朵花……”“你就象那冬天里的一把火……”,不是嗲聲嗲氣就是歇斯底里。臨街放錄像的更會招徠生意,分出只音箱懸在門前樹上,香港功夫片傳出的激烈打斗聲、怪叫聲讓人惶惶不安。
蘭香一下汽車,就被這一片喧鬧的氛圍緊緊包裹起來,頓時頭暈目眩、應接不暇,她沒想到山外的世界如此光怪陸離。蘭香舉著頭,左顧右盼,直愣愣的,幾次撞在別人身上。忽然,一陣香氣朝她襲來,她忙扭頭尋去,一個摩登女郎擦肩而過。那女郎著黑色健美褲,滾圓的臀部和大腿上每塊肌肉都被勾勒出來,皮靴上的鐵掌敲擊在水泥路上特別清脆。蘭香緊趕幾步追上去,人流終于把她和女郎沖散了,蘭香依然踮起腳,四下張望。
焦哥追來,抹著額上的汗:“你亂跑啥?”
“看人。”
“嘿,你不說人看人沒意思嗎?”蘭香抿嘴一笑:“凈會找碴幾。你說城里的姑娘怎么膽子那么大,只要漂亮的她就敢穿戴出來。山里的規矩太多,討厭死了,”
拐進一條小街,蘭香忽地眼亮,瞅見那女郎正提著大電喇叭,朝著街心人流喊道:“快來拍彩照唻,最新設備,價格便宜,保您滿意唻。”
“焦哥,就是這女人,多漂亮呀。”
“走,就讓她為你效勞一回,拍張彩照。”
“我不照,丑死了。”蘭香直把身子往后縮。“照吧,難得進城一趟,留個紀念。”焦哥牽著蘭香的手把她拉進小照相館。
蘭香忙問:“照一張多少錢?”
“不貴,三塊五。”
“乖乖,這么貴呀,不照。”蘭香吐著舌頭。
“如今這年頭三塊五算啥,一斤老鱉15塊,一斤螃蟹12塊,你沒算這帳。”女郎大咧咧地說。蘭香心疼錢,一個勁扯著焦哥衣角往門外拽,小聲道:“走吧,照來照去還不是這個人,能變么。”
“照吧,也是種精神享受嘛。”焦哥還是把錢交了。
蘭香被領到布景前坐下,啪,上下燈光全開亮了,光強得讓人睜不開眼,四周圍著黑壓壓的人。女郎幫她擺正了姿勢,說:“好,別動,笑笑,別板著臉兒。”
蘭香緊張得沒法笑,汗也下來了。焦哥拿起只橡皮狗沖著她一晃:“蘭香,看這個。”用勁一捏,汪嗚—,小狗叫起來。蘭香和圍觀的人全被逗笑了,女郎忙按下快門。
女郎還想繼續抓生意,說:“你們倆不來張合影嗎?我這備有時裝。”
焦哥忙搖手,蘭香騰地紅了臉。女郎笑道:“火候還沒到哇,那我不瞎摻和。這還有戲劇化妝照,姑娘你扮個花旦,手執羅扇,拍出來準跟畫上的大明星沒二樣,來一張吧,優惠價。”
“不不,不照了。”蘭香逃也似地分出人群擠出門。“城里女人真比鬼還精喲。”
焦哥剝了只蜜橘遞給她,說:“其實這女子也不是城里人,鄉下來的,她男人也是個退伍兵,會照相技術,兩口子就跑進城賺大錢,我有個戰友是她們村的。”
“你別認錯人了,她會是鄉下人,鬼聽也不信,鄉下人那有她那副打扮,那么鬼精。”
群峰被絢麗的晚霞鍍上一層金紅色,山道上拉煤的驢車隊走盡了,空蕩蕩、靜悄悄。從喧鬧的縣城歸來,蘭香突然感到這山里的世界太靜了,靜得再不象過去那么安詳、恬淡,反倒透出一種讓人憋悶的氣氛。
蘭香走不動了,兩個山頭翻得她雙腿發顫。真怪,過去挑擔草爬山穿溝全不當回事,逛趟城就變嬌了。蘭香坐在路邊一塊石頭上,捏著手絹扇風;焦哥掏出口琴,倚著顆松樹,晃著頭吹奏,一只手輕輕扇動著打復音。
“別吹了,心里真煩。”
“煩啥?”
“說不清,就是煩。”
“我倒能替你說得清,要我說不?”
“你又不是我肚里的蟲子,你能猜透?”“我要是你肚里蟲子就好嘍,可以天天時時伴著你。”
“去。那我非吃藥把你趕出來。”
“嘻嘻。”
“你是一心要出山了?”
“嗯。挖煤攢夠了錢我就出去,好幾個戰友退伍回去后都發了,辦廠的辦廠,開公司的開公司,氣派、雄心大著呢,我也要干它一場。”
“我要是男的多好。”
“女的也能行,今天那個照相的女子你不是見著了,關鍵在于自己。”
“唉,我不成。”蘭香嘆了口氣。
“你愿在這山里悶一輩子,守著碟大的天過日子?”
“不愿又怎樣?誰讓咱生在這山溝溝里。”
焦哥不吱聲,摸出根煙悶抽。蘭香雙手托著圓腮,凝望著山野。夕陽下,原野象一幅色彩斑斕的油畫:河流銀鏈似地灼灼閃光,田野劃出優美的曲線,淡藍色的炊煙緩緩飄動,灌木掩映的羊腸山道上,偶爾能看到騎著毛驢走娘家的小媳婦身影,叮當叮當的驢鈴聲和野雞的啼鳴,更襯托出山的空寂和曠遠。
“山里的景色真美呀!”蘭香喃喃自語。“確實美,只是美得太古老嘍。”焦哥感嘆著,“走吧。”
進城一趟回來,蘭香愈加失魂落魄,整天不言不語,吃飯干活老走神。她時時感到有一種無形的東西在內心拱動,在強烈地擠迫著她的心神,令她浮躁不安。
這天,石匠哥吭哧吭哧挑著副石門檻來到蘭香家,汗水浸透了衣,緊貼在栗子般的肌肉上。蘭香媽忙把他拉進屋,捧過茶,心疼地說:“哎呀呀,這么遠的山道累壞了吧,又不等著用,你急啥。”蘭香爸咬著煙桿,蹲下身,細瞇起眼,瞅著石檻上鑿出的精美花紋,直點著頭:“晤,好手藝,真真不賴呀。”石匠哥咧著寬厚的嘴巴嗬嗬憨笑。
媽媽喊道:“蘭子,躲在屋里做啥呀,還不快出來見見你石匠哥。”蘭香懶懶地出了閨房,媽又說:“下碗蛋面,瞧你石匠哥累的。”蘭香默默地坐到灶下燒火,家里人都悄然隱去,屋里只剩下他們倆。
石匠哥走過去,從腰帶中摳出個小布包,抖開,拿出20塊錢,說:“我媽讓我給你拿著買件衣裳穿。”蘭香看也沒看,說:“我不缺衣穿,這錢你收著吧。”
“那就買點別的也好。聽說你和人家進了趟城,又照相又看電影,你拿著這錢日后自個玩去吧。”
“我愿和誰玩就和誰玩,不用人多嘴多舌。”
“這錢你好歹拿著。”
“不要。你只會塞錢,就不知道怎樣替我花?”“那明天我也帶你去逛趟城,你說啥好我就買啥,行不?”
“我不想去。”
石匠哥無話可言,悶悶坐著。
“你家里都還好么?”
“好。新房蓋起來了,家具料也備齊了,欄里兩頭豬長得滾肥滾肥,結婚辦席足夠吃了。”
“你不能說點別的?”“別的,別的。”石匠哥搔搔腦勺苦思,說:“哎,我有個在外面做事的親戚,前兒來信說要介紹我去參加啥古建筑隊,家里人說啥也不干。”
“那你自己嘞?”“我也不想去,山里活計都做不完還跑那么老遠做啥。”
“我看就該去,長長見識多好。”
“在家總比出門好,再說山里人老實巴交的,比不得城里人尖頭滑腦,終是要吃虧的。”
“沒出息話,你出過山么?”
“出山不就是為了多撈幾個錢,我一把錘子敲打敲打夠一家吃喝了。”
“唉—”蘭香長嘆一聲,把蛋面盛上,說:“你慢慢吃吧。”她便拿了鞋朝溪頭走去。
山野的夜格外寂靜,迷朦的月光勾勒出大山那黑魆魆的身影。山村人家早早入睡了,沒有一星燈光,沒有一絲聲響。
蘭香慌慌張張地逃出家,焦哥在山口等著她。山風獵獵,夜貓子哭似地長嚎,亂石如怪獸匍伏在前邊,驚慌失措的蘭香走不到幾步就摔倒,臂肘和膝蓋都被石子扎破了,她真恨自己走得太慢。幸好離山口不遠了,她站定,掠掠零亂的頭發,抻平衣服,平靜一下狂跳的心,一回頭,猛見得背后火把搖晃,哭聲動地。不好,家里人追來了,蘭香趕緊跑,腳下的山道忽而變得陡直陡直,一邁步就朝下滑,急得她大汗淋淋。媽媽撲上來,一把摟緊她的腿,哭道:“你這丫頭怎么這般糊涂哇,你讓我日后有啥臉見人啦,作孽的。”爸跑急了,佝僂著干瘦的身子猛烈地咳嗽,臉漲得紫紅紫紅,頓足道:“你,你聽那壞小子糊弄,你當山外遍地是黃金就等你去撿么?過去出山謀生都是些混不下去的人,如今日子多好,你中了哪門子邪喲。”石匠哥也光著腳板喘吁吁地跑來,遠遠地就喊開:“蘭香,你不能走,不能走哇。”四面的大山一齊朝蘭香圍合而來,越圍越小,形成一口深不可測的枯井,蘭香哭著大呼:“焦哥快來救我,焦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