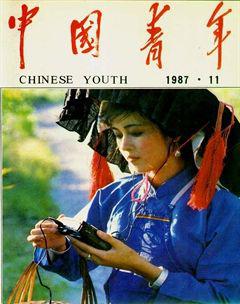尋找精神家園(報告文學)
魯娃
在樂清灣那塊神奇的土地上,我結識了三位年輕的朋友,三位腰纏萬貫的專業戶。他們是農民的后裔。是自然經濟的溫床孕育,商品經濟的血液催生,在溫州模式中直立、亮相的新一代群體的佼佼者。他們憑借著溫州人的膽氣、狡黠和變革精神,步出了貧窮的泥潭,開墾著精神的蠻荒。
他們都還年輕。這年輕使他們充滿了人格的魅力。我試圖去理解他們,用同齡人平等的心,而不是記者審視的眼睛。于是,我不僅看到了他們外在的形象,同時也看到了他們內心的顫動、困惑和迷亂。
困惑——我非財奴的超越和菩提書屋的嘆息
徐元芳是一個26歲的后生。小個子,不帥也不起眼。但在萬岙鄉卻很矚目,常被作為一種現象展覽在各種探究的目光之下。
他經營五金電器產品已有整整6個年頭。名片上的頭銜也隨著歲月的更迭而不斷變換:農民推銷員,專業戶主,供銷科長、合資廠長……在貧富坐標的兩極,他滑翔得十分出色。出色得令人妒忌!
自然,他很有錢。10萬?20萬?抑或更多。這是他的秘密。這個秘密在他與眾人之間壘筑了一道無形的高墻。但再厚實再堅固的高墻也有可能出現豁口。那豁口便是他的菩提書屋
菩提書屋?濃厚的宗教色彩,大徹大悟的情緒。
他其實遠未大徹大悟。
數萬元的造價,換回了他萬岙鄉房屋之最的那份炫耀那份虛榮。四間五層樓,墻面馬賽克,內壁三合板,要多氣派有多氣派。菩提書屋矗立在這氣派的頂端。墨綠的地毯墨綠的窗簾映襯著茶色的天穹茶色的四壁,使35平方米的空間顯得幽暗、凝重而不再寬敞。整齊排列的3000冊書籍,在占據了兩墻所有空間的5個大書櫥的玻璃門后沉默著,矜持而神圣。一張別出心裁的丁字形大寫字臺,懸立于房間中央,象是一艘泊在綠海洋上的古船。室內雖然不乏現代化的裝置:電話,計算器,對講機,但仍然顯得蒼老古樸。
如何解釋這種悖逆呢?我驚異地發現,凌駕于菩提書屋之上的竟是一居佛堂。很小,氣氛卻很濃郁。燭光灼灼,香煙裊裊。只是,寄寓神*的觀世音菩薩,臉上竟有淡淡的凄惘淡淡的倦怠。這是徐元芳父母的精神家園。披晨曦,戴星月,他們日復一日地在此念佛涌經。那篤實,那虔誠,那執拗,使原本極為空洞的木魚聲也充滿了激情。
不奇怪的。兩位老人的姻緣便是佛所締造。一是出家和尚,一是忠實佛徒,廟宇間相識、相知并相好。38歲的和尚脫下袈裟,摟著女人還俗了。于是就有了元芳,有了這個人性的戰利品,褻瀆神靈的孽種。父母的驕傲意識和懺悔心理矛盾地統一在他的血肉之軀中。
他長大。做慣和尚的父親沒有求生本領,貧寒的家就靠母親瘦弱的肩膀支撐。含辛茹苦,母親用番薯絲、咸菜湯還有望子成龍的信念喂養他。母親一字不識,卻用砍柴換來的血汗錢為他爭得學校的一張課桌。一年兩度繳納學費,角票、硬幣湊得齊齊整整,母親卻幾番餓得昏死過去。他因此學得很刻苦,從小學到高中始終名列前茅。他想出人頭地,給母親一份報償。
后來,他當兵了。
后來,他復員了。后來,他就成了溫州10萬供銷大軍中出類拔萃的一員。
原以為,出類拔萃是個迷人的字眼,可一旦落到頭上,感覺并非那么單純。炫耀拌著失落,熱鬧拌著孤獨,甜酸苦辣全有了。閑下來,坐在菩提書屋那張古船般的寫字臺前,他總覺得象在夢中,一會兒天上,一會兒地下,落不到實處。看書、寫東西根本成了一種奢望,書屋也成了一種擺設,文明的擺設!
怎么辦?
走出菩提書屋。走出!
他來到“五一”節的陽光下。
排列,組合。觸目驚心的摩托車方陣!城關鎮人民橋在國際勞動節的早晨展示了這個奇異的景象。回答是驕傲的:摩托車協會的第一次活動。越野賽。目的地:雁蕩山。富裕的展覽,激情的渲泄。
社會心理也隨之本能地顫動起來。
徐元芳殿后。民間摩托車協會副會長在菩提書屋策劃了這次行動,為的是向社會心理挑戰,向自身的困惑挑戰。陽光融融地照著,他心里一片明亮。
正是春耕季節。無數雙泥腿跨過田埂,擁聚到公路邊,目不轉睛地瞪著流星般閃過的馬達的轟響。手里是未插的青苗,臉上是驚詫,是歆羨,是勃動的妒忌和勃動的超越感。
越野賽結束。人民橋畔又聚集起觸目驚心的摩托車方陣。回歸的方陣。徐元芳倚著自己那輛火紅的鈴木,以副會長的名義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講。
他突然感到底氣不足。他看到父親站在陰影里。
鐵窗是陰影涵蓋的世界。父親剛從鐵窗里走出來。33天囚牢生活源出于罪惡的金融大地震—抬會案的牽連。可他們一家并未參加“抬會”。自己是騙不了自己的。但是,那么氣派的房子,那么多錢,從哪來的?不是響當當的赤貧嗎,怎么轉瞬間變為響當當的豪富?這是三中全會政策帶來的吉兆祥云……他想說未來得及說,便被推進死一般的陰影。
這也是一種社會心理嗎?
他有了一種參悟。摩托車越野賽使他對社會心理折射出來的陽光和陰影有了一種深刻的參悟。自主意識和抵抗意識由此*入他的整體思維。在菩提書屋被騷擾的困惑發酵為打入上層、搏擊世態的強烈的欲望。
文學是敲門磚。
他回到菩提書屋。高懸起直言不諱的宣言—我非財奴。四個古樸典雅的篆字飽蘸濃墨鑲嵌在鏡框里,似向世人袒露他自身駕馭的決心。
他一氣訂了16份報紙,29種雜志。《光明日報》《文藝報》《世界經濟導報》《中國文化報》《人民文學》《文學評論》《中國青年》等等,數量之多,檔次之高,使每天踏著車輪而來的郵遞員忍不住發向:“這么多,這么深奧,讀得懂,讀得完嗎?”讀!他擠壓時間,克服惰性,甚至殫精竭慮,象吞咽苦果,但最終總難奏效。
他還參加了分布在全國各地的10家文學雜志社的函授。學費水樣地流出去,教材潮一般涌進來,收效仍然甚微。天知道是漂泊的生活方式所累還是心猿意馬的精神狀態所致。
不過,他還是勇敢而羞澀地步入區縣文化圈。一個20多歲的專業戶,一手捧著服兵役時寫下的長篇手稿,一手攥著“大團結”,敲開文化館的犬門,要求自費出書……這細節不加演繹不用渲染就有了幾分奇特。在一次業余作者座談會上,他慷慨地散發“中華”煙,帶著金錢啟動的自尊和文化積淀的自卑。會議很短,他回家卻激動了整整一夜。你被認可了嗎?
一些表象給了他肯定的回答。
菩提書屋變得門庭若市了。作家、導演、記者、文化干部來來去去,絡繹不絕。喝口清茶,飲杯薄酒,抑或海闊天空地神聊一番,然后留下一串贊語,一片溫熱,一段友情……
但是作品呢?認可的實質在于作品。這一點后來他意識到了。便寫。絞了幾多腦汁,撕了幾多稿紙,他終于使自己的一篇小文變成了上海《解放日報》上的宋體字。好累呀!他于是由衷地感嘆:賺一萬元,發一篇小說,他寧要后者!
戲言歸戲言。錢仍然流進來,小說卻再也寫不出。自我駕馭的羅盤難能把握,他很是懊喪。恰在此時,一張登記表翩然而至,象帶來吉祥的光環。他精神頓覺抖擻起來。溫州市文協會員申請登記表,夢寐以求啊!坐在菩提書屋那艘“古船”前,他抑制著急速搏動的心律,一筆一畫地填寫那張表格。一邊填,一邊看墻上的“我非財奴”,忍不住得意地笑。
笑后,筆卻凝住了。曾經發過哪些作品?除了《解放日報》的小小說《平衡》,再沒有值得一書的文績。他覺出了自己的窘迫,覺出了與表格的難副其實。
不錯,表格是文協通過正常渠道發下來的。可誰能斷定這降格接納里面沒有對他專業戶身分的寬容和恩賜?
表格搖動起來,那一條分割欄目的縱線和橫線利箭似地從紙上射出來,刺激著大腦的敏感圈。他渾身燥熱起來。這是一種不平等,一種居高臨下。他不要!
他愣著。然后開始一下一下地撕那薄薄的表格。一陣風從窗欞里吹進來,卷起紙的碎片,飛飛揚揚。他吁了口氣,疲倦地靠在了椅背上。心里則恨恨道:“我要來真格的。我要名副其實!”
可是,在大把大把賺錢,大把大把花錢的同時,他能坐下來嗎?他能寫出真正的作品嗎?他能實現自我駕馭嗎?
他其實已超越了自己。但他未能意識到。
那是因為,新的困惑又裹住了他。
迷亂—鋼琴曲的華彩樂章與不諧和音
晚霞火一樣地燃燒。
琴鍵上跳著華麗的光暈。這光暈安撫著鄭樂林叩在琴鍵上怯生生的手指,驅逐著生疏感,四鄰五舍,親朋好友,嘖嘖喟嘆之后都散去了,帶著十分的好奇與十分的不解。只留下他一個人,還有這架剛運來的鋼琴。柳市雖屬名聞遐邇的富裕之鄉,鋼琴仍是不速之客。今天,曾經當過樂器修理匠、五金電器小店主,如今是家庭塑料制品廠主宰的鄭樂林,卻用幾撂“大團結”把它請進了家門。
為此,不到30的鄭樂林頗為自負。他倚著烏黑發亮的新鋼琴對朋友們說:“我小時候常常做夢,夢見自己當了音樂家。可夢醒來,什么都沒有,就十分沮喪。買了鋼琴,我覺得那個夢想突然變真切了。哥們,信嗎?我或許會成為柳市的肖邦,樂清的貝多芬呢!”
朋友們沒有異議。在他們的概念里,擁有了樂器之王鋼琴,便等于擁有了音樂。這是富起來的農民在音樂啟蒙階段的認識。
鄭樂林早走了一步。初中畢業,他不愿捏鋤頭下田垟,就跟溫州師傅學了手藝,在家里掛了塊“修理樂器”的小招牌。他有心計,討口飯吃的同時,沒忘了捎帶著給自己的夢想一點滋補。云游于樂清境內,幾百架廢棄的鋼琴死而復生了;大提琴、小提琴演奏法的ABC也掌握了,雖算不得上乘,在對音樂隔膜的鎮民眼里,也已有了炫目的光彩。
但他自己不滿足,兒時的夢想時時誘惑著他。有了錢后,他幾乎是條件反射似的想到了樂器之王。果然,鋼琴給他帶來了殊榮。那殊榮就象琴鍵上晚霞折射的光暈,使他的心境寬敞起來。鋼琴還給他帶來了熱鬧。他和他的朋友們想讓這熱鬧持續下去,使為之取了個堂而皇之的名字:柳市青年音樂聯誼會。這是一,個松散的、自娛型的民間社團。清一色的青年,清一色的音樂愛好者。賺錢和花錢的不滿足感是他們集聚的內驅力,音符—哆唻咪發嗦啦西則是他們凝結的鏈條。彈奏歌唱,他們好生繁忙好生痛快。自然、他們的繁忙他們的痛快還不可能進入審美層次,但從不會玩到玩得高雅,不也是一種進步?他們自我感覺良好。
因為誕生在柳市的土壤上,因為大多數成員手中都攥有小小的搖錢樹,聯誼會也閃耀著金錢誘人的光澤。大提琴、小提琴、手風琴、電子琴,琵琶、二胡、揚琴,還有爵士鼓、鋼琴;還有七七八八的管樂器。價值逾2萬的樂器在手中撥弄,連心態也會富足起來。鄭樂林呢?除了鋼琴、手風琴,還有6把提琴外加一副男中音的歌喉。是首富!
幸福的聯誼會!
只是,鋼琴被冷落了—誰也不會彈。它成了幸福的聯誼會中不幸的裝潢。
鄭樂林坐在這“裝潢”前發起呆來。叩擊琴鍵,他的手指仍是生疏而笨拙的。他曾試圖駕馭鋼琴,最終失望了。缺少天賦,缺少素養,缺少韌勁,缺少左右不旁顧的一意孤行,還缺少……對音樂的真正理解。
認識自己,尤其是認識自己不那么愿意認識的弱點是痛苦的。但他直面了這痛苦。一番反思之后,他把小妹鄭別雷接到了自己的家。
他所匿乏的小妹恰恰富有:高中畢業,賦閑在家,癡迷地戀著音樂,愿一輩子與音樂為友。在她身上轉嫁自己的音樂之夢,該是合理的選擇。
一間清雅的琴房騰出來了。一張小床,一張小桌,鋼琴貼著墻壁,書架倚著窗臺。在樂音的顫動中,他獲得了補償和充實。不彈琴時,哥哥便領著小妹,尋訪溫州的各路名師。雖然此時妹妹已有一手不錯的琴技,但高貴的音樂圈仍對他們顯露出淡然和冷漠。哥哥急了,同時用出兩手,一手捧著金錢,一手捧著誠心,硬是幫小妹敲開了殿堂的大門。兩個人的汗水,兩個人的苦心,兩個人的夢縈魂牽喂養和滋潤著音樂這個精靈,它在琴鍵上的徜徉瀟灑自如了。
妹妹為此有了小小的得意。哥哥卻以為遠未到笑的時候。藝術若滿足于普及、自娛而不思提高,不思步入審美層次便注定會滑坡。他于是拿出一筆數目可觀的人民幣,自費送小妹到省城某藝術團體進修。4個月后,妹妹笑盈盈地回來了。一曲叮叮咚咚、**瓊瓊的琴聲把一個走向成熟的音樂世界推到他前面。他于是笑了,笑得愜意,笑得滿足。他真想抱住小妹,親親她嬌羞的臉蛋。
可是,小妹卻對他說了一句他做夢也想不到的話語:“哥,我要走了,到市歌舞團彈琴去。柳市太小了,沒有知音。”
他懵了,好半天才說:“哥不是你的知音?”
“當然是。”小妹不敢看哥哥的眼睛,囁嚅道:“可我還需要能幫我提高的知音。我要一個充滿音符充滿琴聲的音樂環境。哥哥,你沒有!”
“是啊,我沒有……”一聲沉重的蒼涼的嘆息。
小妹明亮的眼睛濕潤了:“哥,別難過,我會常常想著你。”
他不愿意對整個人生厭倦。這就需要尋找新的支撐點。他苦苦尋找,茫然之中發現了當今青年生活的一個熱點:攝影!這個發現使他有了柳暗花明之感。他幾乎連想也來不及想就把它緊緊拽住了。
他買了高級相機,拍下了一系列實驗性的作品。沒多久,他又運籌帷幄,開始籌建柳市青年攝影學會。后來,學會誕生了。聽說他還當了會長。他又變得躊躇滿志。
無疑,這是他的選擇。然而這選擇,究竟是自我的超越還是追求的迷亂?悲乎?幸乎?
揚棄——人生底片的多次曝光和多次顯影
掌聲轟鳴中,陳志賢從臺上走下來。“先進供銷員”燙金的大字明晃晃的,在手中高擎的鏡框里閃著迷人的光。他似乎應該激動,卻沒能激動起來。自1975年始,他便在“供銷大軍”的小氣候中呼吸。整整10年,他有些膩了。人一輩子有幾個10年,不多嘗嘗別樣的滋味,這世界不是白來一遭了?!他徑自回家了。
他的家很豪華,象一座小別墅。高中輟學后,他不愿象父輩那樣依傍土地pian手zhi足,跟人學了泥水粗活和建筑設計。這幢樓房是他的“畢業論文”,是自認的杰作。在這個杰作的整體中,他尤其喜愛“健身房”這個局部。一位劇作家、電影導演參觀了“杰作”之后感慨:“我跑了全國那么多地方,私人有健身房的實在還未看到,這表明溫州新一代農民的追求已進入全方位……”他曾為此津津樂道。可是今天,當他捧著獎狀進入健身房時,往日的那種得意倏忽間不見了。不是說他們是全新意義的農民嗎,追求難道不應多向、多元、多律?健身房算什么全方位?!
妻輕聲走進來。一身素裝,發髻高綰。基督教徒的她漫不經心地對他說起他一個供銷員朋友的事。他其實已經聽說了。這位朋友原是極其聰明極其干練的小伙子,跑供銷象是得天獨厚,游刃有余,順利得叫人妒忌。可他,賺錢花錢覺得無聊了,就想尋些刺激,一頭闖進賭場的門,原想過過癮,不料一發而不可收。轉瞬間,沒弄明白是怎么回事,9萬元賭注全落了水。人也陷入沼澤自拔無力了。
“該死!”陳志賢一拳砸在大腿上,為朋友叫苦不迭。
“還有呢!”妻又說,“聽人講,查出好些重婚的,要判刑呢!據說都是有錢的……”
他沒響,抬眼看著妻的臉。這類傳聞甚至這類事實在柳市都已沒什么希奇,他奇怪的是妻為何要把這些事攪在一起正兒八經地告訴他。
“想來是活得太乏味了。沒有精神上的寄托……”
他旋即明白了。妻是在轉彎抹角地勸唆他入教呢。她在這個家庭里原是“隨你”的角色,唯在信仰上執拗得令人嘆服。她祈望丈夫也能人教,日后便可雙雙步入天堂。但陳志賢不買帳,無論是上帝的旨意還是妻子的意愿。人都死了,一切也就無所謂了。他只是想活得好一些,充實一些。
一個潛伏已久的想法,經過表彰會和妻子陰差陽錯地點撥、發酵和催化,突然間成熟了。他“嗖”地一跳,攀上高懸的吊環,做了個優美的姿勢,用調侃的語氣說:“你放心吧,我不會讓精神的領地空閑著的。”
幾天以后,一紙“謝絕參觀”的布告在他那幢別致的小洋樓門上貼了出來。登門造訪的人們,聯系業務,采訪參觀,訂購產品,還有猜拳喝酒的,來了,又去了。吃了閉門羹卻最終也沒弄明白陳志賢這小子葫蘆里賣的什么藥。
他不解釋。好象是來不及解釋。一個鼓鼓囊囊的攝影包斜挎在身上,里面裝著價值幾萬元的高級照相器材。“鈴木”一聲長嘯,載著他流星趕月般飛馳而去。
他的選擇令人瞠目結舌。停了業務,撂下大把的鈔票不去賺,偏要玩什么攝影,整天東奔西顛,蹶屁股,瞇縫眼,拿人民幣打水漂漂,買疲勞,這是中的哪門子邪?
他答話了。言語里有幾分揶揄幾分炫耀:“賺錢我膩了,供銷員的頭銜我也膩了。我想換換骷髏。照文化人的時髦說法,叫做塑造新的形象。”說著,勃勃的英氣在臉上蕩漾開來:“我要在溫州的攝影圈里樹起陳志賢的旗幟!”
他完全改變了舊有的生活方式。安逸和享樂遠去了。馬不停蹄的奔跑中,他印下深深淺淺的屐履,載回五彩繽紛的生相圈。攝影具象的形態在他的相機里一次又一次曝光,他自身的心態也在人生的大鏡頭里一次又一次曝光。滿足之后的不滿足紛至沓來。角度不準確,構圖不新穎,意境不深遠……文化的貧血給他的作品和他勃勃的野心設置了種種缺憾。為了彌補,他訂了16份報紙,37份雜志,并從各條渠道購置了有關繪畫、書法、攝影等種類繁多的專業書籍和精美畫冊。他還幾經輾轉,從黑市高價購置了一套美國出版的攝影教材錄相片,整夜整夜地觀摩。他還四處拜師求教。溫州攝影界在全國都是一支不容輕視的隊伍。榮獲全國級殊榮的作品和作者都不是鳳毛麟角。但他憑了韌性闖了進去,又憑了謙遜為之接納。他而且還十分刻苦。酷暑,暗房就象封閉的地獄。但他的狠勁兒上來,便常常在這地獄里一呆就是十來個小時。出來時,臉上的五官似乎都變了形,整個模樣真象是煉獄里廝殺出來的再生之人。
他果然再生了嗎?
他覺得了一絲悲哀。柳市人的悲哀。柳市,是溫州模式的前沿,商品經濟的敏感區,是新聞界和民眾關注的“熱點”。幾年來,柳市每一根神經的顫動,都在報端的字里行間披露。可是,柳市的“清明上河圖”呢?柳市人臉上的喜怒哀樂呢?直觀的形象,形象的氛圍呢?為什么如此之少?答案極為簡單:缺少攝影機后面的灼灼慧眼!
陳志賢感到芒刺在背。其實,當全國各地來參觀學習的人們索要形象的照片時,攤攤手,聳聳肩,表示一下遺憾抑或愛莫能助也就過去了。政府官員都如此。他偏不。于是便生出越俎代庖的煩惱。
或許,這也是時代賦予的情感。畢竟,他不再等同于他的父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囿于封閉的一隅,不問天下紛繁的沉浮。畢竟,走出田野,步入商品世界,不僅僅是換一方人生角逐的舞臺。有了溫飽,有了金錢之后,人變跪著為直立,尊嚴抬頭了,自主意識蘇醒了。他感到自己不再是單個的人,而是群體中的分子。就加大海中的一滴水,天體中的一顆星。他屬于柳市,柳市也屬于他。他有責任為柳市的興衰喜悅和擔憂。很難說清楚這是第三代農民的新集體主義、現代人的社會責任感,還是自我意識涵蓋下的帶有功利目的的新的行為準則。
他不再拍晨曦落日、花花草草,而把攝影的焦點對準柳市層出不窮的心浪和旋渦,捕捉文明妊娠期的每一次脈動和每一次痙攣。他干得很苦。沒有信息網,沒有新聞渠道,官方又不愿為他提供途徑,他只能從報紙、廣播、電視抑或街談巷議中搜尋線索,然后跟蹤追擊,苦心炮制。花自己的錢買膠卷,吃自己的飯使氣力,卻還常遭側目、冷遇、嘲諷,甚至閉門羹、逐客令。有時奔波一日,躺在床上困乏地喘息,真想立即甩手不干。可天明一覺醒來,陽光把整個世界照得通亮,他便又會忘記一切,開起“鈴木”興趣盎然地上路。攝影包斜挎著,任陽光在上面紡著金錢。
報償并不姍姍來遲。很快,柳市的形象疊印著他的名字走向《溫州日報》《浙江日報》《新民晚報》《人民日報》。照片很多,使同行不得不刮目相看。他于是覺得獲取了一種榮耀,一種在社會上挺起來的榮耀。在此之前,他雖然有錢,卻沒有這種榮耀。
……掌聲轟鳴中,他又向臺上走去。這一回他不再是供銷員,而是“攝影家”。在溫州市青年攝影佼佼者大獎賽中,他的彩色作品《歲月、人生》獲得了三等獎,是溫州市所屬9縣作者中唯一的獲獎者。他甩著有力的臂膀,頗有些春風得意地向臺上走去。時時向左右鼓掌的人們矜持地點頭矜持地笑,他很看重這個榮譽。
可當他捧回金燦燦的獎證,從臺上下來的時候,臉上卻多了一層隱隱的惆悵隱隱的憂郁。是因為對歲月、人生再思考觸發的失落感嗎?也許是。也許不全是。
他們—徐元芳、鄭樂林、陳志賢就是這樣在走著屬于自己的人生之路。他們走得不輕松,甚至很累,很艱難。但他們無疑是會一鼓作氣走到底的。就象夸父逐日,在燦爛的金輝中,化為一片鄧林……
迎接文明的到來,是需要血與火的洗禮,需要整整一代甚至幾代人付出代價的。這代價,也包括了徐元芳的困惑、鄭樂林的迷亂,陳志賢的摭拾和失落……
(圖:梁照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