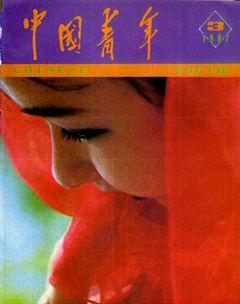那個元旦(小說)
候榕平
那個美麗的元旦!
那個美麗的元旦晚會!
現在我說它“美麗”——任何一件關于少年時代的記憶,日久天長地就變美麗了,美麗得令人向往起來——可當時,情形又是怎樣的不“美麗”呀……我的話越來越少,低著頭默默地嗑瓜子,任憑耳旁的歡聲笑語怎樣誘人,任憑教室中央那些節目怎樣逗人笑。我生氣了,你并不知道為什么。“你怎么可能知道呢?”當你輕盈地鼓著掌,和周圍的同學開玩笑時,我難過又憤憤地想著,也許你深知我的脾氣乖戾,常常“莫名其妙”地生氣,你一直沒跟我說話。
那段“迎新詞”——寫完后被朋友們由衷贊揚的迎新詞,激動人心的迎新詞,鏗鏘有力的迎新詞——竟被晚會的節目主持人念得結結巴巴,令人掃興……
“你怎么了?”你終于輕聲問我。
我歪歪身子,不說話。
我的情緒壞了下來。真正壞了,反倒忘了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了。此刻,你的笑聲和說話聲,象馬蜂一樣刺著我。我低著頭,瞥見你的腿——筆直地伸著,左腳輕輕擱在右腳面上,輕輕地晃,那么自在那么悠閑,我感到眼淚就要流出來了。
我突然發現,我好孤獨啊!
所有的人都在說笑,所有的人都在熱烈地鼓掌,所有的人都在興趣盎然地欣賞著節目,所有的人都把我忘了……
然而,強烈的自尊心使我不能表現出悲哀,我決不能低著頭。
抬起來了,眼皮那么沉。看著教室中央一個同學唱歌。“張牙舞爪的!”我想著,傲然地瞥著周圍的人。他們在傳一個本子,寫著留言。
本子傳到我的面前。我提起筆,想了想又放下了,把它推給旁邊的你。你看了我一眼,好象說了句什么,我沒聽清。我轉頭望著窗,可見遠處燈火通明的白塔、烏塔,和山上隱約明滅的燈。夜沉沉的,不時傳來鞭炮聲響。
你被叫上去唱歌。我看到那個小本子還在你的桌上,不禁又拿了過來,一打開,一張紙飄了下來。那么熟悉的紙,紙上那么熟悉的字!我驚呆了,這不是中秋節我贈給你的詩嗎?我感到血往上涌,腦袋嗡嗡作響,天!剛才,這張紙,夾在這個本子里,傳遍了全班!我看著紙上傻乎乎的我的名字,真想吞下去,而那首詩,又寫得那么蠢!想起了剛才,啊,難怪他們要朝我看了,還指指點點,嘻嘻傻笑……
你回來了,看到我手里的東西,看到我憤怒的目光,呆住了。好一陣子,你誠懇又莊重地把手搭在我的肩上,說:“真對不起!”
我扭過頭,淚水在我的眼里打轉。你說著寬慰我的話,但我始終無法從極度的憤怒中緩和過來。
算了吧,我不愿意聽!我在心里說。我的怒火劈里啪啦地在心里燒。
話筒伸到我面前,漂亮雅致,閃著光,帶著誘惑力。
要我表演節目?我站起來,看著節目主持人。不知他 說了什么,忽然響起掌聲,旁邊的你拍得最響。
我要承認我是很壞的人。我笑了,把《雪萊詩選》拿出來,說:“我朗誦一首雪萊的詩吧。”
我頓了頓,一本正經地念起來:
一個懷恨在心的人來到溝旁坐下
他抱著一把老舊破損的琵琶
他唱了一首歌,其實更象是
對一個下流潑婦的尖聲叫罵……
完了。坐下。我輕松地看看四周。
然而,一個更大的更沉重的包袱立刻向我撲來了—剛才,又做了一件愚蠢的事!我為什么要這樣?我有什么權利去破壞別人的興致以發泄內心的憤怒?!
我好難過!
你不再說笑了,只靜靜地坐著,靠著椅子后面的墻。
誰知道,這一切是為了什么!“老天,我究竟怎么得罪你了,你這樣跟我過不去?”我無力地在心里叫著。我強烈地感到,這是一個十分不愉快的晚上。
中間歇息時,我跑了出來,到五樓去了。那里幽靜、冷落,沒有班級開什么晚會。晚會—讓人詛咒的晚會!我低著頭,雙手插在衣兜里,踱到走廊盡頭。那兒有個小小的轉彎,我縮在彎里,背后的墻堅硬地抵著我,左邊的欄桿堅硬地抵著我,我覺得很安全!
很冷。但很自由很空闊很輕松。所有的剛才的不快在冷風里沉浸著,旋轉著,又被風拉扯散了。我望著遠處的白塔、烏塔,身著熾亮的、珍珠一般的燈,喜氣洋洋地挺立在霓虹燈明滅的黑暗中,啊,它們也過年了。我猛地清晰地發現—今天是元旦!我又大了一歲!鼻子酸酸的,不知什么時候,眼淚流出來了。
背后突然響起輕輕柔柔的口哨聲。你來了。
不用問你是怎么找到的,不用問你怎么想得到,你知道我。朋友間從來是心心相印,言語是多余的。
你站在我身旁,不說話。曉陽,小綿羊,不要緊了,我已不生氣了,咱們隨便說說話吧。今晚多好,這么靜(純潔的靜),星星又是這么亮這么多……
我們是怎樣相識的?既然命里注定我們將成為好朋友,我們本該早就相識,不是嗎?可是,高中快一年,我還只知道,這個班,有個女孩,叫曉陽,在偷看那些交給我的作文本時,我只知道,那個字寫得輕飄飄的,老把“的”寫成“∴”的,就是曉陽。
那天,你來得很遲。站在門口,無力、脆弱,面對著四十多雙疑惑、猜忌的眼睛,又是那么滿不在乎。數學老師瞥了你一眼,示意你歸坐。課上,我忍不住回頭好幾次,看你。你的冷漠、坦然、看透一切的表情,刺激著我的好奇心。
那些關于你的傳言—關于你和那個男孩的傳言,早就聽說了,而且聽說好幾次了。我隱約覺得,今天你的遲到和它有關。下了課,我把你叫出了教室,傻乎乎地問你。
“你聽誰說的?”你冷笑了一聲,問我。
僅這一句,我便知我是怎樣傻的一個人了。連日來你不說不笑,早操也不做,作業也不交,足見你是怎樣的痛苦,而今天我還這樣……“她卑鄙得足以讓我吐血!”你還想說什么,看看我,又止住了,從我身邊走開。我愣在那兒,后悔極了,只覺得慚愧壓住了我,壓得我抬不起頭來。
有人狠狠地、親熱地推了我一把。是“她”—你剛才說的“她”,你原先的“最親密”的朋友。“她跟你說什么了?”她低聲問我,眼角瞥著你的背影。我抬起頭看著她,一句話也說不出。我皺著眉走開了。我重重地嘆了口氣,停下來,便發覺心里那一絲歉疚在長大……
可是,我們從此成了好朋友。
不知從哪個教室里,飄出深沉憂郁的《驪歌》。我輕輕隨著唱了起來,你也輕輕地用口哨和著……
我們美好的時光,我們平靜的時光,一年一年地過去了,再過七個月就要高考,就要分別,多么快呀。可是心里那份留戀卻早已牢牢地抓住了我們的心。留戀?不如說“猶豫”—對將要跨出的這一步的猶豫!因為那太多太多的問題還沒有答案,太復雜太復雜的角色,我們還不能進入!我們幾乎還是稚氣的,但我們自以為很成熟,象個神氣的孩子模仿著老氣橫秋,嘆息著:“社會多么復雜……”
那天,班主任找我談話,美麗的大眼睛里閃著狡黠的光,那意思是:“我知道是你!”
“是我!”我心里笑笑。
只一會兒,她言語里藏而不露的猛烈進攻,就把我弄哭了。
是我,寫的那封匿名信。
只因為那個跟我們毫無關系的人被她大筆一揮劃成三好生。他成績平平—常常還是那“小團體抄”的“戰果”,作業抄襲,遲到早退,我還見過他上課時大嚼油條。可他竟是“三好生”!就因為他爸爸是教育局的官兒!
“算了算了,別寫。”你滿不在乎地勸我。
“要寫,你難道不氣憤嗎?你那么寬容,那么博愛,真是高尚啊!”
“寫了又能怎樣?”你反問我。
可我還是寫了,你也不再阻攔我,而且是我的同盟,
我不后悔,至今不后悔—沒有什么東西值得我后悔。
元旦的鐘聲,從各個開著電視的屋子里傳出來,凝重而深沉。每一聲都長久地回蕩著。閉上眼,合起雙掌,祈禱一下,向這鐘聲,向這黑夜,向著我們摯愛的校園……
“又長大一歲了!”
我們同時睜開眼,同時笑起來。長大了!
可依稀仿佛,我們還是那棵黃花樹下黑板報前亂說亂笑的小丫頭……“那只老鼠好可愛呀!”我指著黑板報說。那是鼠年。
我們看著黑板報上那只肩扛一串沉甸甸鞭炮的神氣的老鼠,大笑不止,笑得彎下了腰,笑完了看,看了又笑,好幾回,才止住。“黃花樹下老鼠張牙舞爪,”你說,“快,對一個下聯。”
我們一同靜立在老鼠前,想了起來。上課鈴響了。我們跑回教室,還東張西望地想著下聯。
課上,你在活頁本的第一頁端端正正地寫下“黃花樹下老鼠張牙舞爪”,認真地想著。“比如說,一只羊換三十斤大米,這是物物交換。”政治老師說著,一本正經地在黑板上寫上:“1只羊=30斤大米”。我靈機一動,把你的活頁本挪過來,拿起鉛筆,在你的那行字下面寫起來:
黑板報前小羊喊爹叫娘
哎喲,別笑,曉陽,別笑,政治老師瞪眼了……
不知為什么會想起這些,那幾乎沒有任何意義。可是想起來了,便心酸—為什么呢?似乎世間的一切都如此,過去了的歡樂在記憶里復蘇時,總伴著傷感,因為那是過去了的,我們又處在如此多愁善感的年齡……
我們多么幼稚多么孩子氣!我們一只手撓著心上的天真,另一只手卻開始擰著眉上的成熟了。世界的不純潔,讓我們感到一種責任,我們天真地承擔著這種責任。我們常常站在教室外面的走廊上,常常跑到五樓沒人的地方,常常倚著操場跑道邊的那棵樹,無可奈何地嘆息,義憤填膺地叫喊,或者唇槍舌劍地爭吵……
那棵樹,從這里可以看到,你看見了嗎?雖然操場上沒有燈火,雖然夜是這般濃,雖然星星不向那里濺一點兒的亮光,我仍然看得見。它已脫落光了葉子,樹枝遒勁地張開。我們常常站在它下面,有時也望望它和它上面的天。它可以作證,我們的心是多么清凈無瑕。但我們的感情又是那么敏感脆弱,容不得傷害,容不得褻瀆……
那回,我們幾個三好生被叫到禮堂,聽華山搶險的報告。其余的同學坐在教室里,聽安了線的廣播。這種作法很愚蠢,我們心里都覺得不舒服。聽完,回來,教室里只剩寥寥幾人。班主任正橫眉立目地發脾氣。我們稀稀疏疏地在自己座位上坐下。
“……有的同學還可忍耐到最后,有的同學呢?”班主任瞪圓了美麗的大眼,“連一點兒的耐性都沒有!……”
我的額靠著桌沿,閉著眼,說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忍耐!”老師您用了“忍耐”這個詞!我們的心還留在剛才的崇高中,我們的情緒還不能平靜,我們那仿佛受了洗禮般的靈魂還在激動地顫抖……您對我們說的僅是這些!最后,她的火發完了,居高臨下地發著命令:“課后,班干部、三好學生,主動留下來打掃教室!一般同學也可參加!學華山見行動嘛……”
我抬起了頭。你正冷漠地靠著后排的桌子,筆直地坐著,手里漫不經心地絞著手絹,緊抿著唇。你抬起眼,朝我無可奈何地笑了一下,聳聳肩。
我們背起書包,不約而同地走出教室,走下樓。
回家嗎?
我們對視一下,想到了烏山……
我們一同向烏山跑去。那里,雜草叢生,古樹蔽日,我們都愛那兒的清靜、那兒的輕松。我們將忘掉大考、小考和測驗,忘掉成堆的作業和提綱,忘掉那些分數,忘掉那些唾沫橫飛的嘴,忘掉那雙美麗的、憤怒的眼睛以及虛偽的“主動留下”……
我們在半山腰停下,張目四望。那重重疊疊的屋頂遠處,最吸引我們目光的,仍是學校那幢白色的樓。它多么美呀,從來也沒發現它竟這樣美。它折射著耀眼的光,那光里洋溢著知識、智慧和活力,洋溢著好奇、激動和熱情……
我們說起了童年,談到了將來,話題卻回避著剛才的一幕,我們的心容不得!
旁邊的寺院不斷地傳出敲木魚的聲音,伴著唱經的聲音,空氣里隱約地飄著香火味……
這樣靜!我們似乎才注意到,一同屏息傾聽……
你長嘆了一聲:“塵世便是如此!”
“‘如此是什么?”
“紛亂,復雜。”
我望著那些青灰瓦片的屋頂,綿綿延延地伸向遠方,突然說:“假如沒有這許多紛亂、復雜,又會怎樣呢?”“真是!為什么要生下來!”你笑了,“算了,理不清!”
我也笑了。
似乎輕松了許多。但心里始終有個悲哀的聲音在喊:怎么辦?以后的路將是怎樣?我們將成為什么樣的人?……
站在這兒,南面就是烏山。看不清黑暗中的寺院,更看不清寺院旁邊的那一塊平潔的空地,站在那兒也看不清這幢白樓,更看不清白樓的第五層的這兩個女孩……但我們永遠也不會忘掉,此刻,彼時,一樣的無比迷惘、一樣的疑惑、不知答案的心情……十六七歲,幼稚和成熟在心里擠著,誰也占不了上風。帶著天真的神情,進入大人的世界。這世界不是永遠讓人滿意的。七個月以后,那罩著我們命運的面紗就要揭開了。想到它,就不由得很沉重,我真不愿再前進一步了,我害怕跌倒……
那時,該怎樣地想念你呀!那條路,常常地,你在這一端,我在那一端,在上學的路上,我們相遇。這樣的機會并不多了。不過,不管怎樣,我們同樣在人生的道路上走著,你在那一邊,我在這一邊,我們遙遙地喊一聲“哎”吧,彼此表達關懷的愛心。不管那路是怎樣的,知道有朋友在念著自己的名字,再難再累,也不孤獨,也不氣餒。你說對嗎?
我們也將忘不了這個元旦—包括那星星,那隱約可見的白云,那閃爍的燈火,那追也似地響著的鞭炮,那總也不絕于耳的大人小孩的笑聲,還有,我們自己!回吧,回教室去,繼續參加晚會,我將好好的,不再生氣了。我不再計較那段迎新詞念得結結巴巴,不再怪你粗心,不再不滿那扭扭擺擺地唱歌的同學……我們終將長大。也許,當我們又一次相遇,我們會不約而同地說:
那個美麗的元旦晚會……
那個美麗的元旦……
作者簡介侯榕平,女,1966年生于福州,現為北京商學院二年級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