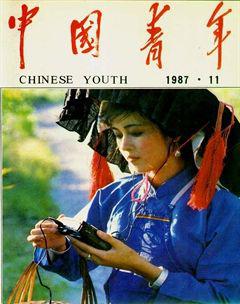灰色的年輕人(小說)
初次見面是在夏末的一天。我們下班回去,發現他在宿舍里。
“哦,你們剛下班。”他微笑著,“我是到這里住的。”
看上去他30出頭,中等個子,寬肩膀,挺壯實,一身灰色衣服,一雙方口布鞋,頭發黑中見白,面目端莊。
“聽說了,你就是辦公室新調來的吧?”
他點頭微笑,給我們讓煙對火,動作十分老練。“剛報過到,以后就請兩位老兄多加關照。”
“不敢當不敢當,老兄有30了吧?”王雷問。
“咱們差不多吧,我24。”
24歲?比我們還小?我們感到吃驚。橫看豎看,他的相貌與年齡還是不相稱。
他有些不好意思:“哦,看上去我是大了點,初次見面的時候,就有人叫我老魏。哦,我叫魏方印。”
以后我們的宿舍里就成了三個人。我在組織部。王雷在團委,他原來是學醫的,能寫會講,五四青年演講會上被團市委發現了,就調了過來。
魏方印從省師大畢業,畢業后被市委定為培養對象,在縣里鍛煉了兩年多,入了黨,現在又調上來。相處一段,覺得他跟我們很合得來。
他學的是中文,古文底子厚實,一肚皮的春秋,又象是活的辭書,常常能準確地道出一個詞句或典故的出處。生怕我們不相信,還總把書本搬出來,直到得到印證為止。
這層樓上住有不少年輕人,大都是這幾年分配來的大學生,時間長了,樓道里邋里邋遢的,誰也懶得打掃,靠樓梯還積了一大堆垃圾,方印來后就把它清除了。以后每天早起他都要把樓道打掃一遍,灑上些水,清清爽爽的。我們屋里的開水總能保證足量的供應,方印打得最勤。伙計們常常端著空杯來喊“勞駕”,“你們整天勞駕!”王雷有些不平了。方印卻總是笑臉相迎,有時還會往他們的茶杯里拈上一撮毛尖。誰要是有個頭疼腦熱的,他就會說:“又不得勁了,來,我這里有藥。”他常備有幾種普通藥,還有一支體溫表。只要有求于他,他都熱心地為你奔跑,成不成都會給你個交待,哪怕是極小的一件事情。
大家都樂意接近他,有了什么好吃的也不會忘記他。有人身子不舒服了還鬧著要他推拿,有人一時高興了還會撲到他背上摟脖子打秋千,有了什么苦衷也都愿意向他訴說。他靜靜地聽,話不多,只聽他常常說:“不要急,慢慢來,解決一個是一個。”他儼然成了我們的兄長,我們也當真不論大小叫開他灰哥了,他還挺客氣地接受了這個稱呼。
說他灰,那是因為他和我們相處一年多,衣著大都離不開灰色,夏季淺灰色,春秋銀灰色,冬季青灰色、鐵灰色,甚至我們還覺得他的臉是灰色的,頭腦也是灰色的,且有一種沉重的精神力量,漸漸地給我們形成了一種老大哥式的威壓。
一下班伙計們就要熱鬧一陣,聽錄音機、彈吉他、猜空拳、無端地怪叫。他不滿地瞟你一眼或是咳嗽一聲,我們就會條件反射似地打住。熄燈后我和王雷躺著閑扯,他在床上晃兩下,我們就不得不住口。后來王雷彈吉他,就躲到外面的洗臉間。
老同志反映,這層樓里最近規矩多了。
灰哥似乎整天都在忙著工作,用“勤勤懇懇”“孜孜不倦”一類的詞兒來形容他,一點也不過譽。他的飯碗就放在辦公室,早飯后,當人們對著空碗聊天或在院里轉悠的時候,他已經在辦公樓里忙開了,掃地、拖地、刷痰盂、抹桌子、打開水,干得很帶勁。晚上當我們躺下看書的時候,他才從辦公室回來。上班時間碰見他總是行色匆匆的,跟你搭個腔也總是“哦,我到那邊去一趟”,也不知道他在干些什么大事情。
一天晚飯后,我拉住了他:“灰哥,來!咱們殺一盤,我還沒領教過你的厲害哩。”
“你算是找到家了,我連棋子都叫不準,還是你們來吧,我去辦公室。”他說著就走開了。
我要看看他到底在忙些什么,就來到他的辦公室。他正在臺歷上寫著什么。
我拿過臺歷,隨手翻了幾頁,見上面寫著:牛主任換煤氣罐:郜主任找電扇箱;羅書記的雞飼料……“你今天挨訓了吧?”灰哥客氣地從我手上拿走臺歷。“說了幾句。”辦公室上午來人檢查崗位責任制執行情況,發現考勤簿上全是空白,部長批評我沒做好考勤員。
“你工作應該認真些。”
“什么崗位責任制,狗啃麥苗一一裝羊(洋)。上下班好多少?還不是一陣風就過去了,我懶得給他們畫道道。”
“那怎么行?人家怎樣說咱就怎樣干,打邊鼓隨大調,領導要你怎樣做你就怎樣做,手要勤快些。”說著,他拉開一個抽屜,里面有好幾個筆記本,“領導講話啦,布置工作啦,給你談個話什么的都要記下來,筆頭懶了不行。”
“嗬,對領導可夠尊重的。才幾個月你就記了這么多。”我把抽屜拉開些,灰哥又給關上了。
年終總評灰哥被評為優秀工作者,出席了市里的先進表彰大會,抱回了獎狀和獎品。獎品很實惠,是一雙流行式皮鞋,后來我們還在羨慕呢,卻見他用鋸條鋸著鞋跟,“發給這玩意,現在真是男尊女卑了,比女式鞋跟還要高。”
“灰哥,你也是二等殘廢呀,”王雷說,“現在的娘兒們怪得很,先瞅你身高,相貌再好也白搭。”
“啥蟲拱啥木頭,我不怕這個。男人穿高跟鞋顯得輕浮,君子不重則不威嘛。在機關里……當然穿鞋戴帽各有所好吧。”他看到王雷腳上的高跟鞋,不好意思地改了口。
君子不重則不威,蓋灰哥服飾舉止之大要也。有一次他理發回來,發式整齊,面目煥然,我們都為他叫好,可他倒象生了一頭虱子,又抓又撓,嘟嘟囔囔:“那個理發員真是的,說是給我吹干,誰知他就來上了,我給他說不吹風。”他用熱水燙了又燙,白白送了幾毛錢。
王雷說灰哥是蛀了的青皮果子,可惜了。
機關食堂前有個小石壇,是專為棋迷們設的。飯后這里少不了擺幾盤。羅書記是這里的常客,飯后常轉到這里來過過棋癮。這天晚飯后,這里又熱鬧起來了,后來不知怎么的我就和羅書記對上了。
“請你先走。”我說。
“紅先黑后,輸了不臭,我就先走了!”羅書記呵呵笑兩聲,擺了一枚當頭炮,我跳了一步馬。開局和中局,雙方旗鼓相當,下至殘局,高潮跌起。對方馬炮雙卒士象全,我是車炮雙兵仕相全,對方略占下風,但并不著急,一枚炮、一枚馬、一枚過河卒,均壓在我方一翼,形成進攻之勢。
我開始撓頭了,伙計們指手劃腳地都成了軍師。
“啪!”我拈起將要沉底的兵,打在對方的象眼上。我步步緊逼,沉底炮高出車,直取對方的底象,幾步棋走過,已是勝利在望。
羅書記坐不住了,他還從未被逼成這般慘狀呢。
“走這兒。”冷不防灰哥插手退了一步老將,危局緩解,緊接著又跳馬逼將,剎時我方城下失火,九宮騷亂,老將在對方炮支馬背的威勢下,只好舉手投降。
“哈哈哈……”羅書記大笑,手點了點灰哥,“你這個年輕人呵,哈哈哈……”大伙也嘻嘻哈哈地走散了。
我追上了灰哥:“你不是不識棋子么?”
他停下來,左右閃兩眼,一本正經地說:“羅書記那次掀棋盤的事你不知道?年少氣盛,不識幾微,你還沒吃過這虧。一開始你就讓人家先走,這就亮你有實力,太不謙虛了。羅書記的話你沒聽出來?”他又寬厚地笑了笑,“我這人是不愛多手多腳多口舌的,你在組織部門工作,我相信你這人不會錯,我可沒有把你當外人看。”
我能夠理解灰哥對于我的好心。可王雷不。
宿舍的墻壁上,王雷布置了一張很大的半裸黃發美人年歷,無論在哪個角度,那雙叫你心旌搖曳的明眸都會瞟著你,這常常使灰哥感到不自在。他說再有出息的男人在體面的女性面前都會變得中氣不足,這種玩意兒會把男性軟化的,晚上脫褲都不好意思。
王雷認為灰哥這話富生活哲理。
“哎,王雷,把這揭下吧。”灰哥乘勢說。“你看看,換上這挺不錯。”灰哥展出了一個銹黃色的條幅。
“在哪弄的,這字咋看不懂?”
“這是鄭板橋的字,難得糊涂”。灰哥念道:“聰明難,糊涂難,由聰明轉糊涂更難。放一著,退一步,當下心安。”
“算了算了,”王雷一擺手,“這玩意,貼你床頭好了。”
“你別看這幾個字,其中的奧妙多著呢。”說著,灰哥抬手要揭年歷,王雷擋了一下。
灰哥有些難堪,臉沉了下來,“你貼這讓外面的人怎樣看我們?這是我們大家的事,影響不好。”
“啥影響?你別拿官場上的那一套來嚇唬人。”王雷公雞斗架般地梗著脖子,眼睛斜著灰哥。
灰哥垂下了眼,苦笑一下,不再說話。
“走,到外面走走。”王雷碰了我一下。
“走吧灰哥。”我拽了他一把。
灰哥遲疑了一下,跟我們一道出去了。我們沿著街一直朝前走,誰也沒有說話。灰哥在小攤上買了3包瓜子,一人一包,我們吃著走著,走到了影劇院,兩邊擺滿了自行車,人們絡繹不絕,正趕著場。
“《青春萬歲》,今晚好電影。”王雷指了指片名。
“灰哥,看看吧……就這一晚上。”我說。
灰哥看了看表,摸著口袋。 “我有零錢。”王雷搶去買票了。
電影開始了。我們深深地被銀幕上那歡跳的營火、青春的熱情、坦誠的友誼、少女的倩影感染了。灰哥情不自禁地抓住了我的手,握得死死的,他臉上有兩道淚光。“灰哥。”我輕聲叫他。“我這人不能激動,一激動渾身起雞皮疙瘩。”我朝他袖管里一摸,乖乖,他的皮膚沙紙一樣蹭手。
“看這片真過癮,就象我們在大學,那時的生活多動人。中秋節,我們把開學時帶的好吃的都拿了出來,圍坐在林中草地上,也有篝火,我們那個女輔導員很年輕很活潑,月光下,我們吃著說著笑著,想唱就唱想跳就跳。”灰哥說得很動情,都有點結巴了。
當我們出了影院在一個餛飩攤前坐下來的時候,灰哥好象還沒有回到現實中來。他眼睛閃著光亮,不住地抽煙,掏手帕揩頭,眉眼亂動彈。轉眼王雷從飯館里提了一瓶酒,抱了一大包牛肉片,“來來,干脆來幾兩,難得坐一塊喝。”
“好,來就來,”灰哥動身坐正,“怎樣來?”
“你說。”
“一門一。”
“好,倒酒!”王雷出了拳。
“哥倆好呀、再好好、好到老……八大仙、包拳包……”
我們大呼小叫,對著瓶子喝,眨眼下去了多半瓶酒。過往的行人象看希罕,攤主倒上勁,“來,使這個。”老太太給我們放了3只空碗。
“好,來就來個痛快。”灰哥掏出錢夾,沖王雷“啪”地一拍,“去,再來一瓶。”
灰哥要過酒,沖著3只碗一氣倒光,“我看你們還欠著點,干了算了。”他端起了碗。
我們驚疑地看著他。
“看我臉紅了不是?一會兒就過去了,來,酒是糧食精,干!”他一飲而盡,又亮了亮碗底,我們趁機潑去多半。
“真是真人不露相,灰哥門高量大,真沒想到。”
“這是硬功夫,在下面練出來的。”灰哥臉上透著紅光。
“基層就是鍛煉人。”
“那當然,要不,我還是個孩子呢。”王雷朝我一笑,遞給灰哥一支煙,擦著火柴:“灰哥,聽說你原先在縣委呆過一年?還聽說他們稱你是90年代的年輕人?”
“那時太年輕了,天真得很,啥都看不慣,他們也看不慣我。開會積極發言,有人說你比領導表態還快;學習文件指正他們的錯別字,有人說你露*能……”灰哥目光滯澀。“那時候我跟頭栽得多了。就說那次五四青年聯歡會,我是組織成員之一。那次匯報演出非常成功,特別是男女對舞節目一推出,滿堂喝彩,我暈暈乎乎地跳著,就象多喝了酒。誰知第二天一上班領導就把我叫去了。說那個節目是你搞的?盡出洋相。我說這有什么,城市都熱幾年了,很快會普及到下邊的,也很受觀眾歡迎么。歡迎什么?觀眾是看稀罕哩,你聽到下面議論了沒有,你把我們單位的牌子也送出去了!”
“后來呢?”
“后來?”灰哥沉痛地拍下桌子,“縮著頭,不敢動;不甘心,還想動,又不敢動。真折磨得夠戧。就這樣弄了個偏頭疼。”灰哥拍了拍腦袋,露出痛苦的神情。
我要了3碗餛飩湯,灰哥端起來手打顫就放下了。
“省里抽調人去看守犯人,領導找我談話,我哭喊著不去,結果就被調到了檔案局。我的腦筋算是轉過來了。在社會上混不住人不行。我就脫胎換骨地改造自己,規規矩矩老老實實,香的臭的都能要。我還學會了抽煙喝酒,和老同志坐下來吹旱煙袋,我連眼鏡也摘掉了。不瞞你們說,我還給局長家里拉過煤球買過面粉,甚至還給他擦過自行車,跟著赴酒場當他的酒壇子。”灰哥扔掉煙屁股,一氣把酒喝光,站了起來。
我們一起走了。酒喝得多了不敢晃,一晃就想吐,我們走得很慢。迎面吹來一陣風,渾身清爽,天上繁星抖了抖,有一顆站不住腳,劃道亮光跌下去了。
“怪不得你瞇著眼睛看人,不戴眼鏡還要發展哩!”
“戴它與人合不來,別人看你別扭。”
“管他那么多。我明天還要穿西裝哇!”王雷打賭似的。
“你穿我也穿,咱們一起穿。”我也來勁了。
“穿那個大開口,我會感冒的。”灰哥摸摸衣領。
“穿件西裝你感冒,跟老婆睡覺你還傷風呢!她是誰?你老灰真是黑瞎子敲門熊到家了。”王雷手一亮,竟是個姑娘的照片。
想不到灰哥還真有一手,照片上的姑娘正是他的對象,是在高中就談好的。她中專畢業后在縣醫院當護士。為了注意影響,灰哥守口如瓶,調來快一年了,也沒讓姑娘來過一趟。這事暴露以后,我們談起男女之間的事情,灰哥也不再那么正經了,也時常愛插話,有時還滾到床上閉住眼。我們建議讓姑娘來一趟,讓弟兄們欣賞欣賞。
姑娘還真的來了,不過是她找上門的,她來市里短期培訓。姑娘一進門就把我們給鎮住了,她長得很好看。說好看不如說耐看,這主要與她的氣質有關,垂兩條長辮,自自然然大大方方。她把兜里的柿子掏出放在桌上,一人遞一個,微微一笑,說:“吃吧。”聲音很順耳,不高不低柔柔和和,就跟她人一樣。
一直到很晚,我們還沒有睡著,灰哥送姑娘回來了:
“老灰,這個了吧!”王雷在被窩里拍拍自己的嘴巴。
“明天還讓她來吧灰哥,在一塊多坐會兒。”我說。
“算了算了,碰到好多熟人,要惹閑話。我是跳門進來的,褲襠掛破了。”他一屁股蹾在床上,壓得床嘎嘎響。
我們一直勸他趕快結婚,結了婚就不顯眼招人了。
灰哥果真宣布要結婚了。
灰哥旅行結婚,伙計們都給他送了禮。這個老灰,總有滿腹的心事,都要做新郎官兒了,還沒一點喜氣勁,反 倒顯得更深沉了。
行前的一天晚上,他把我們請到附近的一個小酒館,點了菜,把帶的好煙好酒什錦糖往桌上擺著。不知怎么回事,他今晚話很少,格外嚴肅。
“灰哥,是先回去還是就打這兒起程?”
“打這兒,票已經買好了。”
“路線定哪兒?”
“走著說吧。”
“明天嫂子來吧?”
灰哥停住了。他的目光停在桌上,面色陰沉。
“灰哥,你精神也不要太緊張了。”
“你是不是有什么難處?”“我覺得這事不說對不住你們,今晚正要談談,”灰哥抬起了頭,板著臉,“我后天跟小羅走。”
“什么小羅?”
“工會的資料員。”灰哥的嗓音變了。我們面面相覷。
“你是說那個小茶壺?羅老頭的小姐兒?”王雷沉聲問。
灰哥沒有吭聲,他額頭上有了些碎汗。我們誰也沒有說話。那個小茶壺我們都很討厭,又矮又胖,走起路來還好一手叉腰,扭屁股擺肩膀,一張口就是俺爸俺爸,在舞會上誰都不愿跟她跳。
“咱們怎么一直不知道?”
“一個月前才說的,說現在就要結婚,我也感到突然。”
“你是看中閏女啦還是看中老子啦?”王雷站了起來。
“大樹底下好乘涼吧。”
“茍富貴,莫相忘啊。……”伙計們都站了起來。
灰哥臉色蒼白:“我怎么說好呢,羅、羅書記托人說的,你、你們讓我咋辦,我們都在這里工作……”他忙給我們讓煙,手抖抖的。
“好一個駙馬兒!”王雷一下把煙打開,抄起桌上的一瓶酒“啪”地摔碎在地,掉頭就走,我們都往外走。“哎哎,別走別走,菜都開始上了。”店主老頭端著盤子攔住,“惡心,熊包!”王雷沖他一吼,小老頭縮身跳開了。王雷轉身有板有眼地說:“我們大家一致祝你,一路順風,四腳朝天。”
“你們走吧。”一聲低沉的呻吟。我們回過頭來,灰哥緊繃著嘴唇……我們還是走了。
灰哥搬走了,他當上了秘書科科長,成為市委領導的貼身人,不少人都知道市委有小小科長。
不久,市委班子進行了大調整。新來的市委書記還不到40歲,操普通話帶變色鏡,老牌大學畢業生,真是個硬梆梆的鐵手腕,一到任他就來了幾板斧。一板斧,使電業局占用市郊耕地正在興建的家屬大樓停工扒掉;二板斧,將搬遷戶作難而變成三掉彎的新興大道一線取直。接著三板斧四板斧撤換調動了一批領導干部,在全市引起了震動。
灰哥臉上的微笑不見了,他又整日心事重重的。于是機關里又有了關于他工作調動的傳聞了。
作者簡介張秉峰,男,1963年生,現在鄭州大學中文系秘書班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