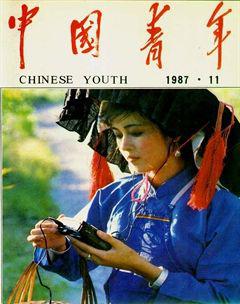干線(小說)
一
郵局今天發《家庭醫生》,王六九5點半鐘就來排隊,當然是頭一個。他掏出準備好的紙片,按次序發號,拿到號的人寶貝似的攥在手里,不時展開看看,想今天有希望。“王叔,你來的真早。”槐花說。王六九點點頭,非常含蓄地笑了笑,之后把手繞到背后去搔癢,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焦黃的胡子抽搐著,很愜意。
當雷勇8點趕到郵局,門前已排起了長隊。他是火車站支局的投遞員,剛進大門,不少人跟他點頭。跟他點頭的人見他站在隊伍的末尾,又加快了腳步。雷勇笑了。
“你笑什么?”賈遺槐問。
“我笑這世道真變了,但也有用我姓雷的時候,那時,要車票,沒有。上煙,不會。問為什么,一個大嘴巴打出去。”賈遺槐笑得直晃,險些坐到地上,他跟雷勇說,你不用排了,去前邊讓你嫂子給帶一百。
賈遺槐說的嫂子指槐花,賈遺槐是槐花的丈夫。雷勇他媽和賈遺槐、王六九在一條街上擺書攤,這條街是干線。
二
這條街南北走向。
雷勇家的書攤在汽車站,王六九在大眾電影院門前,賈遺槐在新華書店北側。雷勇媽出攤最早,雷勇媽是農民,信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原則。王六九每天晚上收攤時都要記住第二天首場電影上映的時間,他按這個時間出攤。王六九的攤子很小,鋪一塊塑料布在臺階上,擺幾行雜志和報紙,然后他老婆守攤,王六九回去吃飯。王六九近視,卻未配眼鏡,看書時把書捧到離鼻子二寸遠的距離,之后歪著頭,眼白大,眼黑小,嘴里嘰嘰咕咕發出一些聲響,象鴿子叫,卻沒有鴿子翱翔時那般悠揚,王六九很少進書,書的價錢大,他怕折本。前一陣有本書非常搶手,他回去跟老婆一學,忘了全名,“一半是男人,一半是女人,半個男人與半個女人,我也記不清,反正有男人和女人。”王六九的老婆浙江人,嘰哩咕嚕跟王六九捶胸揪頭發,觀者不解其意,王六九也再沒提過男人或女人。
賈遺槐是跛子。朋友或同輩人都叫他“老賈”,也有喊他小賈的,那都是滿臉褶皺,胡子發白的人。他走路靠雙拐往前挪,有一輛手搖輪椅車。他希望有一天能去海邊看看,沙漠也可以,最好是亞馬遜熱帶叢林。“我的車爬山涉水如履平地。”這是他跟雷勇夸下的海口。雷勇很早就認識賈遺槐,雷勇媽沒擺書攤時他就常去賈遺槐那兒買書。一個陽光璀璨暖風宜人的下午,他看到有位穿鵝黃裙子的姑娘跟賈遺槐坐在一起,姑娘的身材瘦小,左眼睨視,橫背一只仿蛇皮的女式挎包,正用殷紅的雙唇往外吐奶油瓜子皮。
雷勇:“那是誰?”
賈遺槐:“槐花”
雷勇“槐花是誰?”
賈遺槐:“你嫂子”
雷勇:“?”賈遺槐嘴上叼著“健牌”,臉色醬紫,頭發一根一根往上聳著。
“愣什么,”賈遺槐說:“我遲早會告訴你三件事,三件,少不了你的,只要我不死。但你也別指望太多,太多了,我也沒有,我知道你寫小說,可那算什么玩意兒,扯淡。”
三
雷勇訂電視報一次2000份,其中有王六九的500。1000份以上批發價是82%,1000以下是85%,從此王六九見了雷勇就合不攏嘴。他自己不抽煙,口袋里卻總裝著“金絲猴”,給雷勇抽,當然,也給稅務局、工商局、三整頓辦公室的人抽;遞煙的同時,也合不攏嘴。“伸手不打笑臉人”,他常把這話講給小二聽,小二穿猩紅色的襯衣,高跟皮鞋猛烈地敲擊地面,橐橐直響,一路響著,一路摔打門窗。王六九心疼女兒,又心疼東西,便急忙閉嘴,坐在床上,那天起,小二就在在大眾電影院看電影,她說沒勁透了。下班回家她也不走干線,繞大彎兒逛自由市場,市場里人多,小二說熱鬧。
電視報一來,王六九就坐不住,怕壓在手里,成了廢紙,那時哭都來不及。早上7點,守在學校門口,半小時賣出去200,他也緩了口氣。騎車經過一家羊肉泡饃館,有香味傳來。引得腸胃一陣蠕動。他覷了一眼,搖搖頭,沒有停車,鉆進熙熙攘攘的自由市場,又開始吆喝:
“電視報,電視報,誰要電視報?”
四
“我出生那天,我姥姥生下我小姨才一個禮拜。我是夜里12點降臨世界的。當時,我媽狂喊不止,到后來,一點力氣都沒有,僅能喘口氣了。親戚朋友把我和我媽往醫院送,慌亂之中,我被丟在了門前的一個坑內,當時沒人注意我,光顧著救我媽了,這誰也不能怪。生與死都是瞬間的事,瞬間的事情難以把握,古往今來都如此,我也不例外。我媽叫得很慘,那聲音沒人學得出來,也再沒聽見過,這都是我姨告訴我的,這是后話。前幾年我去老房子看了看,槐樹歪歪扭扭的,有不少殘枝,但長勢卻極為旺盛,根深葉茂,結著不少槐花,槐花很香,離老遠就聞得見,這你知道。我沒有錢,若發一筆橫財,就為我媽在槐樹下立塊碑。可我沒出息,對不起我媽,這話也沒意思,不說這了。我媽剛進醫院已經不行了。醫院要押金300元,這在當時是一筆不小的數字。我姥姥家人口多,拿不出錢來,就東借西湊,錢沒拿來,我媽就死了。聽我二姨講,是我的胎盤沒取下來,把我媽疼死的。
“我媽死后一個星期,鄰居一位大娘懷里抱了一個嬰兒跟我姥姥要奶吃。我姥姥問這是你的孩子嗎?大娘說在門口拾的,一天夜里聽這孩子在槐樹下坑里哭呢,跟貓叫似的,要多難聽有多難聽。我姥姥的眼淚當時就下來了,說這孩子的命真大,不該絕,并喊著我媽的名字說,這是她的兒子,她的命好苦啊,這里的她指我媽。大娘額手稱慶,說她雖然死了,但留下個兒子,也可以瞑目了。大娘是個有文化的人,為我起了現在這個名字,我當然忘不了大娘。大娘早就死了。
“我是用我姥姥的奶水喂大的,所以我跟我小姨長得很象。我媽死的時候18歲,我沒見過我爸,也從未找過他。我媽死后他連面也沒露,什么東西,狗娘養的。”
五
警察:“執照。”
雷勇媽:“在這兒。”
警察:“《美人魚》發票。”
雷勇媽:“發票?這是別人送的。”
警察:“誰送的,你認識嗎?一共有多少?”
雷勇媽:“同志,我……”
警察:“攤子收了、收了,跟我走一趟。”
……
攤子最終還是沒收,雷勇媽一個勁地抽鼻子,抽得警察好難受。警察正患鼻竇炎,也有抽鼻子的欲望,盡管倆人的原因不同,但若抽起來,各方面卻都差不太多。警察把《美人魚》卷走了,讓雷勇媽去一個陌生的地方取收條。警察跨上摩托車,打了個噴嚏,之后用白線手套抹抹臉。雷勇下班后來到書攤,雷勇媽的臉跟警察在時一樣嚴肅。今天所有的顧客都見雷勇媽反常,以為老太太讀書多了,假裝深刻。雷勇媽見到雷勇,說了一句話:“出事了!”淚水就潸然而下。
雷勇幫母親收了攤,路過大眾電影院,王六九正在等最后一場電影。雷勇讓母親先走,然后站在路沿上叫了一聲:“王叔。”王六九扭過臉,笑著跟雷勇點頭,并在口袋里摸索著往外掏煙。
雷勇把《美人魚》的事告訴他,王六九的臉當時就白了,他把《美人魚》往旅行袋塞,邊都卷了,也不在乎。雷勇什么時間走的,更沒去注意。王六九實實在在出了一身汗,他四下瞧了瞧,沒有警察的影子,這才松口氣,用手拍拍臉,暗暗思忖:奶奶的,萬幸。
雷勇來到新華書店北側,賈遺槐正準備收攤,槐花穿著那條鵝黃色的褲子,腳上是雙波士頓白色旅游鞋。
槐花:“吃了沒?”
雷勇:“沒有。”
槐花:“坐吧。”
雷勇:“好。”雷勇見了槐花有些發悚,槐花的眼睛里有一種深邃的不可測的東西,讓人摸不著頭腦,槐花第一次見到雷勇,對賈遺槐說:“哪來的小伙,文文的。”賈遺槐笑得十分豪爽:“這是咱兄弟。”
賈遺槐說,誰敢把我怎么樣,他媽的想砸我攤子,誰砸我攤子我去誰家吃飯,就這回事。
六
“我兩歲那年得的病,很厲害,麻痹到了腹部,再往上來一點,也就沒命了。那時我姥姥還沒死,她把我送進醫院,說我是個孽障。一家不太知名的職工醫院收留了我,命是保住了,人卻廢了。
“我高中畢業后,這里鬧了很長時間的地震,學校放假,那時學習的人不多,我們這么大的孩子都在外野,滿世界撒歡兒,時間長了,能玩的都玩夠了,就想新招,一天,找到了我頭上。
“領頭叫罐,罐比我大好幾歲,我感覺他是成年人,有非常高大的體魄。罐長得漂亮,人也聰明,前幾年得癌癥死了,死的時候就剩把骨頭,我去看他,還讓我吃糖呢。那天罐領了一幫人學我走路,我站著不動,罐就用手推著我往前挪,我以為走幾步是個意思,罐卻很耐心,從防震棚一直把我往家送。走在路在,正值黃昏,天空的顏色好極了。我回頭一看,笑了笑,有21個人跟在我身后,模仿我走路的姿勢,有的喘息,有的擦汗,愚笨些的全身僵硬,象是木偶演戲。我一句話都沒有,罐撲哧一聲笑了,把熱氣噴在我脖子上,麻酥酥的癢。在單元門口,罐突然拉住我不讓進,讓我圍著樓再轉一圈,這可把后面的人樂壞了,不知誰起的頭,于是大家跺著腳,揮著拳頭,高唱‘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在嘹亮的歌聲中,我登上三樓。罐們跟到門口,才哄的一聲往下跑。二姨聽見響動出來,問我怎么了,我搖搖頭,我不愿張口,我知道張口是吐不出一個字的,說什么呢?”
七
今天賣電視報,雷勇天沒亮就起來了。外邊有風,風并不柔和,用刺骨或凜冽形容都可以。掃大街的比雷勇起得早,一路上,盡是嘩啦嘩啦的響聲以及飛揚的塵土。取電視報回來,送牛奶的老頭兒正搖晃清脆的鈴鐺,天空也飄揚起稀稀拉拉的雨點。
王六九沒來取電視報,雷勇直納悶,中午經過大眾電影院,沒見他擺攤。雷勇去王六九家送報紙,開門的是小二,小二冷眼瞧著雷勇,抻了抻橄欖綠色的棒針衫。
雷勇:“你爸呢?”
小二:“住院了。”
雷勇:“什么病?”
小二:“不知道。”小二懷里抱了一只梨花貓,貓頭圓滾滾的,四蹄雪白,毛色鮮亮有光澤。梨花貓見到雷勇,騷動不安起來,發出長時間歡樂的叫聲。
小二:“你說這貓不吃老鼠該怎么辦?”
雷勇:“那它平時吃些什么?”
小二:“魚,豬肝,羊肉。”
雷勇:“沒見過,不知道。”
雷勇有些惶惑地從王六九家出來,他也感到這是一個問題:貓不吃老鼠該怎么辦?雷勇來到書攤,雷勇媽說去看看你王叔,別空手去。
雷勇下午從單位溜出來,買了兩瓶罐頭,一串香蕉,二斤蘋果。賣香蕉的跟雷勇是伙計,死活不要錢,雷勇把一盒“紅塔山”扔給他,伙計差點翻臉。伙計翻不了臉,雷勇想,這是一種巧妙的格局。朋友之間有兩件事不能在一起攙和,一是女人,一是金錢,誰攙合誰倒霉。這事雷勇與伙計都清楚,只是不便挑開。不便挑開的事很多,只要心里有數。
雷勇來到內科住院部,一個漂亮的女護士聽說找王六九,不禁用手掩住口,竊竊地笑,一定是名字古怪,讓姑娘感到開心。王叔告訴雷勇他是農歷六月初九的生日,家人起名就叫六九。王叔的家人沒文化,雷勇想,要不就是文化太多,超脫了,這兩種可能性都有。雷勇走進病房,王六九躺在床上,正打吊針,象是睡著了,床下有一雙開了口的皮鞋,沾了不少土。
王六九的老婆從門外進來,見到雷勇,又見到床頭柜上的東西,沉悶的臉上洋溢出熱情。據她說,王六九昨天上午從城區進書回來,在電車上,被小偷拉去35元錢。回家后,臉色蒼白,不吃飯,不睡覺,精神恍惚,到了夜里開始發燒,蓋兩床棉被還喊冷,把人嚇壞了。今天早上送他進醫院,醫生查不出病因,現在是住院觀察治療,以控制病情的發展。正說著,王六九醒過來,他是被短促而沉郁的咳嗽震醒的,一夜之間,王六九雙頰凹陷,仿佛蒼老了許多。雷勇站在他面前,想說點什么,又找不出適當的話題,于是沉默著,站了很長時間。王六九渾濁的眼睛里涌出兩行淚來。
雷勇從醫院出來后,覺得不舒服,來到賈遺槐的書攤前,想起了小二的問題。
雷勇:“貓不吃老鼠怎么辦?”
賈遺槐:“宰了它。”
八
“那天我正在屋里練字,隸書。這事我記得清楚極了,外邊人聲嘈雜。那是一個初夏的傍晚,滿天的紅云,真漂亮,我再沒見過那么美麗的紅云了。我從家里出來,白樺樹下圍了一群人,我心想這又怎么了,聚眾賭博還是雜耍賣藝?要干也該選個地方。我吆吆喝喝挪到樹下,心里一沉,全明白了。我似乎在什么地方見過她,但肯定又是第一次見面,你說這事奇不奇?她懷里抱了一個嬰兒,超不過3個月,身上裹著一塊紅布,連哭聲都沒有,看樣子,怕是捱不過明天早上。她臉色焦黃,衣衫也不整,身上沒有多少肉,說得文一些,叫憔悴不堪,不知對不對。樓上樓下的大媽大姨們都嘖噴舌頭,說現在男嬰要的人多,比電視里的搶足球還要熱鬧。女嬰也有人要,但差一些,得找機會。她一聲都不吭,低頭看懷里的孩子。我嘆了口氣,這時,她抬起了頭,我盯著她,她的眼瞼下有一層薄薄的淚水。‘有地方去嗎?我問,她搖搖頭。‘那先住我這吧,替孩子找個人家。剛說完這話,我就后悔,有些太冒失了不是?怎么能讓一個陌生的女人帶著孩子在我這留宿。但活已出口,沒有收回的道理,就調頭往回走,她跟在我身后,她的身后,是一片沉默。
“當天夜里,我騰出床來讓她們母女睡,自己架起鋼絲床,心里突突直跳,一夜未曾合眼,聽那孩子的啼哭聲。
“第二天,我就四處奔走,為孩子尋找主家。她默默地流淚,久久地注視著孩子,仍然無話。我說要不就留著吧,把她帶大,她搖搖頭,于是我也無話。我不愿問她孩子的父親是誰,為什么又拋棄了她們,她也從未提起過,到現在也沒有。那種混蛋提他干什么,影響情緒。第四天,孩子被人抱走,她留了下來,當天夜里,她附在我的身邊,告訴我她叫槐花,是樹上結的那種槐花,又香又甜。
“槐花不是本地人,離這有幾百里路,家里還有一個瞎眼的媽媽。下個星期我們要出去轉轉,順便看看她媽媽,我們下個星期就走,我也要有媽媽了。”
九
早晨5點半,雷勇拎了一網兜的水果來到賈遺槐家,從中取出一串香蕉說:“這是王叔送的。”也許是隔夜的緣故,香蕉有些發黑,布滿了大大小小的斑點。槐花接過來問:“他怎么知道了?”
雷勇:“我告訴他的。”賈遺槐:“不應該告訴他,六九叔的身體不好,你今后還要多照顧他才是。”
沒人再說活,房間里出現了短暫的沉默。
雷勇從挎包里窸窸窣窣掏出一面小紅旗來,旗是自制的,上邊用金線繡著“先驅者號”四個字。賈遺槐笑了。
賈遺槐:“這太孩子氣了。”雷勇:“什么叫孩子氣,無情未必真豪杰,孩子氣有什么不好。”
槐花:“他算哪門子豪杰喲。”
三個人同時大笑起來,房間里嗡嗡直響。
賈遺槐把鑰匙交給雷勇,讓雷勇把剩下的報刊替他賣了。“如果我們回不來,這間屋子就留給你做新房吧。”賈遺槐說著沖槐花擠擠眼,槐花笑著說:“不回來去香港呀?”“香港?我還要去非洲看鱷魚呢。”
他們來到大路上。太陽剛剛升起來,雷勇取出照相機,為他們攝下了第一組鏡頭。再見,雷勇揮著手,站在路中央,一股清新的風蕩漾在他的周圍,使他的眼前變得模糊了。
槐花騎上自行車,推了賈遺槐一把,賈遺槐笑了笑,深深吸進一口氣,然后彎下腰,沿著筆直的干線,向前搖去。
作者簡介崔敏,男,生于1963年2月,高中畢業,現待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