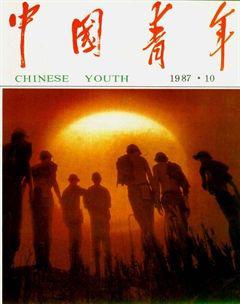旅途匆匆(小說)
一切都出于偶然。
要是火車不晚點,要是自己不在月臺上散步,要是不接他倆敬的香煙,要是……這事就不會發生。
夜色很濃,清風拂面,水銀燈映著腳下一塊塊正正方方的水泥地,讓人渾身滾動一陣陣莫名其妙的興奮。
乘車的人不多,劉維祠點一支煙,在月臺上踱步。
兩個生意人大包小包地把東西從候車棚搬出來,堆在月臺上,然后站著抽煙。
抬頭看看天,那天上黑乎乎的什么都沒有。劉維祠慢慢踱過來,那穿牛仔褲的生意人湊攏打招呼:“伙子,趕這趟車到哪兒?”
停下步,沖他倆笑笑:“到成都。你們呢?”
“同路同路。我們也到成都。”戴遮陽帽的生意人說。
隨即就遞過來一支煙。長把兒的,黑暗中看不清牌子,抽起來有一股中藥味兒,挺適口。
于是,就跟兩個生意人混熟了。
閑談間說起自己大學畢業分到這山溝里一家軍工廠,這里天氣太熱,熬不過夏,特意請事假回家去躲幾天。
牛仔褲便說:“請事假那你車費恐怕報不了銷?”
遮陽帽說:“管你報不報得了。這樣子,我們東西帶得多,怕罰款,兩個人扯了三張票。你趕緊去把你的車票退了,我們勻一張給你。你要是報得了就賺,報不了白坐一趟也不賠,咋樣?”
劉維祠吃一驚:“這個……”
牛仔褲說:“沒來頭,車上檢查起來,你幫我認兩包東西就是了。到成都出站的時候,再幫我提出去。”
劉維祠心跳起來:“這恐怕不太好吧,這個……”
“有個●的好不好。沒得問題。”牛仔褲說:“紅黑我兩個人還是要扯三張票。你莫客氣!”
“來!我幫你退票。”遮陽帽朝候車棚走去。
月臺上,留下劉維祠和牛仔褲。
劉維祠看著遮陽帽的身影,說:“你們是做生意的吧?做的是什么生意?”
牛仔褲朝鐵軌上吐口痰:“對頭!做生意的,啥都做!這回整的是服裝,里頭夾了幾條煙。我們不定樁,賺得到錢作數。哪門子來錢就做哪門子。”
“聽說做生意的人很多,都能賺錢?”
“哪有只賺不賠的生意?有時候賠得精光,褲兒都要脫下來賣了的味道。話又說轉來,賺是多數,要不哪個吃飽了沒得事干肯出來遭罪?你說呢?”
遮陽帽很快就回來了,人影子一跳一跳的。劉維祠不敢正眼去看。遮陽帽走攏來,塞張十元票子和兩張車票給劉維祠。
“這……”劉維祠接了,臉脹得通紅。幸虧天黑,他們看不見。他說:“我有票,我有票的。”
遮陽帽說:“這兩張加上你那張,三張票放在一堆免得各人弄丟了,橫豎一路走就是。”
火車終于來了。劉維祠提著兩大包東西,沉沉的,上車的時候他想:“這里頭真是服裝和香煙嗎?該不是……”心里又亂跳起來。
車上人不十分多,有的是座位。這趟車趕熟了,圖的就是有座位。
劉維祠說要靠窗口,便到側面位子上去坐了,跟兩個生意人隔一條過道。兩包鼓鼓囊囊的東西就堆在他頭頂上的行李架上。那里面塞的究竟是什么?服裝?香煙?或者是別的緊俏貨?或者是違禁品,易燃易爆品?或者是……碎尸?那自己豈不成了同謀犯……
他為這種想頭感到發笑。沒有的事,胡亂編排什么呀!
可是,心里卻再也無法安生,老是覺得有什么地方不對勁兒,渾身都不自在。
走來一個列車員,急匆匆的,胳膊里夾只鐵皮飯盒。飯盒里有一把勺子,叮當叮當響。
劉維祠一陣心跳,雙眼直勾勾盯那只飯盒。
乘警緩緩走過來,背著雙手,雙目炯炯一掠而過。
劉維祠猛地打個哆嗦。
真后悔不該貪這十塊錢,卑賤下作羞恥!
搭眼去看那兩個生意人。牛仔褲趴在茶桌上大睡,遮陽帽在看一本雜志。封面是袒胸露肚的女建美運動員。
他們到底是什么人?
一個問號打劉維祠心底升起,便不能散去。
后來終于閉上眼迷迷糊糊睡著了。
車到內江,深更半夜的,卻一下子涌上來不少人。車廂里顯得擁擠起來。喧囂聲吵醒了劉維祠。睜眼一看,那兩個生意人正眉飛色舞地談著什么。
座位上添了個姑娘,穿一件小網格衫子,碎花奶罩隱約可見,很是扎眼。下面是一條米色裙子,兩只圓圓的膝蓋露在外頭。大概是剛上車的。
劉維祠想閉上眼來再睡一會兒,卻睡不著。聽到牛仔褲和遮陽帽同那姑娘談得火熱。
“錢不錢的不關事!說老實話,州也闖了,府也蕩了,大迭大迭票子見多了,不貪你這兩個,又不是指它吃飯。”
這是牛仔褲的聲音,充滿豪氣。
“不!做生意是做生意,是要雙方都有利才得行。你們也不要覺得臉面上過不去,一就是一,二就是二,這種事不講面子。事辦成了,辛苦費還是事先講清楚的好。”
這是那姑娘的聲音,滿悅耳。莫非她也是生意人?
“他這個人,一向瓜不兮兮。遇到你這么漂亮的姑娘,莫說零對零不賺,就是賠本生意也肯做,看是不是啊?”
這是遮陽帽的聲音,嘻皮涎臉,說罷哈哈大笑。
那姑娘說:“哎哎,不要扯這些,我這是正兒八經辦事,不開玩笑。”
這姑娘怪老練的,一定也不是個好東西!
牛仔褲說:“是要硬逗硬,莫來耍子。拿筆記起,我們跑完這趟就整你那趟,一言為定!”
“一言為定!”那姑娘響亮地應,似乎跟牛仔褲或遮陽帽互擊一掌。
一定不是什么好東西!
劉維祠越發后悔了。三教九流,他們算下三爛!雖然那包里可以肯定不是碎尸不是易燃易爆品,他倆也不一定非是走私犯不可,但是,他們那種人,總是來路不正的。
“你們這趟,弄了些啥東西?”那姑娘隨意地問。
牛仔褲說:“這回是小打小鬧,就幾包服裝。”
姑娘搭眼朝行李架上看:“就這么點點呀?我看沒多大個搞頭。”
“咳!你莫小看了。都是搶手貨。”遮陽帽說,“給你透點風,那邊時興的就是小管褲,莫看天氣恁個熱,照穿不誤。美嘛,不怕勒屁股。好銷得很。”
“整了好多?”
“幾爪子。”
“幾爪子?就這幾包?哄鬼去!我不信。”
“大學生那兒還有兩個大包包。”牛仔褲向劉維祠這邊揚揚下巴兒。
“大學生?”那姑娘目光扭向劉維祠。
劉維祠趕緊把眼睛闔嚴實,裝睡。心卻亂跳起來。
“是大學生。”遮陽帽說,“真資格的大學生。”
“你們咋和大學生打起堆堆來了?”那姑娘很好奇。
“路上碰到撿來的,花錢給他買張車票,雇他出把力氣……”
“噓!”遮陽帽擠一下眼,“小心他聽到。”
牛仔褲說:“這有啥?又說不掉他二兩肉。”
那姑娘朝前伏伏身子,壓低聲氣,還是讓劉維祠不幸聽到了:“你們咋把大學生都撿到了?不簡單哩。哪天我也去撿一個,玩個資格。”
遮陽帽笑瞇瞇地說:“那還不容易哇?茅廁頭牽出來一串一串的就是,到路邊上隨便哈一個就是。”
“有啥了不起,你以為大學生就好啷個?莫那么稀奇,其實他們窮慘了。哪有我們幾個來大錢?跑一趟就進一把,夠他吭哧吭哧掙半年,你信不信?哼,喊我象他那樣子活,兩天就要憋出毛病來!”
牛仔褲把兩只手插進屁股上的兜子里,左手掏出一把手紙,右手掏出一把錢票子,全堆在茶桌上。他從那堆錢票子中挑出一張十元的,展開拂平,兩手張起來對著燈光瞄,說:“看,有天安門,是真真的票子。”接著,他拿起桌上的電子打火機一按,嗒,竄出一股火苗子,藍盈盈顫悠悠,把十元的票子點著了火。那錢票子燃起來,火苗兒竟也是藍盈盈顫悠悠的,又取出一支長把兒香煙叼到嘴里去就那火兒。點著了香煙,把手里燃著的票子一晃一晃,任那錢燃成了皺皺巴巴的一張黑灰,撮起嘴來一吹,這張黑灰飄出車窗,一閃就不見了。
牛仔褲眼里灼著奇光異彩,笑瞇瞇地吸煙。
半車廂的人都驚訝地朝牛仔褲望。
劉維祠臉騰地漲紅了,覺得周身的血液朝臉上涌。
遮陽帽和那姑娘聲色不動滿不當回事兒。笑還是笑,說還是說,連眼皮都不多眨一下。
“是嘛,一個個酸得不得了,其實統統傻咧咧憨包一個。”“算了算了,不說他們,沒味道。”姑娘擺擺手,“你們覺得在重慶搞點高煙容不容易?”
牛仔褲一愣神,跟遮陽帽飛快地丟個眼色。
“咋個?你姑娘家家還要做煙生意呀?”
“這有啥稀奇的?好象做煙生意是個賠本買賣一樣,”那姑娘不屑地一笑。
“弄高煙就下貴州上云南嘛,咋說重慶呢?”
“哎!這話就老外了。未必不曉得路上不好走?又是風又是雨的,高煙多轉幾道手倒無所謂,怕就怕遭一鍋端。重慶算近得很的了。”
“重慶也不好整,才剛剛大查了一回。上次我們到貴州耍一趟轉來,碰端了,車上盤查,遭砍了兩箱去,還倒貼進去幾批錢,栽慘了,差點把牌子耍落,風聲緊得很。”
“但是成都那邊俏得很呵,比你整幾條小管褲強多了。有本事的該走這條近道。”
“可能,可能。完全有這個可能!”
遮陽帽在茶桌上拾起一枚五分硬幣在手中拋來拋去地把玩著,驀地說:“現在興拿這東西燒戒指來戴,另外再花兩三塊錢,一會兒就弄好了。男的女的都肯干。先把它擱火上燒軟了,然后放到砧子上打。”
牛仔褲忿然道:“我說那些人簡直沒名堂!顯哪門子洋盤?有派的打一條金戒指銀項鏈把女朋友拴起。五分錢硬幣算個卵!除非有以前的孫大頭袁大頭還差不多。哼,都是些黃泥巴地頭長出來的洋蔥!”
劉維祠注意到,那姑娘右手中指上戴了一只灰色戒指,卻不知是不是五分錢硬幣燒打出來的。
后來,不知怎么的,他們談起各自的年齡來。牛仔褲23歲,遮陽帽22歲,那姑娘也22歲。
劉維祠酸酸地想:25了,他們都比自己年輕。
后來,他們又扯到各自的家庭。牛仔褲說他是獨生子。遮陽帽說他家哥仨,他是老二,母親已經不在了。那姑娘說她有一個妹妹兩個弟弟,她是老大。
再后來,那姑娘起身走開,進廁所去了。
牛仔褲和遮陽帽伏在桌上嘻嘻地笑。劉維祠隱隱約約聽到他倆交頭接耳說下流話。
“這女子,長得,嘿嘿,還算漂亮。”
“臉嘴倒一般,就是那個……你看那兩只……好露,要是……”
突然提高嗓門:“爬你的喲,你龜兒莫想昏,少恁個邪!”
那姑娘回來了,一路整理著頭發。她很漂亮,臉上充滿自信。劉維祠卻依稀覺得她很可憐。
從車廂門口走進幾個列車員,乘警跟在后頭。
“喂喂喂,驗票了驗票了!都把票拿手上,都拿出來。”
劉維祠打個激靈,猛地竄起身,下意識地往兜里掏票。
那姑娘朝他看,似乎還笑了笑。是善意的笑還是鄙夷的笑?沒看清。也顧不著去看去猜度,要查票了。劉維祠盡管有票卻很慌張。
旅客們騷動起來,紛紛掏兜取票。
那邊有個列車員用彈簧秤勾起一大包東西。
旋即有聲音吼叫起來:“開口就喊罰5元,哪有這個道理!曉得你們在這上頭發獎金。也不能這樣子敲棒棒啊!”
“這是上級的規定,你看不看一下文件呀!要看就到那邊找車長要。”
“我不管你啥規定不規定……”
“有意見去找上頭,現在先拿錢來。”
大家都勸那人:“算了算了,交就交嘛。反正你們做生意的,到站就撈回來了,哪在乎半張票子。”“交錢交錢,莫扯那么多白。喊他們趕快查過去,我這兒好接著睡……”
挨個兒查過來了。不等列車員開口,牛仔褲就站起來說:“我們這兒有四個人是一路的……”
列車員看也不看他,指著行李架上的包大聲喝問:“這東西是哪個的?”
劉維祠心頭幾自狂跳不已。
遮陽帽說:“我們四個人的。”
“哪四個?”
“我,他,她,還有他。”牛仔褲一一指點。
“票呢,拿出來看。”那姑娘說:“何必嘛,我們四個人帶這么多東西未必還混車?一看就不象不買票的人。”
列車員瞅她一眼:“裝的啥東西?打開看一下!”
“沒得啥好看的東西。就幾件隨身行李。”牛仔褲笑瞇瞇地,“他們倆旅行結婚,沿途買了些東西。”牛仔褲指劉維祠和那姑娘說。
劉維祠格外緊張,心頭正咚咚跳得慌,聽牛仔褲這么說,也顧不得臉熱,鐵青著臉,強扯起嘴角笑一笑。
那姑娘臉上緋紅,就手拉開擱茶桌上的小挎包一迭聲兒說:“來來,師傅,吃幾顆糖。”
列車員不睬她,說:“你們的行李怕超重了,過一下秤吧。”但語氣已和緩了不少。
“絕對不可能超重。我們四個人呢。不怕麻煩你就挨個兒勾嘛。”遮陽帽說。
后面的列車員推一推同伴:“走走走,少涮罐子,莫吵了人家的好事。”
一行查票人員從身邊走過去。劉維祠暗暗長舒一口氣。四個人互相對視一眼,咧開嘴就笑。那姑娘笑得哈下腰去。
劉維祠笑是笑,心里卻不是個滋味。
過不一會兒,那邊鬧哄哄走過來幾個人。查到了一些沒有買票的混車者,列車員不時地在他們背上推一掌。
一個穿T恤衫叼煙卷的小伙子回口嚷:“不要掀嘛。補票就補票,罰款就罰款,又不是敲沙罐的死罪,掀啥子掀!”
推他的列車員把眼珠一鼓:“坐車不買票你還嘴犟,扇你龜兒兩耳光,再犟!”
劉維祠心跳跳地看著這場面,早出了身冷汗。
牛仔褲卻來了勁:“呀,逮他媽這么多,精彩!”
遮陽帽說:“坐車子不買票,龜兒子也太寒酸了。省那一張錢干啥?留到二天死了墊棺材?”
那姑娘探過頭來問劉維祠:“你是大學生?”
劉維祠裝著沒聽見,把頭偏向車窗。
窗外黑乎乎的。窗玻璃上映出那姑娘的臉,很模糊。
牛仔褲一屁股坐下去,招呼遮陽帽,二人合力把車窗抬起來。立即,一陣金屬的鏗鏘與轟鳴隆隆地撞入耳鼓。一大股涼風涌進來,滌蕩著車廂里混濁的空氣。
劉維祠面對窗口,呆呆地看那黑夜。他什么也看不見。
之后,迷迷糊糊地又睡著了。
醒來時,天還是那么黑。一看表,已經過了凌晨5點。就要到成都了。于是又擔心起出站的事來。
要是出站的時候人家堅持要打開包檢查,怎么辦?那幾只包里到底裝的是什么東西?他們為什么那么怕檢查?還鬼鬼祟崇的?那女人真的是從內江上的車?她跟他們怎么一下子就混得那么熟了?到底是什么關系?……
猛地,冒出一個念頭:何不離開他們?對,離開他們!馬上就到站了。現在就起身從這里走出去,過幾節車廂,找個僻靜些的地方等著。車一停馬上就下,爭取第一個出站。一出站,身后的人群就堆在出站口了,全是肩擔背馱的行李,盡是東張西望攢動的人頭,他們上哪去找?那就啥事都沒有了。
劉維祠長舒一口氣,仿佛他已經站在車站廣場上了。那幽藍的夜空中繁星密布,四下盡是清新的黎明的空氣。
但是,他猶豫不定。看看那三個生意人,東倒西歪睡得正沉。遮陽帽趴在桌上,呼呼打鼾。牛仔褲靠著窗口,頭昂得高高的,頭發讓風灌得蓬扎扎。那姑娘的頭靠在牛仔褲的肩膀上,牛仔褲的一只大手還扶著她的腰。
哼!真不是東西!賤貨!狗男狗女!
劉維祠站起身,背上挎包,走!
急急地一連走過四節車廂,到餐廳門口站定,這里比較靜僻。很擔心他們發現了追上來。心焦焦地盤算著,萬一他們追上來了,自己該怎么解釋。越急就越是想不出來,滲了一身冷汗。
就說肚餓了,來看看能不能買點東西吃。
終于想出來了。舒一口氣,點一支煙,猛吸。
車速漸漸慢下來。旅客們亂哄哄地動騰了。有的伸開手臂大張著嘴打哈欠,有的提提褲子,動動腰身,有的忙著去行李架上取東西……
窗外閃過一片晃眼的燈光。到站了。
下車,箭一般射向出站口,撇下熙熙攘攘的人群。出站檢票,一掏兜,心猛地一陣抽搐,掏出三張車票!
回頭去看,但見人頭涌動,如同漲潮的海。
“走路走路!東張西望干啥?腳板印掉了哇?”
“走不走?!不走就立到邊邊上去!”
劉維祠被人流卷出了車站。他不走。他把臉貼在冰涼的鐵柵上,鼻尖布了一層細密的汗星子。他朝月臺上使勁睜大眼睛。目光一遍一遍掃過那一群群一伙伙的人。
突然,他看到一堆包包,墳墓似地拱起。正是那種紅藍白三色的大提袋。牛仔褲、遮陽帽和那姑娘站成一條線,三個人都拼命踮起腳后跟伸長脖子四下探尋。
劉維祠掉身就逃。急急跨過橫廊,穿過車道,走到那寬闊的大廣場上。如同一條小魚,游進了湖心。這里人來人往,大家都匆匆忙忙。
他們沒有車票怎么出站?補票?罰款?他們帶著那么多東西怎么出站?會檢查那些包包?那里面到底裝著什么?查了又會怎么樣?又要罰款?罰多少?會讓他們從起點站補票?那,他們會虧進去不少錢的。
不不,不會。他們都是精明人。沒有車票可以混出來。東西多可以找到人幫忙。還有那個姑娘,她一定會幫他們。她準能出個好主意。她辦起事來一定跟她人一樣漂亮。
但是,今天車上有鐵路糾察。驗票的就是糾察隊的人。
劉維祠放慢了腳步。
幸虧沒告訴他們姓名地址。要不他們會找上門來拼命的。他們都是些敢作敢為不要命的人。
劉維祠加快了腳步。
天還沒有大亮,東方卻已經透出些微的曙色。書上老愛這么寫:東方出現了魚肚白。
但是,這車站廣場上的各色燈光仍然十分顯眼,把這朗朗的天地映照得仍象在黑夜。
頭班電車還沒有發出來。不能在這里呆下去,離開這里!離開這里!
繞過街心花園,躍過大馬路,順著街邊的人行道走。越走人越少,離那喧囂與嘈雜越遠。漸漸地就只聽見自己咚咚的心跳和粗粗的喘息。接著,就只有沉重的腳步聲了。
腳步卻又慢了下來,兩條腿軟軟的,骨頭象是被抽去了,塞進一些爛棉絮。
一夜的惶恐逝去了。留下的是久久的淡淡的哀傷。總也散不去。
他很憂愁;此外好象還有一些個他說不清楚的東西。
作者簡介
張勤,男,24歲,大學畢業。現在四川柴油機廠工作。
(題圖:周小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