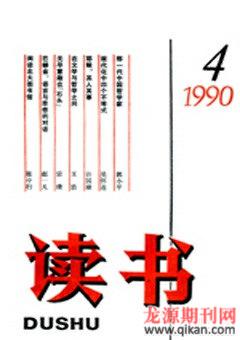現代化的四個不等式
吳懷連
現代化是當今國人談得最多的話題之一,但不知怎么,我總有一些擔心——假如現代化發展起來,跟我們所想象的不同,那么,我們的人民承受得了現實同理想背離的打擊嗎?因此,想找個機會,把這一層擔心說穿。但如此重大的題目,人微言輕,不敢造次。前些時,書友介紹曰:《第三世界》如何如何。拿來一看,果然有些道理。
此書作者是一位西方新聞記者,大名鼎鼎的保羅·哈里森,英國人也。哈先生見多識廣,又勤于筆耕,著作宏富。一九六八年,他來到尼日利亞任教。在那里,他開始研究第三世界的社會發展問題。此后十多年,他考察了亞非拉大部分最不發達的國家,發現這些國家以及整個第三世界越來越貧困,越來越不平等,其最根本原因,不僅是由于它們的文化傳統存在著致命的缺陷,而且也由于西方強行注入了不合時宜的“現代化”,以及它們自己可悲地把這些東西全盤接受下來。一九七九年,他出版了上面提到的那本書《第三世界》,副標題:“苦難·曲折·希望”,正好點明他在這本書中對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的深刻反省。
一工業化不等于現代化
當工業文明在西方首先涌現,并得到迅速發展時,不少西方學者僅以西方的事例下結論說,工業化,只有西方的資本主義的工業化,才是現代化的唯一道路。大前提一旦確定,剩下的也就只有用一些片面的事實來編織他們所謂的理論了。于是,關于工業資本主義的起源,這些學者硬說,只有西方,才有工業資本主義發展的適宜土壤,那里的地理環境、社會結構和文化精神都鬼斧神工地開鑿了工業化的道路,其它任何地方都不行。對此,哈里森另有創見。他承認,經濟發展的初始條件——大自然的秩序是不太公正的,上帝偏愛白皮膚、藍眼晴的臣民,將溫暖、濕潤和幸福留給歐羅巴,而討厭他的黑皮膚,黃皮膚和褐皮膚的兒女,把酷熱、干旱和災難帶到亞非拉。基礎不同,起步不同,結果自然也會不一樣。他還承認,工業資本主義得以率先發展的另外幾種基本條件,如豐富的剩余農產品、不受控制的企業家階級、巨額資本和實用科學的發展等等,西方又得天獨厚。但他指出,問題的關鍵還不在這里,而在于歐洲人靠著他們的武力征服和不體面的貿易,開創了優越的外部環境。哈里森坦率地說:“即使是在這個初期階段,對非西方國家的剝削,就曾對西方資本主義的產生起過關鍵性的作用。的確,如果沒有這種剝削,西方是否能實現工業化都是值得懷疑的。”(第26頁)
如此說來,問題就清楚了。工業化帶給西方的現代化,是以非西方的“犧牲”為前提的。如果看不到這一點,過分相信西方“現代化”論者開的診單,走西方的老路,由工業化而現代化,或現代化必然工業化,那么,工業化即便成了,現代化則很可能仍是鏡花水月。
第三世界許多國家獨立后,為了實現現代化,紛紛走上了工業化的道路。由于缺乏西方工業化早期那種外部條件——沒有什么國家可供它們殖民和掠奪(相反,還要受西方國家的控制),第三世界工業化問題成堆。首先是就業問題。哈里森指出,由于人口沒有得到有效控制,地力耗盡和農業機械化,農村大量的剩余勞動力無法在土地上就業。保守的估計,到本世紀末,第三世界大約有十億勞動大軍等待著就業。然而,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仍照抄西方模式,走資本密集的道路,即不管適用不適用,一概以“大型”、“尖端”、“新式”、“自動化程度高”為最佳選擇,結果搞得弊病叢生。道理很簡單,設備固然先進,但對于人多勞力過剩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它“先進”的意義也就不太重要了。其次是如何利用西方技術的問題。一方面想千方百計甚至不惜以犧牲關系國計民生的農業的利益為代價,將幾個有限的外匯花在進口西方技術上;另一方面,由于其它條件跟不上,設備不配套,大批進口的先進設備又被閑置不用,就象擱淺在水洼子里的鯨魚一樣,或者利用率不高,生產能力白白浪費。至于說,這些國家為了發展工業,而犧牲農業,為了發展大工業,而犧牲小型工業造成的社會問題,則更多。哈里森指出,工業化使第三世界發展成為一種奇特的動物,“它遠不象健康的工業化國家那樣好似一匹體態勻稱的駿馬,肌肉發達,英姿矯健。這個奇特的動物更象一頭長頸鹿,身體的各個部分不成比例,……或者說象一個腦積水的嚴重病例,腫脹的腦袋過大、過沉”。(第224頁)
二城市化不等于現代化
同工業化一樣,城市化給西方和非西方帶來的后果也是相隔天淵的。在西方,城市化曾在一段短暫的混亂之后,展現出天堂般的富足。但非常遺憾的是,在第三世界的城市中,除了市中心幾幢西式大廈裝點門面和密扎扎的一大片人海外,我們見不到西方都市的一點影子。城市化給非西方大多數國家帶來的是混亂之后更大的混亂。
哈里森指出,在第三世界,幾乎所有地區的農村居民都在拚命涌入城市。要說什么是第三世界的城市化呢?那就是臨時工、季節工、修鞋匠……和他們的家屬,各色人等,在通向城市的大道上,潮水般地滾動。當年英國工業革命初期,農民們離鄉背井,來到城市謀生,是“羊吃人”,被迫的,極不情愿的;可現在卻倒過來,農民們趕著他們的“羊”,主動地、滿懷希望地來到城市。為什么農民要涌向城市?問題很簡單:農村勞動力剩余是一個因素,另一個因素便是農村太窮,城市富裕,城鄉差別擴大。
在西方,城鄉差別盡管仍然存在,但不大;而在第三世界,勞動收入本來就很懸殊,如果計算其它方面,差別就更大了。哈里森指出,盡管第三世界貧窮落后,但他們在點綴門面上,花錢是毫不吝惜的。不少國家的都市中心區的景觀,與西方城市毫無二致。居住在這些天堂般城區的居民,是第三世界天生幸運的一小群,他們和他們的農民同胞的差別,絕不僅表現在工資收入和有形的消費上,而且還表現在醫療衛生、教育、生活服務以及娛樂方面。城市居民生活水平高,當然有它的合理的一面,如勞動生產率高、城市生活方式優越等,但也并非無可指責。哈里森認為,第三世界國家領導人用出口資源和農產品換來的寶貴外匯,建設他們所謂現代化的飛地,投資政策向本來是強項的城市傾斜,讓城市居民獲得與西方發達國家相近的生活感受,而任憑農村自生自滅,就是不合理的。還有,為了平息城市人對物價上漲的不滿,而不惜血本,挖空財政,予以補貼,同樣也是不合理的。他引用坦桑尼亞總統朱利葉斯·尼雷爾的話警告說:這樣做,“我們就可能陷入這樣一種局面,即在坦桑尼亞真正存在的剝削是城市居民對于農民的剝削”。(第154—155頁)
農民流入城市,明顯的后果有兩個:一是農村“失掉了那些出類拔萃的人,那些受教育最多,愿意實行變革,適應性強,年輕力壯,精力充沛的人”。(第155頁)農村生產力低下,經濟成長不快,這不是唯一的原因,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二是大批人口涌入城市,會給城市帶來許許多多的問題。首先是失業問題。其次是住房緊張。第三世界領導人奉行的都市政策,無非是照搬西方模式。他們根本不考慮適合不適合,條件具備不具備,一個勁兒地上摩天大樓,高速公路,立交橋,五星飯店。標準太高,資金有限,下一步就只好少建或不建,結果能享受現代化文明的只有那么一小撮,廣大窮人只好望樓興嘆。于是在畸形繁榮的現代城區中心的周圍,又廣布著用簡易材料搭成的貧民窟的海洋。哈里森寫道:這些城市的中心“使人想起拍攝美國西部電影時用的布景,各種建筑只不過是用架子撐起來的表面,在這后面是一片荒漠。這是在悲慘的海洋中搭起的一個小島。倫敦有一條農田構成的綠色地帶,而第三世界的城市有的是那些被排斥的卑賤者聚居的巨大黑色貧窮地帶”。(第166頁)豪華與簡陋、富裕與貧窮有機地結合起來,少數人的幸福與多數人的痛苦息息相關,第三世界經由城市化而追求的現代化,如此而已。
三西方化不等于現代化
哈里森在書中用了一整章的篇幅談西方化,他所列舉的事例與現象,我們并不陌生。例如,青年人喜歡西方雜耍,而不喜歡看京劇,不獨新加坡是這樣,中國亦是如此。現在人們越來越喜歡、越來越習慣于西方生活方式,視西方文化為現代的;越來越討厭甚至憎恨本國傳統文化,視本國傳統文化為異物,千方百計地設法丟掉它。洋衣、洋煙、洋車、洋電影……總之,一切進口貨(當然主要是歐美的),都被認為是高級的、體面的和有滋有味的,即使是帶有艾滋病毒,洋大腿也比本國大腿性感,更能創造經濟效益(不信但看新掛歷,唯有洋女最來錢)!人生在世,不消費那么幾件外國貨品就叫白活。這就是問題的全部,也是它的要害所在。
西方化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殖民主義時代。西方殖民者在海外開辟他們的殖民樂園時,圣保羅教派的教義使他們無一例外地把西方文化看作是優越無比的東西,根本沒有考慮當地文化中是否還有合理因素,更沒有想到要將自己融入到當地文化中去。在殖民地,他們一依母國的樣式,建造城池住宅,過著與當地完全不同的生活。這種異國風光和生活情趣,作為文化的一種最直觀的播遷方式,經由那些高高在上的殖民統治者和他們周圍的人傳送到普通民眾。如果說經濟政治殖民主義統治改變了殖民地的經濟政治結構,使他們被迫依附于西方的話,那么,文化殖民主義統治則改變了殖民地人民的生活方式、規范和價值觀念,使他們自愿接受西方的統治。西方殖民者還通過自己的“比照集團行為”和教育,有效地然而又是無形地實現了他們的文化入侵。哈里森特別提到教育的作用。他說,“學校一直是在青年當中推行西方化的有力武器。學校經常把西式服裝強加給小學生,課程設置注重現代城市活動及其價值觀念”。(第43頁)其結果,這些學生一個個變得好象是外星人似的,對故鄉的一切都十分陌生而且很不習慣,他們看不起本國的文化。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殖民地政治獨立后,那些曾經在西方接受教育,飽嘗過殖民統治的羞辱,發誓要報仇雪恨的政治領袖們,不但沒有阻止西方化,反而使他們的國家西化得比任何時候都更加全面、徹底和順利。哈里森舉土耳其總統基馬爾做例子,他說這位總統先生年輕時在西方求學,曾因戴土耳其民族風格的帽子而備受奚落。當上總統后,他決心使他的國家徹底西化,不但制度要仿效西方,文字和穿著要改成西方的文字和服飾,甚至不惜制訂法律,禁止國人戴曾使他受辱的所謂不文明的土耳其圓帽。
如果說,西方化能使貧窮落后、人口眾多、資源貧乏的中國變成象美國那樣富裕的國家,使中國每個家庭都有小汽車、別墅、空調和高爾夫球場,那么,這種西方化盡管“化”好了,不獨“西化”論者歡迎,馬克思主義者也是歡迎的。但是,正如哈里森指出的,西方化的本意和后果,都不是這樣。從本意上講,西方人到第三世界開工廠,做生意,交流,傳播他們的文化,目的是為了謀求他們自己的利益。為了更大規模地或更好地達到這一目的,他們也許會對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投點資,也許會有一些援助,但你不能想象,商人會盡做蝕本生意。從后果上講,西方化也沒有使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這里所說的現代化,是指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差距縮小,是指發展中國家逐漸擺脫依附于西方,受制于西方的后殖民地的困境。一百多年的西方化,是否達到了上述目的呢?有一份報告說,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五年,第三世界工業在世界工業品總產量中的份額,基本上沒有什么變化,而人均產量同發達國家相比,則有天淵之差,并且仍在逐年下降。更為嚴重的是,西方化的教育,西方文化的傳播,造就了一大批疏遠自己的文化傳統,看不起體力勞動,沒有愛國熱情,向往西方生活方式的寄生蟲。這些人大都以世界主義是尚,為了實現所謂的“人類利益”,他們不惜出賣國家、民族的利益,甚至出賣他們的父母和他們自己。自然,如果西方發展了,作為它的邊緣地帶的第三世界,分得一杯殘羹剩飯,有所發展也是可能的,但這個體系決定了邊緣地帶永遠不可能超過中心,決定了第三世界永遠也擺脫不了依附于人、受制于人的命運,如果西方化一如既往的話。
四市場化不等于現代化
《第三世界》的主題是研究貧困的。哈里森在這部著作中,提出了四種不同類型的貧困:地理型貧困,主要由自然和生態條件造成;社會型貧困,主要由社會制度的不公正,加之人口過剩,技術的分化作用所造成;經濟型貧困;政治型貧困。哈里森特別提到第三類貧困形成的機制,不是別的,而正是被譽為“現代化的基石”的市場化。
作為經濟學研究的重要對象,市場規則是十分簡單的:供求雙方等價交換。經濟學家告訴我們,在市場上,買者和賣者具有同等的機會實現自己的愿望,自由、公平,就象一場足球賽一樣,規則對雙方的要求是一致的,取勝完全取決于你自己的競技。然而,哈里森指出,市場畢竟不是球場,球場的裁判是一個公正的第三者,而市場的裁判則是競賽的雙方,也就是說,這是一場沒有裁判的競賽。他否認現實市場中存在公平交易的說法。他說:“世界上沒有純粹的自由市場。……就連兩個小孩在用貝殼換大理石的時候,也不是完全平等的,如果那個比較厲害的孩子愿意的話,他總會占到便宜。……任何討價還價的結果,都取決于參與者的討價還價的力量……取決于雙方控制市場的力量。”(第488頁)
西方發達國家之所以推崇市場化,是因為在一般貿易中,它們具有控制市場的力量,它們有雄厚的資本、組織良好的公司和信息靈通的銷售網,生產技術居領先地位,不管怎樣比賽,它們總是贏家。如果它們不具備市場競爭的優勢的話,那么這些市場主義者們是會翻臉不認帳——不承認市場規則的裁判權的。中國鴉片戰爭時的中英貿易,現在美國面臨的毒品走私和西方盛行的關稅保護,即能說明這一點。不論過去的市場,還是現在的市場,都是強權主宰的世界。中英茶葉貿易,完全合乎市場規則,可英國人并不遵循這規則,而使用鴉片加大炮,打亂中英正常的市場交易。哥倫比亞向美國走私毒品,雖然在道德上講不過去,但卻是真正的市場交易,而美國不惜動用武力,到哥國土地上去掃蕩。還有美國強制性地限制發展中國家向它出口棉紡織品以及其它產品,亦是它們并不真正信奉市場原則的顯例。
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不懂得其中的奧妙,錯誤地把現代化的命運寄托在市場化戰略上。在國際市場上,它們幻想以“出口導向”、“進口替代”方式同西方一爭高低,幻想以一兩個“拳頭”產品打出去,但正如哈里森所說,這是一場大賭博,所有的輪盤中的骰子和紙牌都被人做成圈套或做了記號,發展中國家不論怎樣,使上渾身解數,到頭來仍不過“孔夫子搬家——盡是書”(輸)。其結果,國際收支難以平衡,赤字增加,加之貿易條件惡化,跨國公司又在其中操縱,發展中國家簡直只有靠借債度日了。但債臺高筑本身亦是問題,它會使債務國自身發展完全無望,徹底依附于發達國家。在國內,市場化執行的是一種社會分化的使命,它使社會按照經濟效率而不是按照社會公平的原則重新組構。誠然,就微觀經濟效應而言,它的作用是積極的;但對社會的宏觀效應來說,卻有消極的作用。一方面,市場機制可以加快經濟動量的運行,創造出更多的財富;另一方面,市場機制又可以導致社會大多數人貧困、社會不平等和動亂。有人說,不錯!要發展,就必然有貧困、不平等和動亂,這是現代化產前的陣痛,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哈里森不同意這種觀點。他說:“這一理論在道義上和客觀實際中都是站不住腳的”。(第483頁)他認為,社會發展的關鍵是解救三分之二的極度貧困的人。如果經濟成長僅僅對少數富有者有利,僅僅是維持、甚至擴大國與國之間的和一國之內人與人之間的貧富差別的話,那么,這就算不上什么發展,而只能是剝削。同時,在實際中,社會財富聚積于少數人手中,并不一定就轉化為資本,促進本國工業的發展。第三世界的大亨們,喜歡將錢存入外國銀行,或用于購買進口的奢侈消費品,而不是象西歐的清教徒資本家那樣熱衷于投資。這樣,第三世界的錢流向國外,社會分化的后果,并沒有象一些人所期待的那樣,在陣痛之后,出現一個現代化。
工業化、城市化、西方化和市場化不等于現代化,反過來說也一樣。但這決不意味著發展中國家可以不要工業和城市,不引進西方的科技和文化,忽視市場機制,而只是說發展和現代化,在過去和現在,西方和非西方,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應該有不同的道路,不同的選擇。哈里森的《第三世界》使我認識了第三世界,也認識了什么叫發展什么,是現代化。但愿我的同胞讀一讀這本書,或許還會得到更多的啟示。
(《第三世界——苦難·曲折·希望》,〔英〕保羅·哈里森著,鐘菲譯,新華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一版,1.40元)
——評《中國現代化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