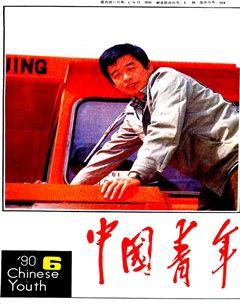在知識的海洋中起舞
胡守文
生活中,以海來比喻的東西很多,最常見的,便是“學海無涯苦作舟”一說。
明知學海的深闊,偏要競舟苦渡,與驚濤搏擊,與潛流抗爭,歷盡艱險,矢志不移,這就是人類至今能取得長足進步、特別是近幾十年來突飛猛進的重要原因。
世界范圍內科技和經濟進步發展的狀況已經呈現在我們眼前。日本提出:日本人要做“國際人”。伴隨這一口號,我們看到在日本,下起8歲孩童,上至80老翁,拼命攻讀外語者大有人在;候車間隙,乘車途中,目不旁視,沉湎于書本的日本人比比皆是。和著這一片朗朗讀書聲,日本產品發出了要占領全世界市場的呼嘯。面對日本這一“經濟動物”的崛起,美國人驚呼:“日本能,為什么我們不能?”
其實,科技與經濟的競爭,說到底,是人的競爭,人的素質的競爭。我們的民族要想趕上和超過發達國家,就必須培養和造就成百萬上千萬有理想有知識的人。一個知識貧窮的民族,也許可以靠大自然的恩賜逍遙于一時,終究是沒有希望的。
中國人聰明,世人皆知。不幸的是,這100多年來,我們落伍了。于是,許許多多的中國人為了迎頭趕上,渴望知識,拼命讀書。特別是改革開放,國門洞開,國外形形色色的新學科、新知識紛至沓來,譯本羅列,真叫人有目不暇接之感。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我們該怎樣提高自己的知識素養、又該學習什么樣的知識呢?有的青年認為,凡是新的東西,都是有價值的,這實在是一個謬誤。正如泥沙俱下,魚龍混雜一樣,新東西中,有的是精華,有的是糟粕,需要認真鑒別的,切不可把偽科學的東西奉為至寶。不能見“新”便不辨真偽良莠,一擁而上,形成一陣一陣的閱讀熱浪,一害自己,二害民族。孟子說過,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是我們可以引以為戒的。食古不化,有悖于時代潮流,食“新”不化,不也是有悖于時代潮流的么?培根有一句名言:“知識就是力量。”其實,這句話只講對了一半,其局限性在于它是建立在實驗科學的基礎之上,還沒有看清知識也可以用兩分法,有害的知識不僅不是人類可以借助的力量,反而會引發巨大的破壞力,給人類造成傷害。
那么,我們應該怎樣儲備自己的知識呢?古今中外的圣賢學者已講了不少。比如,要多讀,納百川入海;不要怕一時不甚明白,多讀自然會增加理解;要讀好書,在博覽的基礎上精讀;等等。但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就是,生也有涯而知無涯,人類的知識在不斷發展著。那我們該怎么辦呢?我覺得,“忘卻”不失為一種求知的好方法。
所謂“忘卻”,并不是真的忘得一干二凈,不能將它視作“記憶”的反義詞來理解,它不意味著記憶的漫不經心,而恰恰是求知時的最佳狀態。
“忘卻”,指人的自持力和條理性,在求知過程中,不被外界所干擾,能按輕重緩急安排自己的學習,進入有序而次第發展。
“忘卻”,同時還意味著在知識儲備過程中有意識地篩選。因為一則知識更新速度很快,知識總量大大超過了一個人所能承受的程度,二則儲備知識是為了運用,而不是為了擺設和炫耀。因此,我們所學的知識必須經過提煉這一道工序,提煉就意味著既有記憶又有忘卻。從這個意義上講,忘卻是為了記憶、記憶就必須忘卻。忘卻最多的人,也許正是記憶最豐的人。
知識的海洋,美麗而神秘,使無數駕舟人樂而又忘返。有膽有識者,才可以在其中輕舒長袖,翩翩起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