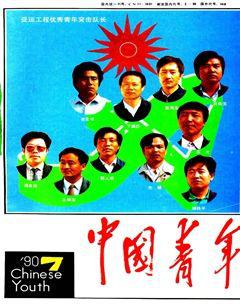采訪北京市勞動就業情況札記 勞動就業:選擇中的難題
王林
“我晃蕩幾年了,至今沒有找到工作。”在北京西城區勞務市場,一個20幾歲的育年沮喪地對記者說。他肯定像他這樣為求職奔忙的青年有很多。“你瞧,”他指著身旁熙熙攘攘涌向勞務市場的人流,“瞎忙活,沒戲!”
的確,近年來就業問題,成了城市青年和他們家長憂心伸忡的話題。特別是治理整頓以來,聽說一部分企業處于停產半停產狀態,更給一些人添了幾分焦慮。一些數字仿佛在印證人們“求職難”的焦慮:
1985年,北京市的待業人數只有1600人。1989年,有12.1萬勞動力需安排就業;
1988年夏,即將營業的合資企業京廣中心在京公開招聘職工200名,可是涌向設在地壇公園報名處的人竟達20000人。20000與200,形成百里挑一的局面;
1990年4月,北京某高檔時裝商店招收50名導購小姐,報名者逾千人,原準備好的報名表格很快發光,只好用白紙代替。
像這樣的數字和事例還可以舉一大串。無怪乎有人高叫“求職難”,“就業難”了!
“不,不能簡單地下這個結論。”北京市勞動部門的一位工作人員說。他也列舉了一大串數字:
1989年,北京煤炭公司600名老工人退休,需招300名新工人,一年多未能招滿;北京國棉三廠在朝陽區勞務市場招工,整整一年,報名人數不到50;1989年北京市建筑行業新增職工2.67萬人,城市招收的只有3800人,其余都是從農村招收的……
據北京勞動部門統計,1988年北京市在冊的農民工達73.8萬人,加上流動的,可達130萬一150萬,幾乎是北京市職工總數的1/3。有人分析指出,目前農民工的崗位,有40%是城市居民可以從事的工作,大約相當于北京市現有待業人數的2倍!這就是說,一個城市青年,想找一份工作,根本不成問題。
那么,北京市為什么會出現“招工難”與“就業難”并存的現象?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城市青年擇業觀念的變化。70年代末,大批在農村經受了磨練的知青返城時,就業對他們來說,選擇的欲望非常小,能夠在國營工廠當個工人,就會使他們滿足。隨著10年改革的推進,在這10年中成長起來逐步進入就業年齡的青年,其思想觀念與上一茬人差別很大。西城區勞務市場負責人王振良認為,現在青年人尋求職業希望具備五點,即:離家近一點,工作輕一點,收入多一點,環境好一點,名氣大一點。進一步分析一下,可以看出現在青年人追求收入高,工作有新鮮感、主動性是其擇業觀念的核心部分。正是如此,青年求職者不約而同地涌向大飯店、合資企業、商業及一些經營性公司,而使建筑、紡織、環衛等行業遭受冷落。這一趨勢的自然結果,是大批農民工涌入城市,填補了城市人為造成的職位空缺。
對于青年這種“高標準”的擇業觀念,我們很難用“對與不對”,“好與不好”來做簡單的評價;假如我們細加分析,會發現這種擇業觀念的形成是一種合理性與盲目性、消極性與積極性的極不協調的組合。
10年前,當一個青年進入就業領域,無論你到哪一個行業,哪一個單位,就業之初,工資差別并不明顯,收入只有隨著工齡的增長而增長;再加上挑選職業的機會不多,無法使人產生可以付諸實踐的選擇欲望。而在這10多年的變革中,統一的工資制度開始瓦解,在行業與行業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出現了明顯的差別。不可否認,幾乎每一個人都希望在工作中獲得高一些的收入,這種愿望在眾多的部門收入水平不同的現實面前轉化成了一種對職業較強烈的選擇欲望。如一些大型國營企業依然按嚴格的晉級制度評定工資,一個學徒工基本工資三十七八元,其它福利加起來多的也就一百元左右,顯然難以滿足一些青年人的消費欲望,這點工資還不夠小伙子買兩條好點的煙,不夠姑娘買點高級些的化妝品。如果進入大飯店、合資企業及一些經營性公司,月收入上二百元已不是新鮮事,而且各種獎金、分紅也使人眼熱。這種現實的對比,給尋求職業的青年人提供了一個對社會工作者來說感到苦澀的導向。這種導向所以使人感到苦澀,是因為人們的擇業方向在這種現實的差別面前而發生轉變是合情合理的,但是這種轉變又是建立在一種不合理的因素之上。這種收入的明顯差別并非是完全建立在合理的按勞取酬的原則之上,同樣是體力勞動,在一些國營企業工作付出的勞動強度并不比在合資企業、大飯店等部門工作付出的勞動強度低,可收入卻相差甚遠。這種不合理的現象使人產生愿到收入高的部門工作的擇業欲望此時就具備了某種合理因素。
但是,這種現實導向引發的擇業欲望相對擇業者自身素質和現實條件來說又往往超前。近兩年,合資企業、大飯店的招工高峰已過;公司整頓,使大批從公司中轉下來的人員尚需安排,更何談大范圍招工;勞動服務公司、街道聯社享受國家優惠政策期限已過,人員已相對穩定;一些熱門企業正為如何安排自己富余人員而尋求對策,招工工作已處于“冬眠”狀態。在這種情況下,求業者的自身素質高低已成為找一份好工作的關鍵因素。大飯店、商業流通行業在招工時,對求職者的身高、外貌、氣質要求頗嚴,且往往要求具備一定的外語水平和實踐經歷;合資企業對人員的文化、技術素質要求較高,這些條件將許多求職者毫不留情地拒之門外。但是,這一現實并未使求職者喪失信心,大批的青年人依然在這些單位高高的門坎前徘徊,而對自身素質和現實條件不予理睬,因此使這種超前的擇業觀念具有了一種盲目性。
那么,為什么說這種擇業觀念又有一定的積極性?這一觀點從宏觀的分析中可以得出。10年改革,不僅是經濟改革,同時也是觀念的巨大變革。它體現在擇業方面,便是青年人在求職中對競爭觀念的認可,這一點使擇業觀念異常活躍。許多青年人希望找一份理想的工作而不愿湊和,他們依仗年齡優勢,在相對10年前無法比的多種就業機會面前,他們選擇的大膽和挑剔使年齡大的人難以理解。在這些選擇中,不可否認具有對人生更主動追求的因素。我們現在常聽到一些青年人說“趁年輕時闖一闖”,這“闖一闖”往往意味著失去醫療福利和分配住房的機會,也許年齡大一些后還將面臨第二次就業,這種敢于擔負風險的選擇可以說與當代青年的精神有較大的趨同性。這種精神通過正確的引導,對社會生活的發展和活躍不能說沒有積極意義。
可是,許多做實際工作的人士對這一點表示了有理由的憂慮。由于擇業者的挑剔,使許多國營骨干企業招工困難,使在崗人員素質下降;一些技術水平較高,有一定能力的在職骨干往往不安心現有工作而出現大量“跳槽”現象,嚴重影響了正常生產,使許多企業不得已不顧常情而制定土政策來“卡”住人員的流動;一些行業因招不到城市工而只好招農民合同工頂崗,這不僅給管理工作帶來許多難題,而且給企業的長遠發展造成了后患。種種憂慮,不可避免地給青年人的擇業觀念蒙上了一層消極的陰影。
尋找解決矛盾的對策,這需要整個社會去努力。為解決就業難和招工難的問題,北京市勞動部門做了大量的工作,主要是對求職者進行形勢和責任教育,引導青年人樹立艱苦奮斗,為國家分憂的思想。但是僅僅靠勞動部門的力量來完成轉變擇業觀念這一工作,顯然難以有大的成效。而如欲扭轉擇業流向,必須在政策制定上使收入分配更加合理,拉開臟、苦、累和有毒有害作業與一般工種的收入差距,使這些行業在招工中具有更大的競爭力,讓工資收入在就業問題上發揮有力于社會發展的杠桿作用。
所以說還需要整個社會的努力,這是因為在勞動就業問題上,我們不能不考慮青年人自身的特點,即對更加活躍、豐富的生活內容的追求。大批青年人之所以向往到大飯店、流通領域及合資企業工作,除去希望有高收入、名聲氣派等因素外,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即青年人認為到這些部門工作可以見世面,可以有更多的交際機會,以使自己的生活更加豐富多彩。在目前青年人業余生活較單調的情況下,這種愿望無可非議。關鍵的問題是,我們如何創造更多更好的條件來滿足青年人業余生活的需要,而不使青年人將這一愿望寄托在職業的選擇上。這方面的工作,對每一個社會工作者來說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另一點,我們希望企業領導者開明一些,更多地關心青年人的生活,為他們在心理上創造一個良好的工作環境。這些因素,無疑對引導就業流向、安定青年人的工作情緒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但是,問題解決的最終實現,也許還是要由青年人自己完成。無論如何,所有青年人的所有愿望得到滿足,這是一句虛話。社會仍將希望寄托在青年人對國家困難,對就業形勢的認識和理解上。在國家處于困難時期,這一代青年人的利益勢必要做出一些犧牲,但這種犧牲不是無謂的,也許它將對我們后代的幸福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正確的選擇,是每一個人的難題,也是每一個人的責任。